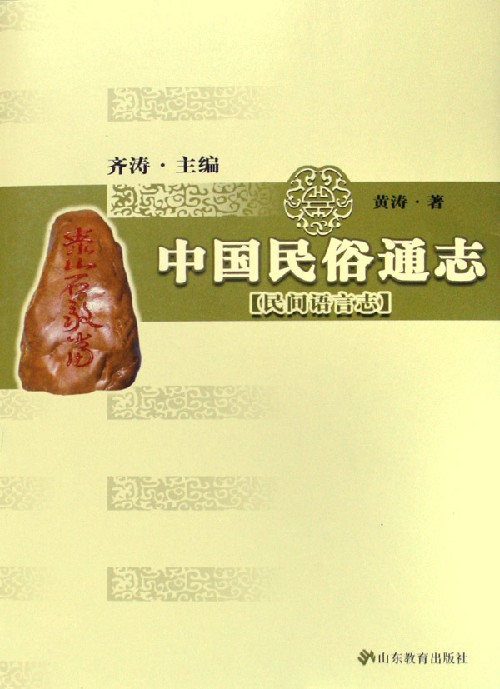 分类必须基于逻辑,这是常识。尤其在学术研究中,尊重逻辑已经近乎于一种工作准则。但在实际工作中,仅仅依靠逻辑的运作一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齐涛、叶涛组织的大型《中国民俗通志》,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分类问题。 民俗是普通民众的直接生活方式。生活何其丰富多彩,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一个区域社会的民俗生活方式都是自成一体的功能系统。每一系统的内部,功能之间是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但在区域与区域之间,也即系统与系统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功能关系,也就是说,各系统的“民俗单位”(一般表述为“民俗事象”)符合索绪尔符号学的“任意性原则”。 若以系统的逻辑来对“任意性”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理论上说,只有在某一个特定的、独立的、完全同质的民俗生活圈内才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我们根本无法为变动不居的文化形态划定一个完全同质的民俗圈,更不用说当我们把搜罗的范围划定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多民族空间之内。 逻辑分类要求同一层次的划分必须依照同一标准。比如,我们可以依存在方式把民俗划分为“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这也是一般民俗学教材的划分方式。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许多现实的民俗事象无法明确地归入到这些类别之中。为什么?比如一个庙宇建筑,它当然是物质的,但是,它的所有结构与功能,折射的全是精神世界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它归入到物质民俗呢?还是精神民俗?于是我们只能更换分类标准,重新划分,但无论我们换成哪一种分类标准,我们都没有办法像庖丁解牛一样把一个整体的民俗事象拆成零碎的构件分门别类地塞进不同的框架中。 逻辑分类要求所有的类别互不相容、互相排斥。这就更麻烦了。同质民俗生活圈内的民俗事象之间固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功能系统,但并不是说,每一种单一的民俗事象,都只承担着单一的功能,只能归入到一个类别之中。餐桌上的一条鱼,可能既是节庆饮食,也是地方特产、社会仪礼、祭祀用品,当你把它归入到饮食民俗类别的时候,你如何能排斥它作为礼仪和信仰的功能呢?生物学上的狗只是狗本身,民俗学中的狗则可能指涉了一系列的功能叙事,或者信仰、禁忌甚至民间艺术。 如果说,从功能系统本身出发的、内在的逻辑分类难以发挥它的权威效用,那么,《通志》将依据什么来对纷纭复杂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呢?只能从“分类的意义”这一外在的要求着手。 民俗事象的分类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分类是帮助普通读者认识民俗文化的一种描述方式;2,分类必须为研究者提供比较研究的方便。以上两种现实意义,最终都必须经由“检索”而起作用。也就是说,《通志》的分类系统必须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检索的方便。 那么,检索的入口又在哪里呢? 在“经验”。 既然民俗志的写作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分类标准,读者就只能凭借其经验知识来作为信息检索的入口。从方便读者的实用写作的角度来说,读者的检索入口自然也就成为了编者的分类基础。由此看来,分类也可以基于编者和读者之间的共同知识,也即对于民俗文化的经验认同。 那么,经验又从何而来?或者说,以什么经验来作为《通志》的分类参考? 《通志》的分类经验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普通民众的经验知识,二是传统民俗学的分类形式,三是既有的民俗研究范畴。 民众的经验知识是最直接的实用分类系统。如《通志》根据民众“衣食住行”的概念直接分出了服饰志、饮食志、居住志、交通志;根据我们熟知的人生三大仪礼直接分出了生养志、婚嫁志、丧葬志等。 传统民俗学的分类形式主要是指通行的民俗学教科书(如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的分类形式,以及传统“风俗志”类书中的分类形式。《通志》参考这些分类传统,列出了生产志、宗族志、节日志、信仰志、游艺志、民间文学志、民间语言志、民间工艺志等等。 既有的研究范畴主要是指已经形成规模的、有一定研究实绩的民俗研究领域。诸如近十几年间兴起的游民社会研究、禁忌研究、庙会研究、民间医药研究等。《通志》据此分出了江湖志、禁忌志、庙会志、医药志等。 从《通志》的整体布局来考虑,经验分类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操作。尤其是方便各专志作者充分发挥他们在各专门领域中的学术优势,方便他们在实际的撰写中根据各自的研究经验重整该领域的分类形式。如郑土有在《信仰志》的撰写过程中,就能够“将自己多年来对信仰民俗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和对构建中国民俗信仰体系的一些想法融入在体例编排上,在分类方面作了一些创新,将地方神信仰、仙人信仰、精怪信仰、他界信仰单独列章。”(《信仰志后记》) 基于经验的知识尽管实用,但毕竟偏于感性。个体之间的经验差异,可能导致整体结构的散漫无序。个体经验必须受到共同逻辑基础的理性束缚,整体的分类体系才有整饬的可能。所以说,逻辑划分尽管显得机械笨拙,但它是规范书写的理性保障。落实到《通志》的具体篇章结构中,我们不可能不考虑类别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通志》的组织者将如何发挥逻辑标准在经验分类中的用武之地呢? 组织者试图通过对于“时空边界”的限定,为逻辑效用提供条件。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事物越是混沌,系统越是复杂,就越有划清边界、明确对象的需要。 首先,组织者把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划定在“20世纪前50年”,这在民俗志体例上是一个极聪明的创举。我们知道,即使是同质的民俗区域,不同时代的风俗习惯也难以纳入同一共时系统,而“20世纪前50年”是一个相对同质的风俗时段,无论是从资料的获取、系统的构成,还是时段的完整等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边界。 其次,考虑到乡村社会与官方社会、城市社会的系统差异,组织者决定把记录的重心落在“以汉族为主,兼及各少数民族”的乡村民间社会之中,在社会构成上尽量将不同区域民俗系统的异质差异减至最小。 再次,组织者主张在个别中体现一般,在一般中突显个别,在生动具体的民俗个案的叙述中,照顾异地同类事象的多样性特点,以点带面。也即以个案为中心,保障描述的生动性,兼以类型为经纬,体现通志全面、周到的特点。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组织者严格地限定了《通志》的记录范围和记录方式,尽可能地将系统间的异质差异减到了最小。 《通志》撰写中的“同质意识”对于同类志书的分类实践无疑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学术话题。 正是在边界清晰,以及大致同质的基础之上,民俗事象的类别数量才能得到有效收敛,不至于发散至无限多样,逻辑才能得以发挥其约束经验分类的作用,使得经验分类能够尽可能纳入到理性和规范的轨道之中。 从以上分析可知,《通志》的组织者在分类问题上既充分地考虑了读者的需求与方便,采用了“经验分类”的方法,也充分地考虑了民俗功能系统自身的逻辑关系,坚持了“逻辑分类”的“同质意识”。两方面的尽可能完美的结合,就是22卷洋洋巨制的《中国民俗通志》。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