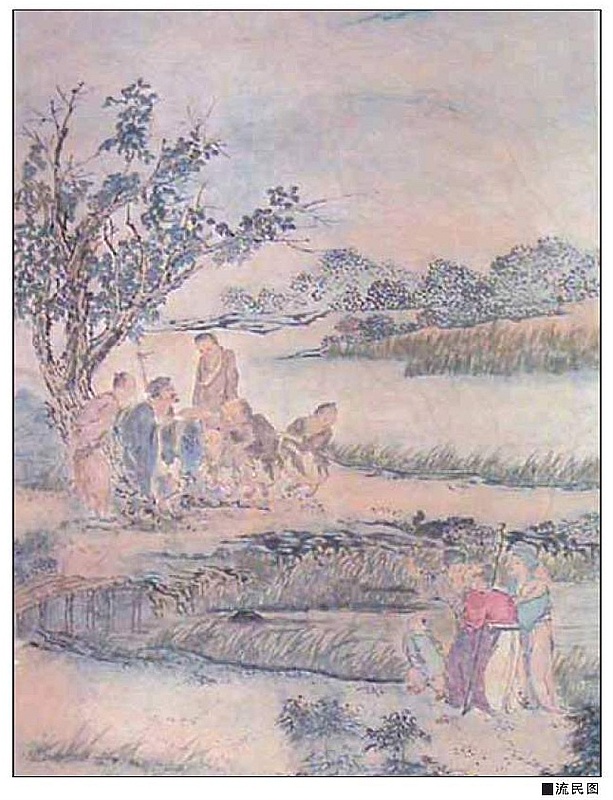 西方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40—70年代基本停滞,80年代以后日益增多,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最早的西文研究是马罗利(Walter Mallory)的《饥荒的中国》(1926)。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频繁遭灾,马罗利以华洋义赈会秘书的身份,考察了这些灾害的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根源。国内最早的研究是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马罗利和邓拓都注重灾害的成因。此后数十年,战争和革命比饥荒更吸引学者们的注意。1980年代初,灾害重新成为中国和西方的重要研究课题。从那时起,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较少关注灾害成因,而更关注饥荒与中国政府的功能、世界历史中的清代救灾活动、文化和宗教对饥荒的反应三个问题。 饥荒与政府赈济 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始于1980年代初的几部重要著作,它们都把救灾作为晚清帝国的一项主要工作和成就。第一部著作是法国学者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该书1980年在法国出版,1990年译为英文。魏丕信运用丰富的资料,考察了18世纪的清政府在防灾和救灾方面的独到经验。他发现,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大清政权维持了庞大的谷物储备来应对饥荒,同时把向灾区运输、发放粮食与其他救灾措施(如蠲免赋税、发放赈银、允许人们迁移等)结合起来。魏的著作鼓励学者们关注传统中国政府的成功而非薄弱之处。在他的影响下,王国斌和彼得·珀杜就官僚制度与灾荒合作撰写了长篇评论,发表在1983年的《哈佛亚洲研究》上,该文通过比较直隶与甘肃、江南两地的救灾活动,拓宽了魏的研究范围。 中国灾荒史研究也极大地得益于1980年8月在哈佛大学成立的“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索斯摩学院李明珠教授组织的,同时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赞助,它把第一代西方的中国学者联合起来关注灾荒,并促成了1982年8月《亚洲研究》(JAS)上的一次名为“食品、饥荒和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包括李明珠的介绍文章、李中清关于1250—1850年中国西南地区食品供应和人口增长的论文、彼得·珀杜的论文《官员目的和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的水控制》、王国斌对清代粮食骚乱的研究和一位研究印度灾荒的学者保罗·格里诺的《南亚视角下的评论》。与魏丕信一样,这次讨论关注的也是政治经济学、治国才能、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这一倾向主导了1980、1990年代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具体而言,他们都考察了政府政策和人类行为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提出了在食品—饥荒史上与更大的人口统计和生态力量相比,政治权力具有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并考察了清政府防灾、减灾能力的不断变化。 在1980年成立的工作室中,五位参与者——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彼得·珀杜、戴慕珍同意更深入地共同研究该室提出的很多问题。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是1991年出版的《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仓储制度》一书。这本论文集主要由魏丕信和王国斌撰写,对清朝各省仓储制度的发展、基本结构、内部运作、成就及最终的衰落进行了丰富的制度史研究,并对清朝仓储在晚清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重要的评价。此外,澳籍历史学家邓海伦在1996年出版的《聚讼纷纭的经国论议》中,对清政府的粮食贸易和大众生计的政策进行了研究。通过翻译和分析一系列重要的盛清文选,邓海伦认为,在国家因为抗灾而干预粮食贸易这个问题上,18世纪的官员有很大的分歧。 在对饥荒和中国政府问题的广泛研究中,李明珠的《华北赈饥荒:国家、市场和环境恶化(1690年代—1990年代)》(2007),考察了300年内直隶地区的政府、市民、意识形态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在20多年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该书对清代救灾活动的成效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在以乐观的眼光考察晚清时期农业、商业和人口问题的修正主义学者面前,李明珠重新评价了中国历史经验中饥荒、人口压力和农村贫困的重要性。她同意魏丕信和王国斌的观点,即18世纪的粮食贸易体系和国家仓储在保证“北京的粮食安全”上是有效的,它引导物资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流动,并且提供了“社会财富支持下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她指出,政府在促进直隶经济稳定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并未导致当地长期的经济变化。另一方面李明珠提出,中国在19世纪的一些危机的根源可能可以追溯到盛清时期激进主义政策的成功。她认为,18世纪高压管理下的成功和政府给灾民提供救济的意愿维持了华北地区空前庞大的人口,并且使人民更愿意移居到靠近湿地和堤坝的水灾易发地区。密集的人口居住区意味着当水灾或旱灾发生时,人类付出的代价更高。她写道:“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生态危机是18世纪帝国运行取得巨大成功而非失败的产物。” 全球视野下的清代救灾 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比较在对灾荒的政治反应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例如,在1982年的《亚洲研究》研讨会上,保罗·格里诺深入比较了印度和中国政府对普遍贫困的干预传统,指出在印度,“类似与中国人生存问题有关的基本政治主题正在大量消失”。而且印度统治者没有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即如果君主让人民无法生活,上天将剥夺准其统治的“授权”。和中国相比,印度人在饥荒期间对政府的期望更加有限。 王国斌致力于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清代荒政。在与彼得·珀杜的合著中,王国斌1983年的一篇评论文章对中国和西欧的荒政进行了对比。此外,在《养民》(1991)一书中,王国斌专门撰写了《清代仓储与世界历史》一章。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中,他对很多比较作了详细说明。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同于罗马、拜占庭、土耳其和莫卧尔等帝国,也不同于早期欧洲国家,因为它对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要承担责任,遇到粮食不足时要肩负国家干预的重任,并且要把维持公共粮食储备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国家经常缺少能力和官方命令去建立和维持粮食储备。他们的建国议程不包括那种反复推动中国人的家长式的关心”,他写道,“比起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清朝的成就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王国斌批评了“面对灾害,欧洲的主动和亚洲的被动之间存在普遍差异”的观点,认为就缓解生存危机而言,“如果不考虑整个的帝国历史,中国已经近代化了好几个世纪”。 社会学家迈克·戴维斯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大灾难:厄尔尼诺、饥荒和第三世界的形成》(2001)中,利用魏丕信和王国斌对清代仓储的研究,对现代世界历史中灾荒的角色提出了独创性的看法。戴维斯考察过19世纪晚期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埃及等地主要由旱灾导致的饥荒,他谴责帝国主义者强行在这些因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戴维斯指出,在中国,“国家生产力、公共福利特别是救灾能力的迅速下降”和清朝被迫向英国和其他列强所代表的现代性“开放”是“一致”的。他认为,伴随着国内战争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动荡导致清政权的仓储遭到灾难性的损耗。这意味着清朝的统治者无法像他们18世纪的祖先那样进行统治,事实也证明他们无法预防1870年代末和1890年代袭击北方且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干旱。借用大卫·阿诺德强调饥荒是“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观点,戴维斯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其实是收入和财富不均衡的产物……他们大多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形成的,在这期间庞大的亚非拉农民阶级开始被整合到世界经济中”。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