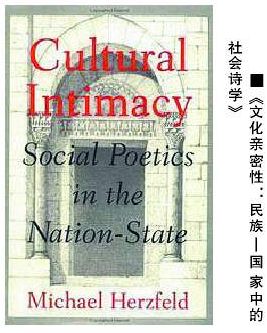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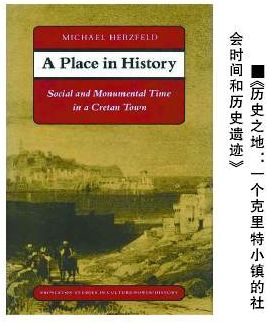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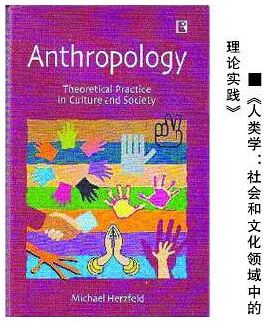 历史学与人类学都高度关注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历史学研究注重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关注事件的时间性。近年来历史学者大量应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强调历史事件的空间性与现场感,产生了历史人类学学科。您认为人类学研究方法对历史学研究有哪些帮助? 赫茨菲尔德:历史学家经常会运用人类学家的观点来阐明自己的研究,这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只不过有时只借鉴那些与其设想相同的人类学概念,略显机械化。 每个学科都有特定的经典理论,虽然学科间的差异能引发一些有趣的争论,但也会阻碍彼此间的合作。尽管如此,历史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目标和关注内容上更为相似,例如,人类学家也收集文献资料,我把它称作“口头文献”。历史学与人类学都高度关注细节,与不负责任的普遍化概括或宏观模型建构相比,这种对具体事实的解读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有很多,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让彼此真正获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正由传统转向现代,您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赫茨菲尔德:“传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的,它更强调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归属感,而非真正起源意义上的“传统”。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定义现代性这一问题,因为当今人类学领域对此有很多定义方式。人类学家并不局限于研究过去的部族、小型封闭社会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诸如“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这些概念并不应该成为人类学领域研究的一种地域划分方法,只是有的国家更多地利用工业技术发展这一优势而已。 另外,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与如何衡量和定义“发展”有关。当今社会工业科技飞速发展,但也对自然环境带来了破坏。韦伯曾认为现代性一方面对官僚理性化有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将人类引入了“铁笼时代”,这带有一定的反讽意味,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同。在研究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过程中,我发现,现代欧洲政府官僚体制所倡导的理性行为可以追溯到欧洲早期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在预测形式和预言结果的解释上,现代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与东非部族的占卜仪式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此外,我不认为应按社会复杂程度给各个人类社会划分等级,地方性的人类学研究往往可以以小见大,为人类学提供独特的视角。 “参与性人类学研究”强调人类学者要有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遗产保护与研究进入人类学视野,文化人类学研究是如何界定遗产这一概念的?作为人类学工作者,多年来您一直在田野工作中致力于遗产保护观念与实践的探索,请谈一谈相关研究的工作体会。 赫茨菲尔德:我们对“遗产”这一概念的使用方式非常感兴趣,这并不是想追究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否真实,而是想考察历史与现在之间的某种联系。 我在希腊、意大利和泰国的工作很大程度是考察历史保存对社会生活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如同考古工作一样,对历史的保护总是部分的。因此,我们常常需要对选择哪一部分做出抉择。这些抉择不仅影响当地人对过去的理解,而且还可能造成一定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而当看到人们因某些不正确的观点或选择而受到侵害时,人类学家应该承担一份道义上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应用人类学,它和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特质有什么关系?您提出的“参与性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应用人类学有什么区别? 赫茨菲尔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用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并不将生产学术知识作为首要目标,而专门服务于银行、政府等某类组织。一些应用人类学常常会采用一些由上至下的社区问题解决方法,而在医药和营养领域也有很多积极的应用人类学。 “参与性人类学研究”则不同,它是从学术工作者的研究中有机生长出来,从比较纯粹的学术实践出发,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和现实问题。我在泰国发现,当地居民在维护景点的清洁和完整性方面愿意与官方合作,我确信他们这样的思路更好。正是由于亲身参与,我才获得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数据。“参与性人类学研究”在做学问的同时也能使当地人受益。我们的研究会以当地居民的利益和需求为尺度,衡量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只有当地人、规划者和官方在“什么对社会有益”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让每个人都受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胡宗泽对本次采访予以大力支持,特此感谢。本报实习记者赵媛也参与了采访录音整理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