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本质标志,但它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却呈式微的趋势。 德波顿这部谈宗教的书谈了许多问题,惟独不谈对于宗教最重要的信仰问题, 反而要人不必秉持信仰,这恰恰反映了现代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特征,即不问信仰,但问有用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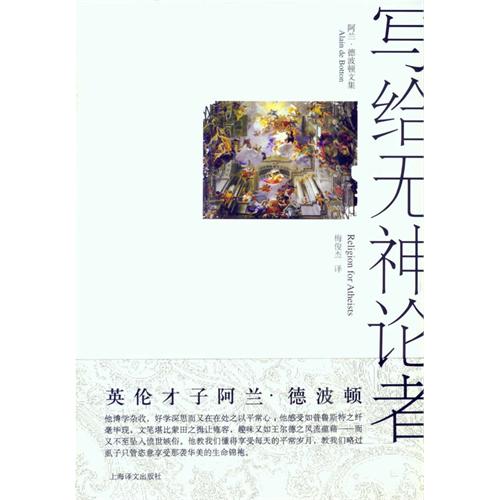 《写给无神论者: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意义》(阿兰·德波顿文集) [英]阿兰·德波顿著,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296页,30.00元 尽管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本质标志,但它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却呈式微的趋势。虽然启蒙思想家把宗教作为“迷信”和“精神鸦片”来对待,但伏尔泰还是说过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这样深刻的话。这说明,即使像他那样激进的宗教批判者,还是看到了宗教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意义。伏尔泰毕竟还是有信仰的。相比之下,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自称无信仰者的英国人德波顿,就秉承英国小店主的传统,只知宗教的用处,而不问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了。的确,正如他这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宗教要获无神论者的青睐,大概也只有说它的现实用途了。可是,说宗教的用处与说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毕竟是不一样的。谈论宗教的用处,对于我们理解宗教,不太会有根本的帮助。 毋庸讳言,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当然是有用的,但宗教之所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却不是仅仅用“有用”就可以解释的。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人性根据,而不仅仅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如果说哲学是人理性的产物的话,宗教就是人情感和信仰的产物。人类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但都是出于人的信仰天赋。西方人喜欢以宗教来区别人与动物,就是因为只有人才有信仰这样一种独特的心理能力和倾向,它与感知和理性无关。信仰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发自人的内心深处,它没有感知和理性的根据,但人们需要它却远过于对感知和理性的需要,也只有人才渴望感觉和理性本身都会否认的东西。 那么,这种情感亦即宗教情感究竟为何?宗教情感首先是生命的情感。人生在世,不能不面对生死问题,正因为有生必有死,人才会对生命有特殊的情感,希求对生死问题、对生命的意义问题有某种理解。不朽也好,轮回也好,死而复生也好,都不是对经验事实的认识,而是出于情感的信仰,坚信生命的永续。人们依靠这种对于生命的丰富热情来抵抗死亡与毁灭。这种信仰再进一步,升华后就是对于无限和绝对的渴求。 按照德国神学家奥托的说法,对于崇高和绝对者,我们首先会产生一种依赖感,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种造物与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或最高存在者相比,不仅无法同日而语,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虚无”。因此,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一种绝对的依赖感。其次,既然我们无异于“虚无”,那么面对上帝的“目光”,面对这位神秘主宰的巨大力量,我们便不能不感到畏惧,感到震颤。第三,既然上帝是那样的崇高,那样强大,那样令人神往,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不满足感或向往感。用奥古斯丁的话说,我们渴望成为上帝。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能说没有类似的考虑。 很显然,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都不能提供“无限”或“绝对”的确切证据,但人自古以来就会渴望绝对和无限,渴望得到一个绝对与无限的超越者,即神的爱。其实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其他事物中人也会追求无限与绝对。这种追求一般不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而是出于对自己根本的有限性的觉悟,正是这种觉悟,产生了对无限与绝对的信仰。信仰是一种独立于感性和理性的力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与感性和理性相矛盾的,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力量,人类的许多伟大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个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历史上真正称得上伟大的人物,无不有其坚定的信仰。正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孔子才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苏格拉底才能为哲学而生,为哲学而死;释迦牟尼才能普度众生;耶稣基督才能坦然走上十字架。 无限与绝对过于抽象,所以人们又喜欢用一个相对具象的超越者——神来代替,这决不只是出于理智的考虑,也是出于情感的需要。人在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无助与根本的有限性时,需要有一个无限者给予他内心的慰藉,让他对神秘找到一种落实。人们在看到人世间根本的罪恶时,需要一个超越者来保证正义的存在。人由于私利作祟,不能明辨善恶,需要有一个绝对者来明确善恶的界限。这都不是感性和理性的需要,感性和理性只需要它自己,情感才需要超越者。以对绝对的超越者崇拜为特征的宗教,就是根据这种需要产生的。 最后,如汤因比所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起宗教,逆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宗教在近代的式微 这当然不是说宗教没有种种实用的功能,而只是说它不能完全用实用性来解释。论实用,许多宗教信仰和戒律往往不但不实用,反而有损实用。而且宗教的实用性往往是从其超越性中派生或变形而来。例如,人天生对神秘的东西有敬畏感,想要理解又不得其解,这就会演变为后来的充斥宗教的各种奇迹或怪力乱神。而人表现在宗教祭礼和葬礼中对于生的热情,对于死的不甘,又可以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和灰心,等等。但所有宗教的实用性,不是宗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乃是出于我们神圣情感和信仰的需要。实用归根结底与信仰是有抵触的。 近代的世俗化过程与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日渐式微,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凯恩斯说过:“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反宗教的,它没有内部联合,没有多少公共精神,通常(虽说并非总是)仅仅是一群有产者和逐利者的聚合体。”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则指出,《圣经》传统用“良心”来理解个人动机,而现代功利主义是用“利益”来理解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情感是不重要,甚至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计算理性,所有事情只有通过它的天平才能决定是否有意义。韦伯说的去魅化也好、理性化也好,都不过是计算理性以它的名义宣布情感产生的上帝已死。现在唯一的上帝是金钱,唯一的宗教是商品拜物教。哥伦布说:“金子构成财富,谁拥有它,谁就能得到他在尘世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有办法把灵魂从炼狱拯救出来,让他们重获天堂的欢乐。”这反映了现代人开始认为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灵魂的问题。但事实却是,在现代人这里,灵魂不再是灵魂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由自然科学研究和解决的物质的问题。 汤因比曾这样分析宗教在近代世界日渐式微的原因:“人们背叛基督教的原因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另一部分是理智上的。其道德原因是西方宗教分歧产生了毁灭性的然而毫无结果的政治和军事的角逐,其实质是恶意的、蓄谋已久的、残酷无情的,其追求的是不可告人的肮脏的世俗目标,与基督教高尚的精神使命正相抵牾,令人反感。理智方面的原因在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的宇宙观是由包括从圣保罗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一系列伟大缔造者从基督神话、犹太经典、希腊哲学与科学的混合物中建造起来的,已不再博得西方人的绝对赞同。” 的确如此。一方面,教会自身的所作所为有悖于宗教的精神使命与道德理想;另一方面,计算理性不再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得到证明。工具理性产生的科学迷信使得人们现在只承认经验科学的实证证明。而对于启蒙哲学家来说,宗教情感也不是人类的普遍情感。有些民族没有宗教,而每一个宗教民族的礼拜和虔诚的情感也不同于其他宗教民族。他们开始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实证角度来看待宗教,贬低情感的作用,抬高外部事物的实证作用。在休谟看来,宗教纯粹是由一些对生活的事件的关心,从不断刺激人心的希望和恐惧中产生的。宗教是从希望避祸求福,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这样非常实际(实用)的要求中产生的,这种广义的对宗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解也包括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休谟的《宗教的自然史》充分表明了它的社会学性质,虽然人们一般把它看作休谟的宗教哲学著作,我宁可把它看作最早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它实际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让人置身于一个去了魅的世界,一切事情都要交付理性的批判,走自己的路而不求助于任何超越的力量。 宗教本来就不是理性与客观事实的事,而是信仰和情感的事。康德似乎明白这点,所以他明确说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然而,在他那里,上帝或宗教只有道德的意义。我们信仰上帝,是因为道德生活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这也是启蒙以来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共同观点。不是我们的情感,而是我们的道德生活需要上帝作最后的保人。但这种上帝已经不是我们情感所依赖的上帝,而是理性的仆人了。所以海涅以他诗人的敏感看出,《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这并不是浪漫的夸张。康德的上帝的确不能解释我们许多宗教经验和神秘体验。当然,对于本质上否认超越性的现代性来说,那些经验和体验充其量只有个人意义,没有普遍意义,因为它们和上帝的存在一样,得不到客观的证明。而在现代性眼里,不能得到客观证明的东西就是迷信。 现代人已经很少会像歌德那样认为迷信是生命的诗歌。相反,迷信意味着非法和无效,意味着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尽管神学家还在苦心孤诣地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但现代人本质上都已经是无神论者了,他们或许也会定期上教堂做礼拜、去祷告,但不过是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而已。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上帝死了,以及上帝死了什么都可能发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