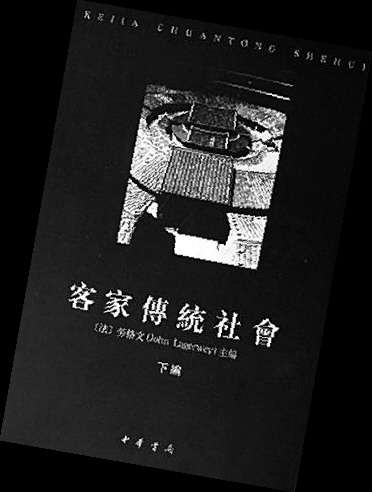 与这本书的相遇,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高中毕业后在广东从化一个客家山村插队当知青的情景。刚到没几天,邻村的一位也是从广州来插队的老知青请我们吃饭。饭间谈到客家人的风俗习惯,他说这里的客家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独特的风俗了,除了讲客家话,就和流溪河边那些属于广府文化的村子没什么区别。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我在生活中最早接触到的民俗与语言相分离的问题。这本由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上、下,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虽然没有收入专门研究客家方言的文章,但是劳格文在“序二”中却谈到了当年那位老知青聊到的话题:“客家地区至少要分成四片,即闽西、赣南、粤东、粤北。我有一个很临时的想法,认为客家语言于元朝在闽赣交界区形成之后,很快就向粤东发展。从明中叶开始,这两个地区的移民把它带到粤北和整个赣南。因为粤北和赣南在清初之前不能算是客家,他们的文化与北方的赣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与客家的关系,更多地是同属于一个语群,而非族群”(第492页)。他在另一处更明确地谈到:“‘族群’这个适用于欧洲的概念在中国是否适用,或者用‘语群’更加标准?换句话说,客家除了共同的语言之外,是否还有共同的社会文化特征?”(第1001页)。现在想起来,我在靠近粤北地区的客家山村生活了两年半,除了学会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家话,对民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了解。原因之一,可能是劳格文所讲的历史因素,然后就是“文革”的“大批判”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民俗文化的复兴还远远没有到来。 与这本书的相遇,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高中毕业后在广东从化一个客家山村插队当知青的情景。刚到没几天,邻村的一位也是从广州来插队的老知青请我们吃饭。饭间谈到客家人的风俗习惯,他说这里的客家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独特的风俗了,除了讲客家话,就和流溪河边那些属于广府文化的村子没什么区别。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我在生活中最早接触到的民俗与语言相分离的问题。这本由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上、下,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虽然没有收入专门研究客家方言的文章,但是劳格文在“序二”中却谈到了当年那位老知青聊到的话题:“客家地区至少要分成四片,即闽西、赣南、粤东、粤北。我有一个很临时的想法,认为客家语言于元朝在闽赣交界区形成之后,很快就向粤东发展。从明中叶开始,这两个地区的移民把它带到粤北和整个赣南。因为粤北和赣南在清初之前不能算是客家,他们的文化与北方的赣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与客家的关系,更多地是同属于一个语群,而非族群”(第492页)。他在另一处更明确地谈到:“‘族群’这个适用于欧洲的概念在中国是否适用,或者用‘语群’更加标准?换句话说,客家除了共同的语言之外,是否还有共同的社会文化特征?”(第1001页)。现在想起来,我在靠近粤北地区的客家山村生活了两年半,除了学会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家话,对民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了解。原因之一,可能是劳格文所讲的历史因素,然后就是“文革”的“大批判”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民俗文化的复兴还远远没有到来。这本《客家传统社会》共收入二十二篇文章,上编主要是“民俗与经济”,下编是“宗族社会”,在这两者之间的连接主线就是“客家宗族社会的民俗与传统经济”(劳格文语)。实际上,这些文章是从劳格文主编的多达十一册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中选出来的,现在买这本书还附有这十一册书的电子版光盘。“本书的最大特点,也可能是学术界出版物中首次见到的,就是这些文章大部分并不是学者们写的,而是由当地人自己写的。在这些当地人中间,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现已去世。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前从未写过这类文章。……在我们与他们相识之后,曾安排了一个或数个学者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一起做田野调查,搜集资料”(劳格文“序一”)。劳格文对此写作方式的解释是:让创造本地历史的人写自己的历史;在“序二”中他继续说:“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应该到人口仍占90%以上的乡下:中国的历史可以在二十四史读到,而中国人民的历史,则必须通过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之类的工作才能了解到。”事实上,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由人民自己书写历史的模式,更不是过去那种“千秋功罪,我们评说”的“工农兵写作小组”加上“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模式。对这个问题,董晓萍在为本书所写的后记《传统社会与民俗社会》中,以“本地人化”这个概念做了很好的解释:所谓“本地人化”就是指在传统社会众多的内部成员中,选择最适合的本地合作者,通过观察他们与传统社会的联系的深度,对他们培训,唤醒他们的民俗意识,要求他们以传统经济、宗教、家族和节日作为出口,参加调查和写作。这种工作方式由于符合对方的认识习惯和表达可能性,也能很快被接受,民俗社会史料的记录和表达因此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种“本地人化”具有自己的人员选择标准:传统经济的知情者、宗教社团的内部人、撰修族谱的当事人、熟悉本地风俗习惯的人(第992-998页)。 这种“本地人化”的工作方式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早在1980年左右,我在历史系就读,学习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老师安排我们去粤西的信宜县钱排镇的山区,调查一支据称是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起义军的历史资料,那支农民武装的头领叫凌十八。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当地公社党委介绍知情的老农民,我们翻山越岭去一个一个地访谈,有些史料如起义的路线、农民军中流行的民谣等,都是请他们中有点文化的人写下来的。当然,在当时的农民起义理论的引领下,我们着重唤醒他们的记忆的是关于地主剥削、凌十八的反抗精神、农民军英勇战斗的情景等。后来还把我们整理的资料编印出版了一本《凌十八农民起义军调查资料》(我手头已无书,记得大约是这个书名),那种文字和内容的确与文化宣传部门撰写的“农民革命斗争史”之类的文献很不相同。 当然,这套书或者说劳格文所带领的这个研究项目,还有远比写作方式更深刻的民俗学研究意义。大约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俗学研究者就趋向于把“民俗”(Folklore)拓展为“俗民生活”(Folklife)的研究,即把传统的习俗行为、传统的物质文化和口头传统一起作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且在对传统的民俗进行研究的同时也研究当代民俗(参见J. H. 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第1页,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劳格文的研究项目和方法则比这种拓展走得更远、更踏实,他发现从传统社会的崇拜到传统社会的经济,民俗所扮演角色既是重要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便逐步扩大到我们所称的‘民俗社会',即’被民俗所规定了的社会‘各方面”(第491页)。关于“民俗社会”这个概念的解释和学术框架的建立,是劳格文和他的同事的重要工作;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和整个学术表述并非是颠覆性的,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在“民俗社会”的概念中,过去人们容易笼统而谈的“客家文化”应该被看作是具有多样性的地方文化的综合体。中国文化就是由地方文化拼接而成的“一个很大的文化拼图”.当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呼吁应该正视“中国”概念下的民族差异、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认为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见其《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劳格文等人的客家“民俗社会”研究正印证了这种观点。在劳格文附在本书末尾的论文《词汇的问题或我们应该如何讨论中国民间宗教》中,他提出应该保留“民间宗教”这个概念并证明其独立性,“以便使’中国宗教‘一词变得有意义”(第955页),也是基于同样的学术意识。  在当代民俗学研究中,如何使考察与描述向深度阐释发展,使文本的意义真正呈现出来,这就是除了田野民俗考察以外必须进行的文本研究。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的论文集《民俗解析》(卢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正好提供了一个与劳格文等学者的田野工作相对应的文本分析工作的范本。邓迪斯自称为“图书馆民俗学家”,因为他注重的是文本分析研究,尤其是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收入书中的《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通过对精神分析学史和民俗学史相互交叉影响的论证,说明两者的互补使研究受益很大;《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则更聚焦在收集民俗这个具体问题上,收集行为与资料提供人的关系其实在劳格文的研究项目中也是深受关注的。邓迪斯在为中译本撰写的“序”中指出,“民俗(包括中国民俗)包含许多幻想的材料,而幻想就需要对心理因素给以一定的关注。是否存在着对中国民俗的深层心理学研究呢?如果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第2页)看来,在客家人的“民俗社会”框架中还有待发展出“民俗心理”这一个心灵上的神经脉络。 在当代民俗学研究中,如何使考察与描述向深度阐释发展,使文本的意义真正呈现出来,这就是除了田野民俗考察以外必须进行的文本研究。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的论文集《民俗解析》(卢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正好提供了一个与劳格文等学者的田野工作相对应的文本分析工作的范本。邓迪斯自称为“图书馆民俗学家”,因为他注重的是文本分析研究,尤其是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收入书中的《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通过对精神分析学史和民俗学史相互交叉影响的论证,说明两者的互补使研究受益很大;《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则更聚焦在收集民俗这个具体问题上,收集行为与资料提供人的关系其实在劳格文的研究项目中也是深受关注的。邓迪斯在为中译本撰写的“序”中指出,“民俗(包括中国民俗)包含许多幻想的材料,而幻想就需要对心理因素给以一定的关注。是否存在着对中国民俗的深层心理学研究呢?如果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第2页)看来,在客家人的“民俗社会”框架中还有待发展出“民俗心理”这一个心灵上的神经脉络。(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