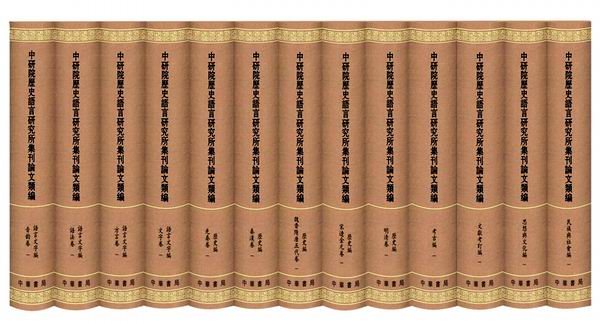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 分为语言文字编、历史编、考古编、文献考订编、思想文化编、民族与社会编等6编,共50册 如果要了解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发生、发展,尤其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可绕过。该刊创办于1928年,从广州、北平、李庄到南京,历经战乱,未有中辍,1949年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至今,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极为少见; 该刊依托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是陈寅恪、李济等学术大师的重要成果的首发之地,积累了崇高的学术声誉;该刊是中文世界中,极少数收入国际上权威的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的学术期刊,被国际学界所推重……不过1949年以后,《集刊》移师台湾,内地就很难见到,内地各大图书馆甚至搜罗不到一套完整的《集刊》。中华书局在1987年曾影印出版过1949年以前的《集刊》,但1949年以后的《集刊》,身处内地的学者并不容易看到,也无从利用。日前,中华书局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将1928年到2000年全部200多期集刊所刊文章全部按照现代学术分科,重新编排,影印出版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使内地学界可以方便地使用《集刊》这一学术宝库了。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的出版得到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当时担任所长的王汎森先生在这一大型出版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为此,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对王先生进行了采访。 读书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在内地出版,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您对这个出版工程得以顺利实施有什么感想? 王汎森:长年以来中国内地许多学者、学术单位都抱怨读不到史语所集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部分,中华书局翻印过一次,一九四九年以后六十年的《集刊》较难读到。过去购买不方便,还有价钱方面的考虑,对许多想读《集刊》的人是很困扰的。 因为史语所是一个将许多学科:历史、考古、古文字、人类学、语言学等合一的研究所,所以《集刊》的文章门类很多。老实说,如果手上没有一本分类目录,是不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文章的,而“分类目录”从未有人编过。 中华书局提议要印“类编”,将同类文章辑在一起,这当然是方便参阅,同时也使个人有能力就其专业相关的那几册加以购藏,用意良善。 我认为将来如果有机会,照《集刊》的原样一期出版一次。 读书报:《集刊》在中国人文学界以及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您觉得《集刊》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王汎森:《集刊》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一时不易说清楚。首先,史语所是中国近代新学术的开山,而《集刊》是它的机关刊物,代表的是这一大群卓越的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绩。史语所能不间断地努力超过八十年,几乎每一代都有出色人物,《集刊》存在八十年的时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都是不易见到的。 另外,史语所及《集刊》始终与中、外学术界的顶尖学者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点在《集刊》中也有所反映。 据我亲自参与编务的这些年的观察,《集刊》的作业过程大体上非常严格、非常谨严,参与《集刊》编务的研究同仁常常抱怨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我也提醒大家,史语所除了《集刊》之外,还负责英文的国际知名期刊AsiaMajor,中文的还有《新史学》及《古今论衡》,过去几位同仁还负责《大陆杂志》(后来停刊),所以工作量是很大的。 读书报:请介绍一下目前《集刊》的一些情况:《集刊》行政隶属如何?每年出版几期?每期发行量多大?在内地及欧美的订户占多大比例? 王汎森:《集刊》行政隶属是史语所的编委会。史语所有一个编委会,负责全所的出版品。史语所的出版品中除了AsiaMajor这个英文刊物、“历史文物陈列馆”的出版品或特殊性出版品外,其他的所内出版物都要到这个编委会来报告、讨论、通过。 目前编委会由三群人构成,同仁选出的编委、由主管同仁担任的当然编委、所外专家。 《集刊》每期大约印一千本。可能是因为汇兑上的困难,内地没有订户,但有七八十个长期交换的单位,欧美、日本等地有一百个左右的长期订阅或交换的学术单位。学术刊物与畅销书不一样,印量通常不大,发挥影响力也不在一时。 读书报:《集刊》采取怎样的评审制度?《集刊》在维持、提高学术质量方面有哪些措施? 王汎森:文章收到后,常委会开会推荐一串审查名单,照名单送至少两位审查。如果一正一负,则送第三位。在编委会中,针对每一篇文章还有一位执行编辑,负责通读全文并与审查意见作比较。最后,文章必须经全体编委共识才能印行,有时候甚至还动用投票。 这个形式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早期我刚进所时,《集刊》似乎是陈槃老先生负责的。槃老在通读每篇文稿之后批下数字“可刊”、“不可刊”或写“读后记”。有时“读后记”太长了,还成为单篇文章发表。槃老年纪很大之后较少到所上班,我有一位同事曾经担任编委会秘书,常常到他家记录他的批示。后来似乎也有同仁中某院士为了审查意见太过严苛,要求院士的文章免审,但是这个提议或者没有通过、或者通过之后只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是一律要审、一律公平。某任所长的文章就在他任内被退,我也曾撤过稿。 此外,编辑作业过程也非常严。现在编委会的工作人员真是“心细如发”,我不时碰到有人抱怨他们太过挑剔,但是也有人大感佩服。 读书报:历史上,《集刊》曾有一期刊用一个作者多篇文章,乃至由一个作者“包圆儿”,于是出现“陈寅恪专号”、“王叔珉专号”的情形,这在当今的期刊界是不可想象的。 王汎森:《集刊》早期确实有一期里面多篇陈寅恪先生文章的情形,我粗算了一下,陈先生在《集刊》发表过六十几篇文章。近几十年来在台湾的学术期刊变化很大,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二十世纪初叶几个重要汉学刊物上,都有“一人通包”的现象。我印象中伯希和刊于《通报》上的大、小文章恐怕有几百篇,高本汉在他自己办的《远东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有六十多篇,据他的学生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书中统计,共达三千五百多页。早期的刊物往往是专人负责,那个刊物“成也由我,败也由我”,个人色彩比较浓,有时候虽然不尽严谨,但通常比较能见精神。这种情形完全不可能再出现,而且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 近十几年来,台湾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报受美国学术刊物及学术指标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台湾也建立了两种指标,想要进入这两个指标的刊物,从编委会的组成、论文格式的统一、内外稿的比例……都规定得非常仔细。在这种规范下,恐怕连一期之内出现同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都是不允许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