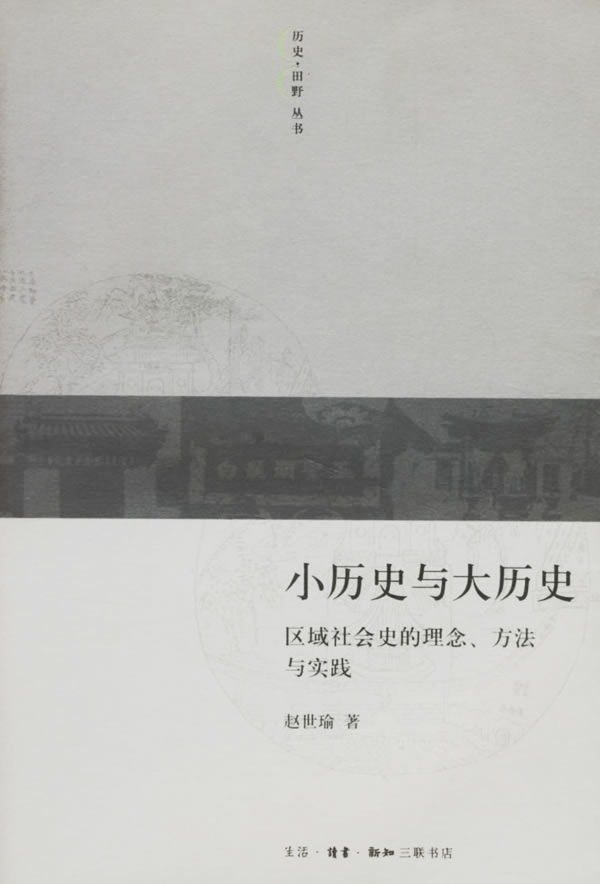 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出版后,陆续又写成一些文章,在这里结集呈现给读者。在我自己看来,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已经有些不同于前书,所以才有结集成书的理由。在出版过程中,我又陆续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章,于是便可以在书出版后拿出来亮相,作为下一步工作的起点。 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出版后,陆续又写成一些文章,在这里结集呈现给读者。在我自己看来,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已经有些不同于前书,所以才有结集成书的理由。在出版过程中,我又陆续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章,于是便可以在书出版后拿出来亮相,作为下一步工作的起点。这些年来,我们一群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在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献钩稽外,注意了田野调查。在10年前社会史的年会上被称为“田野派”的,如今似乎已经不再被目为异端,而且好像得到更多学术界同行、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注意。但是,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误会,比如一些朋友把我们所做的工作概括为“进村找庙”,关于这一点,本书有一些部分对此做了说明。 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主要是研究乡村,这当然也不错,因为对历史上的乡村,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尽管乡村人口在那时所占比例更大,乡村经济对国家更加重要。所以,过去我们有许多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但由于不了解乡村,所以对农民战争的理解就存在偏差。我们过去依赖的史料,也往往是由那些不太了解乡村、不太熟悉农民的人生产出来的,所以讲到一些重要的制度,往往只是概念上的,我们距离那个时代久了,就很难明白。比如里甲制度、赋役制度等等,通过乡村中找的碑刻、契约、族谱等等,就可能帮助我们理解。 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只研究乡村。本书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即使对北京这样的都城,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比如很多年前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和中国学者李世瑜研究过的保明寺和沟连宫廷与民间的西大乘教故事,就属于我们不熟悉的那部分生活。有篇博士论文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部、户部和内务府材料,讲述清东陵的故事,想想我们今天政府招标修个大工程,比如高速公路什么的,就可以想象,在两百多年的“陵工”里,会有多少精彩的故事,更不用说皇帝的多少次谒陵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了。还有篇博士论文专论清代北京的内城,我所希望藉此了解的是,旗人如何成为了“北京人”或者城市人?有了旗人的北京亦如何由此成为了一个不同的北京?这样的问题意识显然已不是传统的北京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要想回答好也不那么容易。回答得好,也许就可以与罗友枝(E.Rawski)、柯娇燕(P.K.Crossley)他们对话了。 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所谓“剩余的历史”,也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国外一些学者批评社会史研究的上述趋势,国内一些学者也颇有类似指责。的确,有相当一些“社会史”的研究者关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看来过于琐碎,但这并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这些研究主题本身的过错,而在与他们是否希望透过这些“细枝末节”去理解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还是只停留在津津乐道于描述它们。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所谓“剩余”还是“主体”究竟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假如历史学家们认为,只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才是历史的全部或者大部,而其他都是“剩余”呢?至于研究推向具体,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碎化”.首先,进行概括的基础,必然是大量个案研究,也许“碎化”是达到整合的必然阶段;其次,习惯于进行大而空洞、千篇一律的研究者,已经无力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于是“碎化”之讥可能变成一种逃避努力的托词。 想想今天的事情,我们就会很容易地认识到,对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去表达。如果是这样,那就一定是某种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力量,想方设法遮蔽了其他不同的声音,只留下有利于己的那一种。历史资料也是一样,我们的史学界长期使用一种材料,却毫不担心会被它们误导。我们走进田野,就是要去发现不同的声音,也即柯文所谓的“历史三调”,但可能远远不止“三调”.因此,以为我们只是去发现前人没有利用过的新材料,固然不错,但却过于狭隘。单纯使用碑刻或族谱资料,就和单纯使用档案或者正史资料一样,有其片面性,都可能被资料的创造者牵着鼻子走。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民间文献去理解正史或档案,是寻找不同材料或不同声音之间的差异,甚至,以某种材料去证明另种材料的真伪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一个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