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纪念,由丹麦政府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作为赞助人的Bikuben基金会特发起主办“2005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年”纪念活动,这个周年纪念活动从2005年4月2日(安徒生出生日 )起至12月6日止,届时将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35个国家加入这一丹麦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全球庆典。在世界文坛,能够享受如此高规格礼遇与庆典的作家又有几人? 安徒生是翱翔在世界文学蓝天的真正的“白天鹅”。然而,他也曾经是备受奚落与冷遇的“丑小鸭”。在安徒生辉煌成功的背后,还有着不幸与独特的另一面。解读安徒生的另一面,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某种更深的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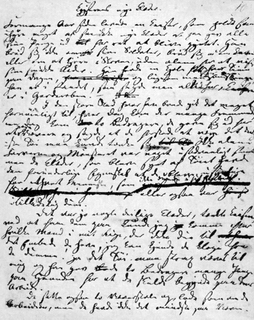 安徒生的手迹 濒于绝望的京城打工者 安徒生1805年4月2日出生于丹麦中部富恩岛奥登塞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个终生在作坊里操劳的鞋匠,喜爱文学,但一辈子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郁郁终生,因而把出人头地的期待寄托在安徒生身上。他的母亲比父亲年岁大,没有太丰富的经历,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慈善而勤劳的家庭妇女。穷困潦倒的父亲为了谋生,不得不去拿破仑军队当雇佣兵,但因身体不支,两年后就退伍回家,不久便去世了。为了生活,也为了还债,母亲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一天到晚躬着身子趴在小河边一块平坦的大石上为别人洗衣服。安徒生一生写过三部自传,他的小说、童话故事也大多有自传性质,如《即兴诗人》、《奥·多》、《幸运贝儿》等,尤其是《丑小鸭》。在这些作品中,安徒生如实地描写了他最熟悉的鞋匠、洗衣妇等下层百姓的生活,透过这些形象,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安徒生对命运的抗争与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少年心事当拿云。14岁那年,安徒生口袋里装着13个银毫子离家去了首都哥本哈根。一个从乡镇来的小小打工者,从此在陌生的都市开始了“京漂”生涯。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女神的钟爱驱使安徒生不断进出演艺圈。他曾学过舞蹈,16岁时与著名芭蕾舞演员安娜·玛格丽特·沙尔夫人同在一个舞剧中担任角色。他又在皇家歌剧院附属音乐学校学习,但后来因嗓子出了问题,被迫退学。他又想通过写作谋生,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但他写的诗歌与小说却不受赏识,非难与伤害深深地刺痛着他,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处境:“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将整个被巨浪冲走。我深深感到尖刀的刺伤,由于这时我已被人们抛弃,我濒于绝望了。我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冷嘲热讽,每每那些我所深爱的人也对我进行恶毒的抽打时,我就深感那些鞭子简直就是蝎尾鞭。” 年轻的京城打工者经受着巨大的生存考验与精神磨砺,但他最后终于战胜了命运。当他在童话世界找到了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才情与幻想天才的方式时,他的文学道路一下子变得如此坦荡开阔。 三次失败的恋情 然而,这位志存高远的京城打工者,虽然在文学之路上赢来了无数的鲜花与赞语,成了丹麦文坛的“成功人士”,但丘比特的爱神之箭却屡屡与他擦肩而过。贫寒的出身、丑陋的相貌令安徒生内心深处积下了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安徒生的第一位恋人是他同学的妹妹丽波尔·沃依特,安徒生爱她爱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坚信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爱得如此深切,而且认为丽波尔也是如此倾心于他。然而,丽波尔是一位富人的女儿,更使安徒生没有料到的是,丽波尔那时已经订婚了!1830年,25岁的安徒生与丽波尔的恋情以失败告终。 安徒生的第二位恋人是性格文静有着湛蓝眼睛和一个像竖琴的琴声那样动听的名字的姑娘露易莎·古林。为了向她坦露自己心里的每一个角落,安徒生开始动手写作自传《我的一生》。但是,露易莎的父母却坚决反对女儿的恋情,他们认为露易莎应该嫁给体面的、前程似锦的年轻律师林德。为了阻止安徒生的痴心妄想,古林一家很快操办了露易莎与林德的订婚礼。那是1833年1月,安徒生28岁。 安徒生的第三位恋人是被誉为“瑞典的夜莺”的歌星珍妮·琳德,她是斯德哥尔摩第一流的歌唱家,不但深深地吸引着安徒生,而且对安徒生的文学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透过珍妮·琳德,安徒生第一次意识到艺术的神圣,懂得了艺术家献身艺术必须忘掉自己。安徒生对珍妮·琳德的感情近乎痴迷,少年的梦想与中年的缠绵交织在一起,汇聚成一首汹涌澎湃的心灵之歌,使他写就了不朽的童话名作《夜莺》。在这篇童话中,安徒生把美丽的夜莺变成了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使者,增添了爱情的神秘与浪漫色彩。然而,在安徒生一生坎坷的情感历程中,他最钟爱的夜莺却拒绝了他的求婚。那一年,安徒生已过了“四十不惑”之年。孤寂的安徒生一生怀念着珍妮·琳德,每当想起她时,就会站在窗前反复吟咏海涅的诗《他们使我苦恼……》:“可是她,她最使我/苦恼、气愤和悲哀,/她从来对我没有恨,/也从来对我没有爱!” 或许是由于独身没有家累,或许是作家的职业喜欢在流动中获取灵感与幻想,或许是本性酷爱旅游,安徒生从14岁离开家乡以后,一生都走在路上,走在路上的生活使安徒生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行侠”。从1840年35岁以后的9年时间里,他曾做了30次国际旅行,他的足迹遍及欧洲各国,最远到过土耳其。安徒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希望有朝一日能到神秘的东方古国旅行,但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一直要等到20世纪初叶,安徒生这才有机会骑着《野天鹅》,与《卖火柴的小女孩》、《安琪儿》、《拇指姑娘》一起,来到中国进行“精神访问”。  安徒生童话在早期曾经倍受诋毁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考验,安徒生童话已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世界文学经典之作。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经典的产生、形成与共识是需要历史尺度、价值尺度、审美尺度一起来评判的,因而不少经典在当时并未为人所识甚至倍受诋毁。安徒生童话在早期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欧洲文学史告诉我们:丹麦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出现的诗歌雏形。中世纪晚期,丹麦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口耳相传语言通俗表达民声的民谣,流传至今还有六百多首。安徒生的创作灵感尤其是童话往往获益于早年听到过的民谣与民间故事,作品大量运用丹麦民间的日常口语,借鉴民间故事的形式,充满着浓郁的现实主义倾向与乡土气息;又由于童话的主体接受对象是少年儿童,因而他的作品自然又充满了童心童趣以及儿童般的想像与语言。与儿童的心相通,与自然的美相接,与民间的味相融,这是安徒生童话的显著特色。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他的作品在当年的丹麦文坛却遭到了否定、讽嘲与诋毁,认为是“不合语法”,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三流之作。虽然后来这样的歧见很快没有了市场,安徒生的作品不但赢得了孩子的喜欢,甚至包括丹麦国王与王后在内的无数大读者也迷恋上了安徒生童话,但是对安徒生童话的争议却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处于“革命与救亡”的中国,安徒生童话就曾遭到过十分尴尬甚至被否定的境地。当时曾有论者这样认为:“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实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这种看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全面肯定、推崇和接受形成鲜明对比。安徒生为什么在两个不同时期的中国会遭致如此不同的遭遇呢? 安徒生的当代争议 其实,对安徒生的“否定”在今天依然存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发表的署名文章《安徒生童话个别篇章在接受问题上的反文化倾向》一文认为,用反文化思想视角重估安徒生童话的文化意义,就会发现其中一些篇章隐含着反文化现象。作者着重剖析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两篇童话,得出的结论是:前者“带给人们的是违背现代社会价值原则的负面信息,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或许在他们的心灵中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它很容易误导人们的私欲极度膨胀,并诱导人们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进行暴力侵害”;而后者描写的“小克劳斯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反道德人物形象”,“在今天看来,小克劳斯的以恶报恶的行为和种种骗取钱财的计谋,是与工商业时代的公平、公正、依法维权、合法谋生的生存准则相违背的”。 进入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红尘万丈,价值多元、文化多样、信息爆炸的时代,安徒生童话以及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未成年人心灵的世界传统文学经典,究竟还有没有现代价值?《中华读书报》曾发表过两篇署名文章《不敢再读“格林童话”》《该不该读童话寓言》,就对此提出了看法。后者有这样一段十分扎眼的文字:“我听周围许多家长说,不要让孩子看这种童话寓言,因为这样的东西看多了,会把孩子心眼看傻,以后长大了上了社会只会被人欺负。你说,我要不小心培养出个窝囊废来,他这一辈子不就完了么?”而前者则大声疾呼要“救救孩子”,不要再让孩子读格林童话了。 正如一百个读者眼里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莱特,作为见仁见智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普世流传的经典名著,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与语境下,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评判与接受,这是正常的,这也是经典的生命与魅力之所在。当我们将视线移开笼罩在安徒生头上的耀眼光环,绕到他的背后,解读他成功人生的另一面,包括解读对他的童话世界的不同评价的另一面时,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立体的安徒生,他的成功与不幸,他的光荣与梦想,他的伟大与平庸,将会带给我们更多更深的思索。但是不论怎样,安徒生创造的文学世界特别是他的童话艺术世界,已经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个世界是如此丰富神奇,充满着诗与幻想,充满着爱与感动,充满着美与悲剧。童话大师安徒生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解读不完的童话,正如安徒生在自传的结语中所说的那样:“我一生到目前为止的经历,如今像一幅浓艳、美丽的油画展现在我面前,激励着我的信仰,甚至使我坚信好事从不幸中诞生,幸福从痛苦中产生。这是一首我所写不出来的思想无比深邃的诗。”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