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悦(1979年—),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古代罗马史研究。在《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世界宗教文化》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翻译《罗马世界》,合译《西塞罗传》、《探寻古罗马文明》,参与编著《西方古典著作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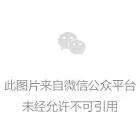 由治权到帝国——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 王 悦 编者按 现代西文中与帝国相关的所有词汇多出自同一渊源,即古罗马官员掌握的治权(imperium)。治权概念随行使范围的空间扩展而内涵延展,从罗马官员的权力到皇帝的权力,从罗马人民的权力到罗马国家的统治,从区域性的统治到对整个世界的统治。imperium词义的演变说明了罗马国家蓬勃的发展态势,帝国的成长与帝国观念的更新共同演进。罗马人在很长时间里体认的是一个权力帝国,这一权力帝国的基础在于对其他地区和族群行使治权。罗马人怀揣抱负,相信以军事手段制服对手才是罗马立国图强的最佳出路,这与自蒙森以降视罗马为防御性帝国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 ★ 关键词: imperium 权力 帝国 罗马扩张 罗马帝国不仅是古代西方世界统治疆域最大、延续时间最久的大帝国,更是后世西方人提振民族精神、壮大国家实力时常效仿的对象。从查理大帝到俄国沙皇,从近代的西班牙到19世纪末的英国,所有的欧洲帝国都不断从罗马帝国获取榜样的力量乃至词汇的力量。古罗马的许多词汇和象征成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宣示个人或党派权威、彰显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正因为近现代对帝国统治采取与古代颇为相似的表达,又因为这些表达词汇在近代以来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意义重大,论者多会有意无意地将古代和近代的帝国混为一谈,混淆古今帝国的独特性格。古今观念差别甚远,古今帝国分野极大,罗马帝国有专属于自己的帝国本质和历史变迁。 罗马帝国的建立,与传统上罗马帝制时代(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的划分无涉。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无非是在政体上完成了从隐蔽的君主制即元首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但帝国无关乎政体,判定是不是帝国与罗马是否确立起帝制没有多少关联,共和制也不是断定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不是帝国的理由。历史学家在谈罗马国家向帝国转型时,往往强调国家政体结构由共和而帝制的变迁,而实际上罗马在由皇帝当政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共和国时代的对外战争风起云涌,罗马人在对外战争中追逐国家安全与个人荣誉。战场在古代乃至近代世界永远是赢得荣耀的主要场合,战争最直接的受益者元老贵族,利用身为统治阶层的各种便利合法占有或非法侵占国家资财,又通过军功让个人声名显赫,为家族增光添彩。普罗大众投身战争,抵御外敌,他们也从国家的公众福利和公共设施中获益。罗马在共和国时代已经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帝国了。 在拉丁文中,帝国表述为imperium,而且围绕该词又产生了一系列与帝国相关的表述。这些表述的演变,恰好见证了罗马帝国的缔造过程,也反映了罗马人帝国观念的变化。因此,通过梳理这些表述的语义变迁,可以深刻理解置身其中的罗马人眼中的帝国样貌,有助于辨明罗马帝国的属性,也会对罗马“帝国主义”有更清晰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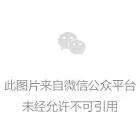 ★The Roman Empire in 117 AD. 1 imperium释义 现代西方语言中表达“帝国”的词汇多源自拉丁语imperium,可解作“治权、最高权力”。imperium的词根来自动词imperare,意即“指挥、命令”。imperium是罗马官员的至高权力,包括军事指挥权、解释和贯彻法律的权利等。按照古罗马文献传统记载,治权最早属于统治罗马的诸王,王的权力简称为治权。在最后一位王高傲者塔克文被驱逐后,这一权力转由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员行使。 罗马历史上曾握有治权的官员有执政官、拥有执政官权的军事长官(公元前445年—前367年)、大法官、独裁官和骑兵长官。治权按其词根的涵义“指挥、命令”,可以看作下命令、要求个人听从的权力,代表着国家在处理与个人关系中的绝对权威,被授予治权的官员代表着国家行使这一权力。后来,治权也由代行执政官和代行大法官等任期延长的官员执掌。他们在担任执政官和大法官的任期结束时被赋予新的使命,手中的治权也相应延长。罗马历史上拥有治权的还有获得特别指挥权的个人(privati cum imperio)以及一些领有专门使命的人士,如负责土地分配的委员会成员等。 原则上,治权至高无上,实际上受到的制约却越来越多。共和国初期,王被逐,由两名被称为“司法官”(praetor)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执政官取而代之,他们的权力因为同僚协议和任期一年的规定而受到制约。在民事领域,同一时间内仅一名执政官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另一名执政官的治权和占卜权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出面阻止同僚的行动时他的治权才发挥作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两名执政官的权力可能同时处于休眠状态,听命于一名独裁官。独裁官没有同僚,获得6个月内的治权,6个月在理论上正是一个作战周期的时长。上诉权也制约着官员的治权。根据《瓦莱利乌斯法》(lex Valeria,文献传统中记载此法曾于公元前509年、前449年和前300年多次颁行)的规定,对于官员的判决,公民有权上诉公民大会要求审判(provocatio),官员不经审判不得在罗马处决公民。也许颁行于公元前2世纪初的《波尔奇乌斯法》(lexPorcia)对《瓦莱利乌斯法》做了进一步延伸,公民的上诉权扩展到罗马之外,身居国外的罗马公民可以针对官员的死刑裁判进行上诉。另外,任期延长的代行官员在行使治权方面也受到明确的限制。他们的治权仅能在指定的战区或行省(provincia)内行使。如无特别批准,一旦步入罗马城界,其治权自动失效。代行官员的治权往往只在一年内有效,或者至其完成使命时终止。当然,也出现过授予几年治权的情况,但仅出现在共和国末年,传统的共和政体趋于瓦解之时。 帝制的开创者屋大维也拥有治权,他曾在公元前43年先后担任代行大法官和执政官,公元前42年—前33年间是“三头同盟”之一,公元前31年—前23年为执政官,从公元前27年起担任多个行省的代行执政官,这些身份都有治权作为坚强基石。公元前23年,他辞去执政官职务成为代行执政官。这时,代行执政官的治权转变为大治权,不仅可以在罗马城内行使,而且也囊括意大利。于是,代行官员的治权在罗马城界内自动失效的规定到此已经废止。在公元前27年、公元前8年、公元3年、公元13年已获得“奥古斯都”尊号的屋大维,屡次获得为期10年的治权;在公元前18年和公元前13年,他还获得为期5年的治权。也就是说,从公元前27年到奥古斯都辞世时止,他每一年都掌有治权,之前也几乎连年拥有治权。治权在实际上几乎成了奥古斯都一人的专属品,其他人的治权期限和实际权利实难望其项背。皇帝的权力源于治权,治权对皇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通过在实践中取消对治权的各种限制,皇帝确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 治权是古罗马政治、军事、司法领域最重要的概念。前文已经提及其囊括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和司法裁判权,涵盖广泛。古罗马史家多把共和国官员的治权看作王权的延续,不可分割的整体,官员在某一领域的职权只是这一绝对权力的具体体现。而现代学者则多把国王的治权和授予官员的权力截然分开,认为后者受到诸多制约,与国王的权力存在着本质区别。譬如在德拉蒙德(A. Drummond)看来,古代作家之所以把共和国官员的治权看作王权的延续,不过是受到希腊政治理论的影响,急于强调罗马政治发展的连续性而已。然而,不论官员的权力承继自王权,还是官员的权力远不及王权,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假定治权从一开始便完整无缺、至高无上。他认为,并不存在如此完整统一的治权,所谓明确定义的治权概念完全出于人们的想象,也许直到晚后,当官员离任后治权延长而成为代行官员时,治权才首先被清楚认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 另一位学者贝克(H. Beck)对治权的属性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对治权的完整性是因还是果没有直接表明立场,反而独辟蹊径地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他指出,尽管共和国官员增多似乎使治权的威力较比王权大打折扣,但官职的增加反而强化了治权的普遍性。治权从完全的国王权力演变成为罗马共和国公民所普遍接受的权力坐标,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具有等级性的共和国政治制度。从前有学者把治权看作从最初完整统一的权力分解出的各项权力,抑或看作随时间发展不断充实的统治权,在他看来,虽然这两种思路并不相容,但其价值在于两者都相信治权是存在于共和制度中最核心的一种衡量力量。各个官职是否拥有治权,或者所拥有的治权权限高低,决定了官员的上下级关系。治权的不断演变塑造了共和国的权力机制,共和国的政治稳固与发展崛起有赖于这一权力机制的良好运作,罗马公民也普遍接受治权对国家安定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到帝国早期的文献资料中,对治权至高无上性的称颂及理想或现实中治权的描绘屡见不鲜。治权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原因之一在于其神圣性。治权在实践中是元老院授予官员的权力,宗教上则是神赋予的权力。罗马人认为治权来源久远。在传说中,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建城之日,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进行占卜,由天神朱庇特放送12只秃鹫的鸟占卜象确认了他的权力,此后他的权力在王政时代历任国王间传承。治权与占卜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国事占卜”(auspicia publica)的传统一脉相承,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行动均需占卜神意,请示神的意旨、解释神的征兆成为了国王执掌权力以及共和国官员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 治权贯穿于罗马历史发展的始终,从罗马建城时起便生生不息,它也成为罗马最为核心的力量。治权至高无上、无所不容,行使治权者则大权在握、发号施令。但诸如一年任期制、同僚协议制和对公民上诉权的保护等措施规定,使得共和国官员的治权必须服膺于共和政制的结构框架,即便拥有继承自罗马王权的权力,作为罗马的公职人员也必须服务于国家和人民。随着罗马国内国外形势的日益复杂,管理事务和统兵之责日益增多,增设新官职在所难免,治权在重要的职能部门中广泛分布,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到帝国早期元首制确立之后,也从未切断与共和传统之间的联系,治权的重要地位无可替代,于是皇帝选择打破对治权的各种约束,从根本上确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 治权伴随着罗马历史的变迁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演进呈现出共和期与帝国期两分的特征,折射出两个时代的本质区别。治权的权限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治权在罗马国家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治权观念深入人心,每个罗马人都深知治权重大而神圣,拥有治权意味着可以在国家的军政舞台上大展拳脚,怀揣仕途抱负的罗马人无不把担任握有治权的高级官员作为奋斗目标。拥有治权并担任高级官职是个人乃至其家族的无上荣耀,是个人积累政治资本的绝好机会。拥有治权的军事将领驰骋沙场、建立战功,也为罗马开疆拓土、建立广阔帝国开辟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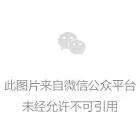 ★The Augustus of Prima Porta. ★The Augustus of Prima Porta. 2 帝国观念的衍生 imperium本指官员所行使的权力,而由官员行使权力的空间范畴视之,它又具有了地域空间的内涵,所反映的是治权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实践。古代文献提及治权时常加一限定语“domimilitiaeque”(国内的和战场的),将治权分为国内治权和军事治权两类。在罗马城内行国内治权,在罗马城外行军事治权,由此可见治权在民事领域与军事领域并置的特点。此即治权在空间上最基本的对分。然而,这种将治权按行使区域一分为二的传统做法近来受到某些学者的挑战。德罗古拉(Fred K. Drogula)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治权并不存在于城界之内,没有国内治权一说,治权纯属外向型的军权,军事性是治权的惟一属性。这一解释凸显了治权在罗马崛起中释放的军事能量,在实践中统兵权是治权最重要的体现。衔领治权的官员在经库里亚权力法批准后,穿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成为统帅。随着与外邦战事的展开,也治权行于国外。统兵权与将领停驻地之间建立起关联是治权在实践中的突出特征,甚至在广义上成为罗马号令世界的反映。 自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跨出意大利半岛,通过战争在海外拓展霸权,官员下达命令和使人服从的治权也扩展到海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蓬勃发展并最终确立,在该时期imperium的用法也经历变化,涵义延展,出现与之联用的新词汇。imperium的词义随历史发展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是本义,即罗马官员的权力,该词的基本用法保持不变,表示官员权力的内涵一直沿用到帝国时代;再则是新衍生出的空间涵义——imperium行使的空间即为罗马帝国。 追溯帝国一词的用法,需参照官方文献以及修辞学读本中该词的使用情况。在实际使用中,该词还出现在异族和文学的语境中,尚有其他内涵。在这里,本文仅就对罗马崛起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内涵加以讨论。虽然imperium涵义演变的情况颇为复杂,既有意涵上的差别,也有时间上的交错,但从对其各类用法的梳理中可以获知其涵义演变的大体趋向。 Imperium的空间内涵出现于海外行使治权之后。罗马帝国的官方表述首见于公元前2世纪60年代罗马与色雷斯的马罗涅亚(Maronea)签订的条约,条约文本为希腊文,上面提到了“罗马人和他们治下的人”;这一概念的拉丁语表述见于罗马与卡拉提斯(Callatis)有关黑海的条约,“罗马人民和在他们治下的人民”([... Poplo Rom] anoquei[ve] sub inperio [eiuserunt ...])。这些异族被置于罗马的治权之下,意味着罗马实现了对相关地区的统治。公元前167年,在一次元老院演讲中,老加图为罗马与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交战时罗德岛人的行为辩解,他称罗德岛人不想见到罗马人完全打败佩尔修斯,因为害怕“处在我们独一无二的治权之下(sub solo imperionostro)”。在这里,“我们的治权”指的是罗马人民的权力,此处罗马人民的权力等同于罗马的统治,因为罗马可以简称为“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意为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罗马人民的权力也就可以理解为罗马国家的权力或罗马国家的统治。鉴于治权是罗马国家要求罗马人民服从的权力,罗马人民的权力也便可以看成罗马人民要求外族服从的权力,即对外族的统治权。 前文提及imperium已具有“罗马人民的权力”的内涵,但“罗马人民”与“治权”两个拉丁单词连用的短语imperium populi Romani,直到公元前1世纪初才在拉丁文献中出现,首见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修辞学作品中。在这篇托名西塞罗所作的修辞学作品中提到:“谁会相信,有人会如此愚蠢,打算不依靠军队来挑战罗马人民的权力?”此处“罗马人民的权力”仍遵循前文提及的用法,指罗马对外族的统治权,挑战罗马人民的权力意味着挑战罗马的统治。另外,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划时代的用法,不仅把罗马人民的权力指向其他地域和民族,而且涵盖整个世界:“所有族群、国王、国家一方面出于武力强迫、一方面出于自愿,都接受罗马对整个世界的统治,当世界或被罗马的军队或被罗马的宽厚征服时,让人不大相信的是,有人会以孱弱之力取而代之?”罗马依恃军威和外交政策所向披靡,所有国家都服膺于罗马,罗马的统治不限于一方之地,广纳整个世界。当然,这里提到的“世界”是指罗马人居住其间的整个地中海世界。西塞罗在另一段演说词中同样表达出罗马统治世界的态势。他提到了独裁官苏拉,称苏拉是共和国惟一的统治者,统治着全世界,并以法律巩固了通过战争恢复的伟大权力。在西塞罗的演说词里,有大量把罗马人民的权力延伸到全世界的表达。这些用法绝大多数属于抽象意义上的,而西塞罗惟一一处可能是对罗马人民的权力扩大到世界之边的实指,见于《论共和国》篇末的西庇阿之梦。在梦境中,小西庇阿被已故的养祖父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引领上天,在繁星苍穹下,他既欣喜又不安。星空广瀚、地球渺小,他为罗马的统治(imperium nostri,直译为“我们的统治”)感到遗憾,因为那触碰到的只是世界的一小块。这无疑暗示了罗马人对统治广阔世界的无限憧憬。这种宣称罗马统治世界的表达方式在公元前1世纪首次出现,此时对imperium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官员的权力抑或罗马人民的权力,而是罗马对世界的统治和世界性帝国。在共和国末叶,关于罗马的权力无远弗届的认识已经司空见惯。 现今可见的资料呈现出imperium语义发展的整体趋势: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该词在官方文本中最主要的用法一直是赋予官员的权力;到公元前1世纪,该词的涵义更为宽泛灵活,官员权力之意仍广为使用,新见短语imperium populi Romani也用以指代罗马人民对他者的权力和统治,这种权力被看成世界性的权力,可以控制整个世界,近似于orbisterrarum(意为世界)的用法。尽管imperium的词义演变仍表现在权力扩展上,但已有空间意义的构想,认为罗马的权力无远弗届,即将罗马想象为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帝国。此时imperium的领土意涵尚不明确,但随着罗马世界的扩展和时人对这个世界认识的加深,imperium增添了某种“帝国”的涵义。这一涵义后来也愈发确切,逐渐具有了领土国家的意味,最高权力演变为权力运行的地域,成了领土意义上的帝国。 罗马史家李维叙述称,“公元前191年在亚细亚,不久后将发生安条克与罗马人在陆上和海上的战争,要么正在寻求统治世界的罗马人失手,要么安条克失去自己的王国”。另一处,“路奇乌斯·西庇阿曾征服世上最富庶的王国,将罗马人民的权力扩展到陆地最远的边际”。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罗马已经放眼世界,寻求世界性的统治。这也是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文献中对罗马统治的普遍用法。李维在另一处还记载,“安条克致信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信中抱怨称,罗马人正在前来亚细亚的途中,他们是来摧毁所有的王国,以便世上除了罗马帝国(Romanum imperium),其他帝国荡然无存”。此处,Romanum imperium的地域意义十分明确,因此理解为罗马帝国更为妥当。李维指出,罗马已经有了统治世界的抱负,愿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世界之边,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所有帝国,唯我独尊。生活在共和与帝制之交的李维虽在追述古人言论,反映的却是同时代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人们的普遍想法。因此,可以说,最迟从公元1世纪起imperium Romanum已由罗马的权力引申为罗马的帝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指称。老普林尼和塔西佗的著作都使用了imperium Romanum一词。老普林尼在描述美索不达米亚时说:“特巴塔(Thebata)和从前一样仍在原位,这个地方也同样标示出在庞培领导之下罗马帝国的(Romani imperi)边界”。塔西佗称“巴塔维人(Batavi)曾是卡提人(Chatti)的一个部落,他们由于自身发展渡过河,那将使他们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pars Romani imperii)”。这两处,imperium指代的无疑是领土意义上的帝国。 帝制时代前后,在罗马人心目中,罗马的统治区域无边无际。公元前75年,罗马的钱币已铸上权杖、地球、花环和舵的图像,象征罗马的权力散布到全世界的陆地与海洋,象征着没有边界的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掌权时,“帝国”(imperium)的概念已与“世界”(orbis terrarum)的所指别无二致。1世纪的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内加写道:“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两个国家,其中之一是广阔而真正公众的国家,神与人被怀抱其中,我们看不到它的这一端,也看不到那一端,但可以用太阳来丈量我们公民的边际。” 2世纪,皇帝安敦尼·庇护接受“全世界的主人”(dominus totius orbis)的徽号,鼎盛时期的罗马延续着罗马人主宰世界的梦想。 罗马形成帝国的领土空间概念较晚,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罗马人的思维方式与希腊人一样,多谈民族,少谈地区。这种思考方式使得他们对权力帝国的理解早于对领土帝国的理解。相较于建立领土意义上的帝国,使外族外民受制于罗马的权力,服从于罗马的统治,才是罗马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有时候,在迻译拉丁文的过程中,对民族而非地域的考量往往会被忽略,用一个地名取代一个民族的名称,统治一个民族被译作统治一个地区,实际上在微妙处曲解了古人思考国家及国际关系的方式。比如罗马统治希腊人截然不同于罗马统治希腊,前者表示希腊人对罗马人的服从关系,后者则加入了不见于早期拉丁语的领土和地理纬度。 在imperium词意拓展的过程中,还涉及一个重要的词汇provincia,英文中行省(province)一词由此而来。provincia起初为元老院分配给下年度掌握治权者的职责。由元老院分配官员职责的惯例一直延续到奥古斯都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初,provincia已具有了地理上的隐含意义,指代指挥官行使治权的作战区域,即战时官员行使强制性治权的地区,此后又演变为帝国海外领地的行政单位——行省。从官员的职责到行政制度,provincia也同样经历了类似imperium的涵义变迁。provincia的本意不是治理国家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对拥有治权者职责的界定。元老院往往将据信对罗马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连年指定为战区,指派拥有治权的官员赴任。元老院在战区的择定上具有主动权,在每个任职年的年初指定战区,分派握有治权的官员。倘若元老院确有拓展边疆的意图,则焦点在于扩展个人的治权及所在战场或行省的治权行使上。在连年作为战区或是罗马的权力想要在此牢固扎根、常态化管理的地方,渐渐设立起管理政府和行省总督,行省的建制渐趋成熟。 与imperium相关的各个词义有时叠加,有时混用,但这些词义都在不断丰富和细化,新衍生出的词义没有取代古老的涵义,各个词义杂糅并存。从罗马官员的权力到皇帝的权力,从罗马人民的权力到国家的统治权,从对其他民族和地域的统治到对整个世界的统治,imperium词义的演变说明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大展拳脚的蓬勃态势,这种扩张态势使罗马人的国家观念不断更新。不论称霸地中海所催生的帝国观念,还是罗马早在建立之初就具有尚武好胜的民族雄心,帝国的不断成长与帝国观念的更新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使罗马人怀揣世界性抱负不断扩张帝国。从权力到统治,再到统治的地域,imperium词义的变迁见证了罗马的帝国成长,更激发着罗马人向远方进发。有历史进程中的罗马帝国,也有罗马人想象中的帝国,二者共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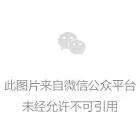 ★ An aureus of Antoninus Pius, 145 AD. ★ An aureus of Antoninus Pius, 145 AD.(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