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85年的小册子《蒙田》到今年出版的《图像证史》,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有9本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这9本书展现了“新文化史旗手”的学术经历和个人视野。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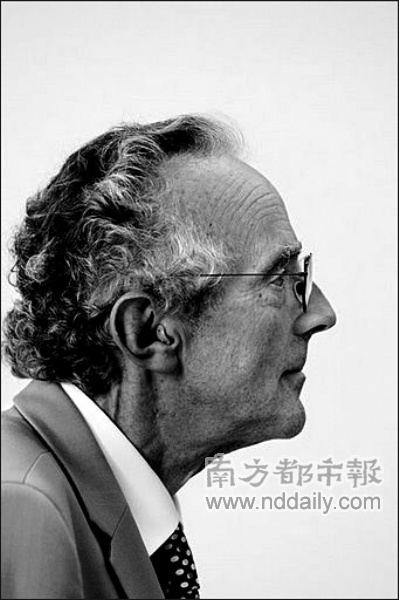 | | 彼得·伯克(PeterBurk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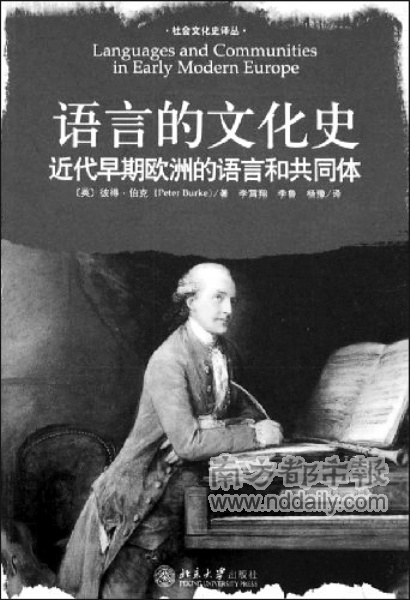 | | | | | | 《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李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28.00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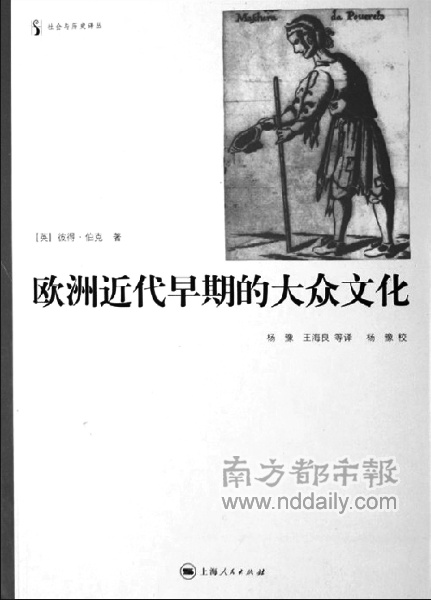 | | | |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6.00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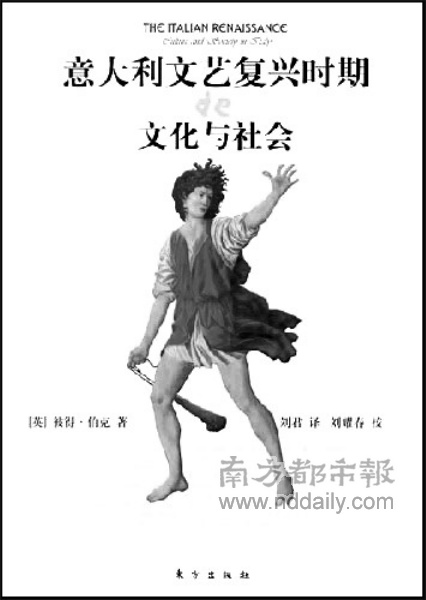 | | |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9.80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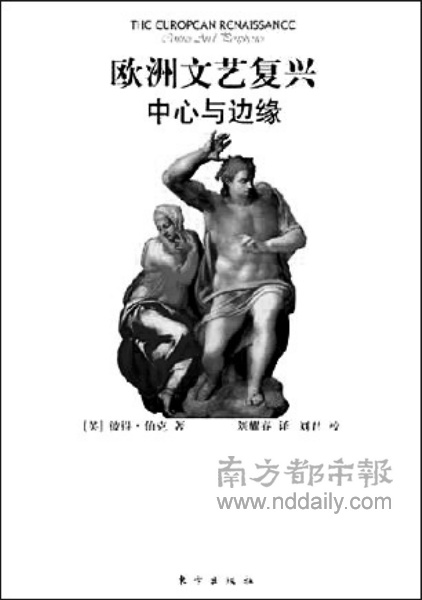 | | | | 《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刘耀春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5.90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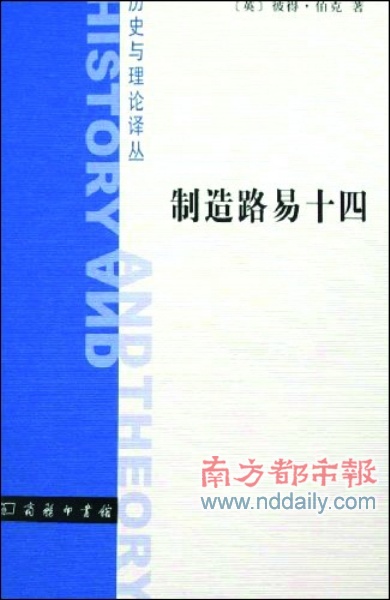 | | | | 《制造路易十四》,赫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版,29.00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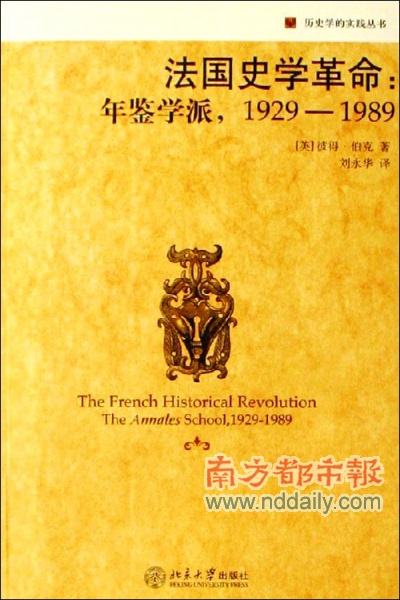 | | | |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20.00元。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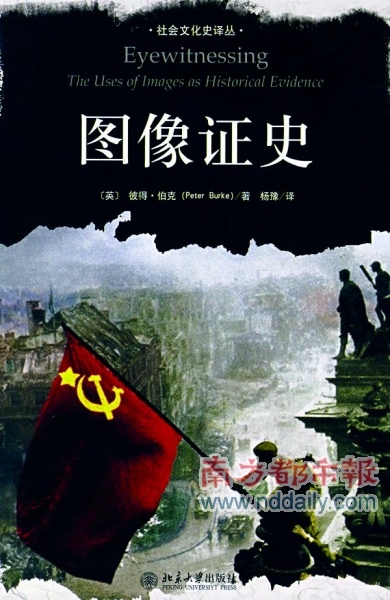 | | 《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33.00元。 |
| | |
彼得·伯克(PeterBurke),1937年生于爱尔兰。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伯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其学术生涯,此后一直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他著述丰赡,出版专著数十种,发表了大量论文,研究范围涉及欧洲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欧洲近代大众文化,欧洲近代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和语言史,曾参与著述《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伯克的学术视野开阔,其历史文化史研究和社会史理论旁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哲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批判理论、文化理论、女权理论等等领域。
1985年1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其中有伯克撰写的一本小册子《蒙田》。2001年以后,伯克著作的中译本陆续出版,计有《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制造路易十四》(商务印书馆,2007年)、《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知识社会史:从古滕堡到狄德罗》(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大众传播史》(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尚未译成中文的伯克著作:《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17世纪荷兰的大众文化》、《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维科》、《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解释》(论文集)、《交谈的艺术》、《安特卫普:从比较的视角看一个大都会》、《廷巨的命运:欧洲人对卡斯提寥内的〈廷巨论〉的接受》、《多元的文化史》(论文集)、《何为文化史?》、《近代早期荷兰语的社会史》等。据悉,伯克的系列作品将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社会文化史译丛”和“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中陆续推出。
《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一书刘耀春的“中译序”,有伯克著作的详细书目(未列论文)。
历史学的魅力
1944年6月16日,因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逮捕的法国“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被枪杀于德军集中营。这位令人敬佩的历史学家赍志以殁,遗下一部未及完成、可视为其一生史学思想结晶的手稿《历史学家的技艺》,由其好友和同事、另一位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整理成书出版。布洛赫说,家国兴亡,感时伤世,乃撰写这本小书,“聊以排遣心中的忧愤”。国事蜩螗,下笔之际固然别有寄托,但令布洛赫萦绕于心的,却是一个关乎史学家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在布洛赫就义前几年,他的儿子曾经向父亲提问:“历史有什么用?”身为著名历史学家、早已凭《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这两部力作奠定其史学巨擘之地位的布洛赫,竟然未能给儿子以圆满的答案。自此至被捕前,布洛赫都在不断地思考这个“切中了要害”的重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看似玄奥实则极严肃的问题,它针对的是“史学存在的理由”。于是,布洛赫结合自己的治史经验和史学理念,写了这本言简意赅的书,为历史学辩护,为“史学存在的理由”辩护,亦试图为像他儿子那样的许多对“历史”感到疑惑的读者进行解答。
布洛赫认为,历史并非只是枯燥的叙述,它也应该具有“娱乐的价值”,具有“活泼而和谐的韵味”,以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历史学家要“为了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而努力”———“历史学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布洛赫说,在本质上,历史学可称为“(处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其中蕴含了史学的“技艺和法则”。布洛赫阐述他的历史美学观:“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科学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伟大的莱布尼兹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在历史中)探幽索奇后的喜悦。……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未免太荒谬了。”(以上引文见《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充满诗意的历史学,才是富有魅力的历史学。布洛赫的传世之作《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出版)、论文《欧洲中世纪的“发明”》和《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见《年鉴史学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都极具卓见才情,是渊博的学识与诗意的完美结合。
《历史学家的技艺》只有数万字篇幅,它或许始终未能对“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给出圆满的答案,或者说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布洛赫的“逆溯历史”的整体史观,即“从现在开始退行到过去”的一种研究方法,对后世治史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费弗尔曾这样表述:“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科学,关于现在的科学。”柯林武德则谓:“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布洛赫强调人类的历史不能割断,今昔之间不可分离,此亦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学观。保罗。利科说:“把不同时段放在一起,正是法国史学界(引者按:此处特指年鉴学派)对历史认识论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4月)
伯克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伯克自言“在社会理论方面涉猎甚广”,《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是他积多年治史经验,阐述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发展的理论著述。他认为所谓“社会理论”,应理解为涵盖“文化理论”,他承认他在此书中对历史学的观察和理论分析,是借镜年鉴学派第二代学术首领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念;所谓整体史,“不是对历史作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强调在人类的不同探求领域之间的联系”。
近现代社会的愈趋复杂性,影响了社会理论的变化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会愈来愈明显,历史学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学,反之,社会学亦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学。伯克在此书第一章“理论家和历史学”中,对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近现代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发展,有独到的分析。他说:在关注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显然是学术上的近邻,“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的发展和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而事实上,历史学和社会学却并非和睦相处的邻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挑剔对方的缺点,它们之间的对话,就像布罗代尔所形容的,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但在十八世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并没有争吵,因为那时社会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身份,往往模糊不清。所以,对孟德斯鸠、约翰。穆勒、亚当。斯密、伏尔泰、吉本、马尔萨斯等人的“学术身份”的界定,后来就引起不同学科之间的争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都想把他们视为本学科的“开山鼻祖”。伯克认为,将上述学者称作“社会理论家”,可能会更妥帖,因为“他们系统探讨的是所谓的‘市民社会’”。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未尝不是“社会的哲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既是社会史,又是经济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是政治史,也是社会史;伏尔泰的《风俗论》,称之为“历史哲学”,不亦宜乎!
十九世纪后期,奉行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兰克学派”异军突起,在史料、方法和观念上掀起一场“历史学革命”;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史学家们的著述多聚焦于国家,社会史渐渐让位于政治史。伯克指出:“这种对社会学的拒绝,在十九世纪晚期一些哲学家如狄尔泰的著作中表达得尤其明确……”二十世纪初,克罗齐亦持类似狄尔泰的观点,认为“社会学纯粹是伪科学”。然而,狄尔泰、克罗齐对社会学的拒绝和片面指责,并没有影响社会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和创新,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对社会学均有革命性的建树,成就非凡,此已证明狄尔泰和克罗齐对社会学的见解浅薄。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议论深入广泛,近现代以来的各种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殆无遗漏,还涉及权力和腐败、革命和暴力、政治组织和反抗、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等等方面,从另一角度看,此书不仅是一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发展史,也是一部政治思想史。
年鉴学派的“史学革命”
自费弗尔和布洛赫于1929年创立“年鉴学派”,数十年来历经三代史学家的学术传承,这个“新史学”团队不断壮大,名著迭出,对现代历史学的发展贡献至巨。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对年鉴学派做过专题研究,著有《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一书。伯克对法国现代历史学家群体尤其是年鉴学派的评价很高:“二十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著作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伯克所指的,当然包括年鉴学派那些“最具原创性的史学著作”,“一整个书架的出色著作”———如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勒高夫的《圣路易》、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等等。
因此,伯克将年鉴学派的出现称之为“史学革命”。伯克在论述费弗尔、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大师的史学成就之余,对他们作为杰出学者的品格亦略有评说。伯克不无讥讽地称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是“学术政客”,暗指他们都曾在“学术与权力”的关系中纠缠不清;而对布洛赫则充满敬意:“难能可贵的是,在布洛赫日益感到孤立,日益为其家庭、朋友及国家的未来去向感到焦虑之时,他还能撰写他对历史学目的与方法的心平气和的反思。这本讨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至今仍然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书之一。”布洛赫将其创立的“历史回溯法”(即“逆溯历史”的史学观)成功地运用到《法国农村史》的撰写中。伯克对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推崇备至,认为“《法国农村史》最为出名的,也许是所谓‘回溯法’。布洛赫强调,由于我们更为了解晚近的情况,也由于从已知推导未知更为谨慎,必须‘从后往前看历史’。布洛赫非常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方法”。而《封建社会》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综合性论著,它运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从900年至1300年长达四个世纪的欧洲史,探讨了奴役与自由、神圣王权等论题的重要性;它注意发掘“集体意识”、“集体记忆”、“集体表象”之下的“封建制文化”内涵,并把“封建制”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法国农村史》是“乡村史”的开山之作,《封建社会》则是布洛赫一生史学之集大成,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两书都是年鉴学派的早期代表作,对该派第二、第三代重镇如布罗代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影响至深且巨。虽然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的作者)宣称“超越年鉴学派”,超越费弗尔、布洛赫等“学派祖师”开创的学术传统,摆脱布罗代尔史学体系的束缚(傅勒的研究路数确实与几代年鉴学派史家大异其趣,不涉社会-经济史和心态史,其毕生倾注心力而有所成就者,乃在法国革命史及政治史的“宏大叙事”),但他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渊源有自,是食年鉴学派的乳汁长大的;在学术关系上,无论“家法”抑或“师法”,追本溯源,终究是该派一脉传承。
或曰年鉴学派史家多侧重于“微观史”,批评者认为未免流于琐屑,缺乏宏观气度。然则另一位以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名世、与年鉴学派关系密切的史学家勒费弗尔,撰文分析法国大革命骚乱及其集体行动之心态,不遗“微观”之微,着力搜寻隐藏在历史事件中的细节,以其视野“宏观”,见微知著,成为传世的史学名篇。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描述的是中世纪法国一个小山村几百个村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及村民与天主教的关系,这部“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巨著,是年鉴学派的史学代表作之一,对研究乡村史、人类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伯克赞许勒华拉杜里重构日常生活的新颖的史学方法和原创性,“《蒙塔尤》是‘微观历史学’的一个典范。作者借助一粒沙子研究整个世界……它是历史想像的精心杰作,是对人类学化历史之可能性的一个启示”。由此可见,衡量一个史家的功力,不在史学方法的“微观”或“宏观”与否,乃在其识见之高低。
“新文化史”的观念和方法
年鉴学派是二十世纪“新史学”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克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未尝不是年鉴学派“新史学”的赓续。伯克从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大师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家的技艺”;而他自己认为,以赛亚。伯林和克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作者)对他的影响更大。比起这些仅以一部著作就足以传世的史学大师,伯克显然略胜一筹;其虽未逮大才槃槃之辈,也仍是一位功力深厚、富有叙述魅力的出色的历史学家。
伯克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一文,对新社会文化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据伯克考察,西方新文化史运动肇始于法国,它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在1970年代初传入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播及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新文化史运动的参与者已不囿于历史学家。
“新文化史学者所研究的内容相对于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说是全新的”,伯克将“新文化史”大略分为七个类别:一、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饰、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包括书籍)的历史;与年鉴学派的经典史家如布罗代尔等人相比,新文化史家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学术探讨。二、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外延所及,亦包括情感史、恐惧史、幽默史等;在性史研究方面,福柯自然是先行者(《性经验史》)。三、表象(形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像及感知的历史,法国史学家谓之“表象(形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在此方面颇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想像的共同体》。四、社会记忆史。伯克举了一部由一群法国学者合撰的煌煌巨著《记忆之点》,我以为已译成中文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和美国学者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亦可归入此类。五、政治文化史,新社会文化史家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政治,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以及革命史。六、社会语言史,如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等。七、行为社会史,如旅行史等。
伯克指出,“新社会文化史有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新文化史学既吸收了年鉴学派“新史学”的一些史学观念和方法,同时又是对旧“新史学”风格的反动。伯克以他自己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为例,阐述“新文化史学”的观念和方法:“新文化史学家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认为文化影响甚至决定政治和经济的行为;他们强调他们所称的文化‘建构’或‘创造’,许多作品在书名中使用了‘创造’一词。我自己的书《塑造路易十四》就是体现这一趋势的一个代表。我选择‘塑造’(fabrication)而不是‘创造’(invent)一词以强调王室形象的物质性和集体建构的共同作用。我使用‘塑造’这种说法并不表示路易十四是人造虚构的,或其他人是真实自然的。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路易十四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在塑造的过程中,他得到特别的协助。‘塑造’表示一种过程,可以传达出发展、过程的意味。路易十四‘形象’的塑造者是当时的画家、雕刻家、版画家、裁缝师、假发制造人、舞蹈老师、诗人、典礼仪式司仪、设计者等等……有学者非常简洁地将这一历史写作中的变化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转向’,这就是‘社会文化史学’一词的源起。”
伯克是“新文化史”运动的健将,阅读他的文化史、社会史方面的著述,可以感受到一种“新文化史学”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其间。
从图像中发掘历史的细节
最近,伯克的又一种著作《图像证史》(Eyewitnessing:TheUsesofImagesasHis-toricalEvidence,一译《见证: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功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伯克说,《图像证史》的内容是关于“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涉及政治事件、经济趋势、社会结构及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等范围。按照伯克的界定,所谓“图像”,不仅包括各种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版画、广告画、宣传画、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图像是历史的遗物,记录着历史的痕迹,从图像中发掘历史的细节和证据,此即“图像证史”。
这是一本饶有趣味的“图像文化史”。试举几幅“图像”,看看伯克是怎样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场”进行“解构”和“还原”。十九世纪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有一幅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描绘的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把国王查理十世逐出法国)期间巴黎起义的“自由形象”。由于这幅名画上有些人物身份暧昧,每每引起错误的“解读”。伯克分析:“德拉克洛瓦塑造的自由形象一半像女神(模仿古希腊的雕像胜利女神),一半像凡间的妇女;一手高举飘扬的三色旗,一手持步枪。她裸露的胸膛和弗吉尼亚小帽(有古典的含义)象征着自由,而革命正是为自由而发生。至于‘人民’,那位头戴高礼帽的男人,依据他的头饰,往往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化身。但事实上,当时的工人阶级有些也戴大礼帽。无论如何,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穿的衣服,特别是他的腰带和裤子,就可发现这个人物是个手工工人。”伯克质疑以往把此画中戴大礼帽者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化身的说法,从细枝末节中发现了历史现场的真实信息。
伯克“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时,特别留意到一些独裁者的共通之处,都很注重自己出现在宣传画上的“崇高形象”。在表现“伟大领袖”的正面绘画里,独裁者日常生活中的阴鸷、暴戾、专横的性格特征全然消失,而呈现出慈祥、高昂、深邃的智者形象,或如耶稣基督般坚忍,一副救世主模样。伯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辨析,在很多历史图像中发现独裁者为了表现其“造假形象”而进行画面处理:墨索里尼喜欢让人拍摄他光着膀子跑步的“阳刚气质”,以展现他的个人魅力;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刻意在街头“散步”时亲吻孩子,以显示“平民化的领袖风格”。群众围绕在领袖身边,欢欣鼓舞,仿佛沐浴着和蔼的春风,这种“宏大叙事”的图像,旨在突出独裁领袖被群众衷心拥戴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为了突出领袖的“高、大、全”形象,御用摄影师们基本采取镜头从下往上拍的仰角度,御用画家们也采取画面从下向上仰视的角度,以使伟大领袖比人民更高大、更有英雄气概。墨索里尼是矮个子,为了“拔高”自己,他在检阅军队时站在一张脚凳上;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也是矮个子,他的“拔高”办法是缩短透视的角度,与墨索里尼可谓异曲同工,而他的照片,要先处理掉脸上的皱纹以后,才准许在报纸上发表。在表现战争的宣传画上,希特勒身穿甲胄,墨索里尼头戴钢盔,一副身先士卒状,暗示他们正在进行“圣战”。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齐奥塞斯库等独裁领袖,都有一幅“像神龛中的雕像”的标准相,每当重大节日或庆祝活动,虔诚的群众就像圣徒一样抬着他们的巨幅画像参加游行。
通过电影也能解释历史事件。匈牙利导演扬索的影片《红军与白军》,是苏联政府为纪念俄国革命50周年而委托他拍摄的,背景是红军与白军反复争夺一个小村庄。本来苏方的意图,是要淡化“内战”中发生在红军方面的暴力,但导演依据的历史,如实表现了双方在战场上的“恐怖”。红军中有不少自愿兵,纪律松弛,具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而白军一般是职业军人,多恪守战场规则。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更守纪律,暴力的自发性更低。
图像史也是“艺术”的社会史,当你翻阅这部丰富多彩的图像社会史,藏在历史缝隙中的重要事件的细节就会露出它真实的一面。伯克别具只眼,选取了八十多幅“图像”,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一一解读其中的隐秘,发挥了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功用。
专题撰文:沈展云
(沈展云,学者,著有《灰皮书,黄皮书》,现居广州)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