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源自于亚洲的民族大迁徙 在中古时期,世界史家很少认真去讨论古代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关注于宗教伦理教育,通过强调帝国兴亡乃历史的必然现象,从而劝谕统治者不要迷恋于人世间的权力和虚荣,要从兴亡之道中认识到上帝的意志,虔诚信主。中古晚期知名的历史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伊本多菲(Thomas Ebendorfer,1388—1464年)在其《罗马帝国编年史》中还在坚持这一传统。在叙述西部罗马帝国的历史之后,他特地写作了一个“启示”:“上帝的审判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在罗马建城907年之时,奥古斯都开创的西部罗马帝国,在可怜的小奥古斯都手中丧失了其荣誉,可怜地落入了诸外族(exterarum gencium)之手,开始走下坡路……依据上帝公正的审判,度量其他人的,自己要被度量;用武力和欺骗取代其他王国的,自己也会被卑微者取代,受到其他族群的摧毁。它曾将自己立为全世界最高者,首先被阿拉里克所羞辱,此后被奥多瓦克统治了14年。”他们的笔下并没有统一的、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民族大迁徙,有的只是各个具体的族群的迁徙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却并不这么来认识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15世纪的大学者比昂多写作了名著《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在这部模仿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的作品中,比昂多揭示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蛮族入侵的关联性。他认为:从君士坦丁之子君士坦提乌斯至提奥多西诸子统治的70年间,帝权经历了巨大的衰落。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攻陷罗马城,此后匈奴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纷纷统治高卢和意大利。在查士丁尼统治之下,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复兴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攻灭了许多蛮族王国。但是,宦官纳尔苏斯招引伦巴第人入主意大利,带来了灾难,断送了复兴。从赫拉克略时期开始,帝权的巨大衰亡开始了。由于先后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入侵,使得帝国一直衰落下去,仅仅维持了帝国之名,而无其实。 比昂多全面讨论了蛮族入侵,其所论及的蛮族也极为广泛。这些蛮族来自四面八方, 始于哥特人而终于土耳其人。他并没有提到“日耳曼人”,甚至都没有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北方佬”(Septentionales)。两代人之后的马基雅维里,就是在“北方佬”的视野之中来理解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他还是沿用了主祭保罗的理论,认为北方人口繁殖快,必须迁徙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的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个国家为由北方来的移民定居下来提供种种方便,这样就把罗马帝国毁灭了。”一部出版于1564年,由匿名作者撰写而托名为马基雅维里、声称从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语的作品,其标题即为《北方族群的迁徙和帝国的灭亡:清布尔人被马略征服之后》。在书中,译者提出了“五百年帝国必衰亡”的理论,而帝国衰亡则不外内因和外因,外因即“这些北方族群的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15世纪末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重新发现,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事件。近年来德裔美籍学者克里布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耳曼尼亚志》认可史的文章,2012年更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巧妙地通过《日耳曼尼亚志》的传播史来解析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 尤其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但是,学者们对《日耳曼尼亚志》的接受情况,要远比克里布斯所想象的复杂,而且《日耳曼尼亚志》本身的内容就相当庞杂模糊。例如在种族源流方面,塔西佗对哥特人的归属就非常模棱两可。他既提到哥梯尼人(Gotini)又提到了哥托内斯人(Gothones),两族相邻,哥梯尼人更靠近罗马边境。塔西佗认为,他们不属于同一部族,其中哥托内斯人是日耳曼人,但塔西佗对该族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信息;而他了解较多的哥梯尼人,则因为说高卢语,被认为“不是日耳曼人”。应该说,在近代早期,与其他古典史书相比,《日耳曼尼亚志》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对待。在使用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将它与其他古典史料相提并论,并没有厚此薄彼的现象。至少在哥特族源问题上,塔西佗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令人信服的信息。 哥特族源的归属问题是日耳曼人源流史上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正是哥特人开启了“蛮族”大迁徙的大潮,是他们第一个攻陷罗马(410年),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比昂多就认为哥特人属于斯基泰人,而非日耳曼人;在他看来,后来的土耳其人即是哥特人的后裔。针对这一问题,1531年,著名学者贝阿图斯·瑞纳努斯(Beatus Rhenaus, 1485—1547年)专门写作了论文《与卜尼法斯·阿美尔巴奇论哥特种族源流书》,强调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所依靠的史料主要是拜占庭帝国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普罗科比的《战争史》。他说:“不仅我们德意志人很少读普罗科比所著史书,而且还被一些拉丁诗行所误导,认为哥特人出自于斯基泰人。” 但是,因为古典作家的论述各自不同,所以哥特人是否属于日耳曼人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17 世纪末,学者们仍然存在着分歧:“迁徙民族中的第一个就是哥特人。其名字是日耳曼语辞源,意为‘好人’。《卢恩文文献》中的记载多模糊不清,约翰·罗肯尼乌斯(Joannes Loccenius,1598—1667年)证明它与‘Getarum’的族名是同义词。语言和习俗也非常类似。但是约翰·蓬塔努斯(Johann Isaak Pontanus,1571—1639年)和克吕维尔(Phillip Clüver,1580—1622年)对此予以否认。我们认为‘Gothos’,‘Gotos’,‘Gottos’和‘Getas’是同一群人……以免古老的哥特族名湮没无闻。古代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被称之为斯基泰人,现在则被称之为鞑靼人。至于他们的来源,争议不会更少,他们是来自斯基泰人的兵营,还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但如果哥特人是日耳曼人,那么很清楚,他们来自于北方的日耳曼尼亚,即今天的日德兰半岛(Jutia),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到17世纪中期,比得·海林(Peter Heylin,1599—1662年)就总结说:“关于古代民族的辞源多不可靠,大部分要靠推测,所以置而不论。” 哥特人只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对于日耳曼人这个词汇究竟来源何在,是什么意思,近代早期的学术界异说蜂起,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些人依据罗马作家的意见,认为日耳曼人意为‘兄弟’,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人情绪暴躁、身材颖长、头发金黄、躯干魁梧,习俗、宗教仪式与高卢人相近,如斯特拉波即持此说。有些人则以为这是针对罗马人而言的,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在宗教仪式或者军事习俗方面相互交流,犹如兄弟,故罗马人称其为兄弟。这是普鲁塔克的看法。有些博学之士则从日耳曼语言考察其辞源,认为‘ger’意为‘全部’,‘man’指‘人’,合起来就是‘所有人’的意思。另一些人则推测,‘ger’在高卢语中为‘战斗’,所以‘Germani’即为‘战士’之意。有些人认为这个族名源自于‘germinando’, 因为该族人口繁殖极快。主祭保罗即持此说。还有些人认为这个词来自于亚洲的族群‘Carmanis’,字面意思为‘起初’。鲍伊克鲁(Kaspar Peucerus? 1525—1602年)认为‘日耳曼人’来自于‘Hermenner’,即‘好斗之士’;朱尼乌斯(Hadrianus Junius? 1511—1575年)说这个词来源于‘Thogarma’,这位陀迦玛是歌篾之子,歌篾是雅弗之子,雅弗是诺亚之子。” 与此类似,对于早期日耳曼人究竟包括哪些族群,近代早期的学者们也是各自有所发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近代德国诸侯并立的局面是异说蜂起的现实土壤,而是强调了提供有关日耳曼人信息的古代作家,措辞较为随意,且与时而有所不同。“塔西佗、普林尼、奥罗修、斯特拉波、托勒密都讨论过日耳曼人,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弄清日耳曼人所属各族的名字,所以我特别惊讶地发现,这些族名与特定地区相连时会出现时代错位;也会同样地感到奇怪,没有哪个作家在族名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一致,而是各自使用了不同的称呼。”在列举斯特拉波、塔西佗和奥罗修各自对日耳曼人所包含族群的名称之后,作者总结说:“族名如此悬殊,无他,唯博学的学者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地给蛮族取名,就如同今天我们德意志人自由地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给外国人取名一样。这是因为过去在日耳曼尼亚,根据塔西佗的观点,男女老少都不识字,即便高卢人在接受罗马的统治之前,也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毫无疑问,希腊人和罗马人也为他们提供族名。罗马的文字与罗马的统治一道传播开来,同时为许多族群提供了族名。” 但不论他们对“日耳曼人”的辞源和所属族群存在何种分歧,他们都倾向于认为日耳曼人一直处在迁徙之中。通过不断地迁徙,这些不同的乃至互相矛盾的历史记载得以被贯穿起来,互相歧异的历史观点被调和成篇,从而提供一幅日耳曼人在旧大陆各地来回迁徙、战斗的历史画卷。虽然总体上和谐,但细节上费解。早在中古时期,日耳曼各族群各自迁徙的历史都已著录于篇。其中有关法兰克人的迁徙故事,流传最广。大约自6世纪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提供了最早的记载,经过7世纪的史学作品——《弗里德伽编年史》,发展成系统的迁徙谱系。“弗里德伽”认为,法兰克人源自于特洛伊人,在特洛伊城破之时,离开故土,转战于欧亚大陆,最终来到莱茵河畔,在墨洛温家族的领导下,创建法兰克王国,成长为西部欧洲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弗里德伽编年史》的作者,还试图依托于《圣经》,将法兰克人的起源,追溯到上帝所造的第一人亚当。 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地方史志编修活动蓬勃发展,从地方的角度追溯族群源流变得非常流行,也提供了大量的地方族群源流的资料;另一方面,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需要挖掘自身的族群源流。1555年由维也纳大学教授,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官方史家沃尔夫冈·拉齐乌斯撰写,1557年出版的巨著《族群大迁徙论》,就是针对这一需要,集合地方史志研究成果,整合经学和古典作品而成的一部集大成式作品。现在学术界公认,《族群大迁徙论》正式提出了“民族大迁徙”(Migrationibus gentium)这一术语。拉齐乌斯认为“一切族群皆在迁徙之中”、族群之间彼此“交流融合”。他的这部欧洲族群史,按照族群分卷,每个重要的族群都分得一卷,凡12卷。在每卷中,先论述特定族群的源流,然后叙述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最后梳理所有源出于日耳曼人的、当时散布于欧洲各地的教俗贵族之谱系;从而“见证日耳曼人和基督徒之名声”。 拉齐乌斯认为,日耳曼人包括汪达尔人、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他们都来自于亚洲,是在大洪水之后130年左右浮海来到了欧洲。日耳曼人源自于诺亚的孙子杜伊斯科尼(Tuiscone),这是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日耳曼人。科隆附近的杜伊斯堡即是其定居之地。诺亚的另一位孙子亚实基拿也来到了莱茵河。他们的后裔纷纷进入到欧洲各地,成为当地的原住民。最初的日耳曼人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后来由于不断胜利,其他部族出于恐惧,很快地改变其族名,变成日耳曼人。最初的日耳曼土著被称为“杜伊斯科尼人”和“加拉泰人”,后来被称为“阿勒曼尼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高卢人”。由于试图整合所有的基督教经书和古典史料,按族群编排,所以,拉齐乌斯的这本大书难免语绕重复,对各地教俗贵族的源流的梳理难免在细节上遭人诟病。但他将大洪水之后诺亚后裔的迁徙视为欧洲原住民的形成史,与特洛伊之后的英雄大迁徙所开始的移民史糅合在一起,以原住民与移民的融合创新为纽带,将欧洲两大历史传统和资料融会贯通,从语言互相借用的角度印证族群之间的融合,从而重新型塑了统一的欧洲文化基础,影响极其深远。 拉齐乌斯的《族群大迁徙论》依托于经书所提出来的“日耳曼人大迁徙”理论,总体来讲,勾勒的是从东向西的迁徙历史。这种学术观点在当时数量繁多的地方史志作品中,极为流行。在1598年修纂的《迈森源流记》中,耶拿大学教授艾利亚·霍伊斯勒努指出古代地方史就是族群迁徙史,而以《圣经》为权威,“写作族群起源、他们最初和古代的定居之所、迁徙、变迁和事迹,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古代史家很少会提到,而且在劫掠中,文献会丧失,人们也往往放弃学习。那些得以留存下来的材料,都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和不确定性,有些资料甚至没有根据、毫无道理地夹杂着传说。我的原则是追随经学,以便得到确定的观点。如果缺乏经书,则综合可靠的作家,或者遵从较为古老的说法,以期得到真相。”而他得到的真相是:迈森人与其他日耳曼人一道从东方迁徙到这些地区。至于这些人为什么经常改变定居之所,到处迁徙,霍伊斯勒努提供了三个理由。第一是寻找更好和适宜的定居点;第二是迫于人口压力,原来的土地过于狭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第三个原因则是受到邻近族群的压迫,不甘于屈服,而自愿迁徙他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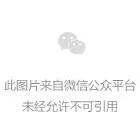 流亡中的日耳曼人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