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冬君:谢谢读者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阅读的周末,这是我们来的第三个纸的时代了。第一个去的是郑州,第二个是合肥,第三个是厦门。 今天下午让我们一起回到“纸的时代”,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也就是让我们要回归纸的时代,回归文字的时代,回归阅读。 我称阅读为一种精神收藏,之前有一段时间有股收藏热,各行各业都在收藏,但是唯有阅读,我认为是一种精神收藏。这种精神收藏是永恒的,一直伴随着我们一生,是最有价值的。我曾经有一篇文章是在北京《新京报》上发表的,就叫《阅读是一种精神收藏》,所以阅读对我们这个纸的时代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次新书的分享,题目叫“回到古典世界,期待文艺复兴”,这本书也叫《回到古典世界》。这本书是我和刘刚老师继《文化的江山》、《通往立宪之路》之后的第三本,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学术来历和我们的思路。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是我们两个人合作的第一本书,这套书有上下册,主要是重读中国史,就是把中国历史重新解读一遍。重新解读的立场,就是突破了传统教科书的立场,我们在那本书里说到有两个中国,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王朝中国最长不过三百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说中国历史有五千年是因为文化江山的不断传承,才把历史传承到今天。  第二套书叫《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讲的是近代史。近代史和晚清史分开了,实际上还是王朝历史和文化历史的区分。《回到古典世界》这本书,原来是叫做《文化好东西》,这个“东西”,指的是东方和西方,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讲的是普世性的文明在东西方文化上怎么融合。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回到古典世界》,也就是说,文明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时代,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走才能回到“文化好东西”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先请刘刚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  刘刚: 我先从这本书的书名讲起,《回到古典世界》,为什么要用“古典”两个字呢?“古典”和“古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都说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而古典也包含在古代史里面。但其实,我们强调它的古典性,古典和古代是有一个质的不同,现代性是从古典性发展出来,不是从古代性发展出来。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有几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等等,它们是古代性文明的产物,它们没有经历过古典性的时期。它们在古典性到来之前,也就是古典的理性觉醒之前就开始衰亡了。 那么,古典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如果把古希腊、希伯来作为一个标志来说的话,那么从古代性向古典性转变的标志就是摩西领导人民出埃及,从摩西之后,现代文明的根在古典时期就已经种下来了。  那么古代文明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在摩西出埃及之前有一个过渡时期,用太阳神统一诸神。统一失败后,又过了100年,摩西出现了,之前阿顿神是太阳神,摩西出现后,就变成了人格神的上帝,古典理性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觉醒了。 觉醒之后,原来古代性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的形式开始瓦解,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政教就分开了。它的基础是法治,犹太人跟上帝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人神契约而有法治,而实行政教分离。我们说的古典时期,是有一个来龙去脉的,摩西是一个开始。如果从古希腊来说,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古典世界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追求世界历史的统一性。  那么相应地,我们中国的古典文明是从周公开始,周公和荷马、摩西是相近的。从周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也是一种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追求。 轴心期在希腊,应该是在哲人时代,有一批哲学家,在中国,就是诸子时代。但是,这个诸子时代从哪来的?是从周代开始,我们用古典时代把轴心期前后两个时期也都包括了。这个轴心期向哪去?向着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去了,我们把它延伸到秦始皇统一,亚历山大帝国形成,这就是我们对古典时期的一个概括。  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世界”两个字,为什么是《回到古典世界》?古典时期就是从古代的王朝文明,从一个地域出发,走向的是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不管是亚历山大还是秦始皇都是这样,他们都有一种世界史的眼光。 因此,这本书有两部分,一个是“希腊化世界”,一个是“中国式天下”。“中国式天下”是自秦以来,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一种追求,“希腊化世界”也是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一种追求。把“古典”和“世界”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 如果我们要接着写“文化好东西”系列的下一部,就写“世界史的形成”。因为东西方都在追求世界史,亚历山大帝国留下了希腊化世界,秦汉大一统后也开始了它的中国式天下,东西方在对世界史的追求中走到了一起。 它们是通过什么走到了一起?通过丝绸之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开始联系起来。我们现在看来,丝绸之路的形成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中国因素,中国提供丝绸,还有一个是希腊因素,实际上它提供这条路,从西域、中亚到西亚,整条丝绸之路都属于希腊化世界范围,丝绸之路是用中国丝绸、希腊货币来进行交易。 罗马帝国并未进入那个东方的希腊化世界,一直被西亚的帕提亚人阻挡着,所以,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在陆路上没有交集,在海上有过那么一两次,罗马帝国派使者来。希腊城邦是被罗马帝国一个个灭亡的。 《荷马史诗》里面,希腊曾经征服特洛伊,据说,罗马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后来罗马取代希腊是一次历史性的报复。我们现在都说“两希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但在罗马时代,希腊是被视为东方的。他们的基督教,也分裂为西边的天主教与东边的东政教,一直到11世纪,还是把希腊看作东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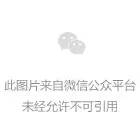 到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欧洲人才开始回到了他们的古典世界,才发现原来还有希腊人,有很多的诗人像歌德那样,都自称“我们是希腊人”,这样,希腊才开始回到西方,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标志。在此之前,希腊都属于东方。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东西方问题,我们现在谈到不同的文化就说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做文化比较也要讨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欧洲文明是以西方自居,自以为西方文化如何具有现代性,有一种西方中心论。如果我们考察西方的历史形态,你会发现西方也是不靠谱的,你会发现西方也是相对的。 如果仅仅从地理上来说,我们知道近代的时候,西方人很反感中国人的天下观,尤其对“中国”这个名字很不以为然,他们都说地球既然是圆的,那么中心在哪一点?如果你是中国,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叫中国。  现在想一想,这样的推论其实也可以放在西方上,东西方也是相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是西方。本来,美国在地理上应该在我们的东方,但在文化上,却说我们是东方,把我们划在了东方的范畴里,而他自己永远不东方,不管他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所以,东西方的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人费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西方学习,终于走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进入了东西方的世界格局。 西方的格局,实际上就是文明冲突的格局,《文明的冲突》里写到文明的冲突,其根源就是东西方的冲突,在这个格局里会产生冲突,还会制造冲突。不管是世界一体化还是大同文明,在东西方的世界格局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谈到一个文化问题,我们总喜欢做东西方比较,讨论东西方分别,比对着西方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实际上这是一种在东西方格局里的思维,这种思维本身就有分裂性。 从近东、中东到远东,希腊人还是被定位在近东的范围里,到了近代,我们中国是在远东的范围里,世界历史不是经由陆地,而是通过大航海形成,如果我们要做第三个题目,就涉及到“东西方大航海”,东西方的格局怎么形成,中国是怎么一步步从天下观进入到东西方的格局里。 谈到大航海,我们一般会讲到欧洲,讲到美洲新大陆。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也有大航海,从唐朝开始。在海外,对中国人有两种称法,叫做“汉人”和“唐人”,面对北边西域胡人,我们都是汉人,到了下海的时候,我们就是唐人,像现在就有很多唐人街。日本人一直称我们为唐人,不管在哪个朝代,派的使者就叫遣唐使。中国开口岸通商从唐朝开始,真正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则到了宋代,从宋一直到明。航海人数,闽人最多,其次是粤人。通过大航海,中国几乎把南海变成了中国海。  李冬君:我们在座的可能都知道泉州在当时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 刘刚:大航海时代不是由中国一家开辟的,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开辟了大航海时代,通过大航海时代把南海变成了中国海,据说每年闽粤之人都有几十万出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水浒后传》,里面写到宋江被朝廷招安之后还留下了一批人,他们又重新出海了,跑到暹罗去,李俊还做了暹罗国的国王。这本书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下海的状态,当时很多人就是占一个岛就做一个国王。  有一本书叫《渡海方程》,中国的海岸线北边是从东北下来,一直到波斯湾,当时它还提出建议,中国的海关光设在泉州、广州、宁波是不够的,要设到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那边,甚至要到马六甲海峡,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一带走。 谈到宋朝,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从另外一面看,它大大扩展了中国的海疆,在以中原为中心论的王朝史观里,对此视而不见,成就没有反映出来,因为开发海疆,形成华侨世界,是依靠民间力量,反映的是民间的海权。像李俊跑到暹罗国去做国王,其实算是一个海盗。 李冬君:挖掘这段历史,看正史基本是没有,要看当时人的笔记,从笔记里抠出一些资料来,我们才发现民间海权对中国海权的扩展和坚守。王朝实际上是不在乎这一块,甚至不要这一块,因为到了明朝就开始海禁,不让你下海。  刘刚:修宋史,中国在海洋上的扩展就没有得到反映,一代王朝也没有真正地去落实海权,只有民间力量在这里活动。 但它在经济上对宋朝的财政收入支持很大的。南宋丢了大半河山,三分之二的人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减少了,但是财政收入比以前还要多。增加的收人就是大航海带来的,就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是民间海权带来的,对宋朝历史的评价要结合这一块才是全面的。 李冬君:因为北边有辽津压迫,不得不往南走,所以放弃了那边,在南边沿海扩展,民间海权给它带来了利益,它的财政收入比原来还要高出很多很多。 刘刚:为什么岳飞北伐搞不起来,就是因为大家都下海了,下海可以带来很多利益,往北打仗劳民伤财,所以南方人不太愿意去北边。从宋到明,中国下海的人很多,却没啥海权,问题出在哪?在于王朝中国没有把国家意志表达在海洋上面。西方人进入印度洋、进入南海时,都带着国家的一种主权行为,都有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在后面做支撑。中国华侨是社会力量,但它不能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达,不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反过来,华侨社会力量反而成为西方国家的支撑,比如荷兰人到华侨社会里从华人里面选领袖来治理。曾经还发生大的灾难性的事情,荷兰人曾经屠杀华侨,那时候是乾隆时期,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乾隆说“那是天朝弃民,那些人要是在国内,我就要把他们抓起来,有人帮我们杀了更好”。 西班牙人在明朝的时候也对中国人实施过一次大屠杀,也杀了好几万人,那次是完全由一次误会引起的。因为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交易的时候,金银都是西班牙那儿来的,用马尼拉大商帆运来的,听说菲律宾的树上都长金豆子,所以福建的一批人就到菲律宾去。西班牙人就说你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一问原因,就说树上怎么可能长金豆子,你们肯定别有用心。因为西班牙害怕华侨人多,整个社会力量都是由华侨构成,所以把华侨骗去枪杀了,后来明朝也不了了之。  一个原因是仗也难打,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跟西班牙历来很好。过了一阵子后,大明王朝反而派人去安慰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跑到菲律宾主要是要跟大明王朝做贸易,发生这件事情以后,贸易也做不成了,损失很大。他们看到大明王朝派使者来了,趁势巴结,又开始做贸易。大明王朝和西班牙两个王朝的贸易相同的地方比较多,贸易一直做得很好。后来,荷兰人进来了,就不一样了,荷兰是共和国的,国家属性不一样,而且荷兰与西班牙是敌对关系,互相驱逐,所以荷兰闯进来的时候,明朝也接受不了了。 但是,王朝中国也没有海权力量来跟荷兰人对抗,真正跟他们对抗的,是中国的民间海权力量,像在福建出现的郑家父子,郑成功等,打了正儿八经的海仗。像郑芝龙那种海仗的打法,到了林则徐那时都不会了。  魏源写《海国图志》的时候,还是用在江河流域打仗的那种打法,放在大海上根本不行。在这样一个大航海的过程中,西方人把中国的天下观改变了,中国不得不进入一个东西方的格局。 在东西方格局里,首先做了一个文化上的反应,其实在中国还具有海权力量的时候,它的反应是比较平和的。比如利玛窦随着大航海到中国来了,徐光启等人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中西会通”,强调孔子和耶稣有很多共同处,例如,他们都主张爱人。那时强调共性的一面比较多,因为它是一个对等、平和的时代,但是后来在文化上的反应越来越严峻了。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国家转型,政治形势变严峻了,文化的反应也变严峻了。从“中西会通”变成了“西学中源”,有一个说法,说西学的源头都是中国,这样的说法,从黄宗羲就开始了,他说,西方的几何学,是从中国的勾股数传过去的,西方人保留下来并发展了。 一直到康熙皇帝以后,康熙学了很多西学的东西,还请了很多传教士做西学的老师。那些西学的老师为了拍皇帝的马屁,把西方的学术都变成“东来说”,都是从东方传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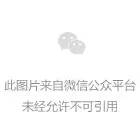 康熙听后很认真地下御旨,编了一本数学方面的书《数理精蕴》,他说数学的根源都在中国,但是在中国失传了,后来传到西方,西方人把它保留下来,发展之后又回到我们东土来了。当时一个大数学家李之藻就把康熙皇帝的那道御旨体系化、学术化了,所以这个反映越来越严峻了。 “西学中源”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东西方还没有分别心,比如这个东西去了西方,又回到了东方,原来就是我们家的,来了我还是可以接受,没有排斥它。 但是后来就有所排斥了,西方的东西虽然好,但是不能为本,所以就出现了“中体西用”说。西方的船坚炮利、机器生产可以用,但是文明的根本,政体、国体都要是中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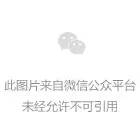 李冬君: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讲到文明冲突、文明碰撞,那么在一个同一时空中,人类都是从一个大峡谷中走出来,但是走着走着为什么文明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同一时空中文明不一样了,为什么有的文明渐渐消失掉了?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断? 本来人类文明是在同一时空,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到了轴心期或者是到了某个阶段突然就不一样了。我们虽然说东西方是相对的,但是还是有一个分界,像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这些几大文明都消失掉了。西方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又出现了现代性的一种文明,但是中国始终沿着自己的轨迹一直走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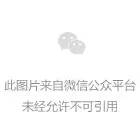 刘刚:这里面跟书名也有关系,为什么要回到古典世界?像那些中断的文明都没有被古典理性的光芒照耀过。被古典理性光芒照耀过的,比如说古希腊文明,它的国家可以不存在,古希腊民族可以不存在,但是它的文明还在。 欧洲人认祖归宗,说我们都是希腊人的子孙,说明它的文明传承没有断,只是不是以国体、政体、民族的方式传承,而是以希腊化世界的方式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当代世界是希腊化世界的一个现代化。 那么五千年来中华文明能够一直传承下来,它的幸运也是因为接受了古典理性光芒的照耀。先秦诸子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周公,和荷马、摩西同样的时期,我们的先秦诸子和希腊哲人是同一个时期。经过这样一个时期,被理性光芒照耀过,都具有现代性。 中国不再以天下的方式呈现了,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以天下的方式呈现,现在呈现的方式,是希腊化世界的现代化。实际上,我们回到古典时代的时候会发现,先秦诸子比我们当代更接近古希腊时期,它们有很多统一性的东西。 在这里面,我们所要挖掘出来的是古希腊的古典理性和中国的古典理性的会通之处。现在,在东西方的格局下,在东西方文明论的背景下,你是找不到的,要找到它你必须走出东西方格局,真正地回到古典世界,在古典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来寻找。 李冬君:古典世界的高峰就是轴心期,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是轴心期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在这段时期呈现的各种文明不一样,比如说在印度出现了印度佛教,中国从周公开始到春秋战国,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人时代。 轴心期之前有个先知时代,代表人物有摩西、荷马,之后,有个实践理性的哲学家王时代,追求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我们这本书叫《回到古典世界》,就是回到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不一样的文明样式,比如古希腊的文明样式、佛教的文明样式,还有中国的文明样式。 刘刚:不同的文明样式也是文化上容易产生分别的一个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是它有更多的共同性,这就是世界史真正的趋势。比如说这些世界史的因素在佛教里是怎么呈现的,希腊因素又是怎么进入佛教?我们现在看佛陀的佛像,它是以阿波罗的图像为原型的,佛教一开始是没有雕像的,后来是希腊人带过来。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在汉朝时期,在丝绸之路。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对话的时候说到,要是让他在世界历史里选择一个时期和一个地点,他说他要选择唐朝时期的西域,唐朝时期的西域是人类的一个最好的时期。 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化,比如阿拉伯文化、佛教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形成真正的世界史,而不是一个一个王朝。 李冬君:古典世界特别具有普世性,或者说更具有世界历史主流性,或者说对人类文明贡献更大一些。 比如古希腊文明,它的制度性贡献,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里就有很多古希腊因素。 刘刚:我们中国人在拜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接受古希腊因素的影响,像这些佛像,还有唐朝文化里有很多这种因素。所以有的人提出了一种观点,中国的敦煌就像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世界文化形成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前两天我在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石碑,包括很多中国人的墓碑,上面刻的都是基督教,中国人的墓碑上刻的文字都是元朝的。 实际上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像我们说的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孤立地发展,自给自足地发展,而是在一种交流中发展。 李冬君:其实古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侧重于制度,比如它的城邦民主制,中国的制度基本上也是从那个时候形成的。还有西方人说他们是希腊人,其实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希腊思想和精神传下来了。 中国在那个时代,从周公到孔子、老子,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侧重在天工开物这一块,比如丝绸、茶叶。尤其是丝绸,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西方交流贸易媒介。 刘刚:中国和希腊各有千秋,希腊作为一个国体、政体,国家的延续性并没有到现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体、政体,它的文化江山的完整性保留下来了。 李冬君: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讲的希腊化世界是从亚历山大把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从河西走廊一直打到帕米尔高原,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按希腊城邦制建立一个城邦国家。 希腊化世界一直到帕米尔高原,直到亚历山大病倒以后,(他30多岁就去世了),这条路线都是希腊化世界。希腊化世界留下来的遗产,它的城邦遗产,它的文明样式遗产,包括它的精神遗产,在那一带还发现了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手稿,但是,今天的中东好像没有继承这些文明。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自从世界进入东西方格局,原来希腊化世界就一直不得安宁,成为文明冲突的战场,比如阿拉伯问题、伊斯兰问题。但是,欧洲人真正把中亚、西亚的区域问题解决了,处理得比较好的只有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处理他的亚历山大帝国的时候,他在希腊是城邦国王,到了波斯就是君王,到了印度就变得神圣了,到了埃及就是法老。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姿态对各种政治文化兼收并蓄,没有搞那些东西方格局,没有搞文明的冲突。 对他来说,如果有“东西”,那也是“文化好东西”,只要这是个“好东西”,只要对我有用,就拿来用,因为在他那个时候没有我们这种形成文明冲突的东西方格局。 罗马人从来没有搞定希腊化世界,凯撒想过来也过不来,克拉苏被帕提亚人杀了,十字军东征也是来来回回,没有搞定。包括现代美国,只要把它放在东西方格局里面,也解决不了东西方问题,你把太平洋装进这个格局里也解决不了。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走出了天下观是不够的,还要从东西方格局里走出来,谁率先从这个格局里走出来,谁将赢得世界。我们的书开篇和结尾都是讲这一块的。 李冬君:不光是在近代史这段时期我们要从“天下观”走出来,当今世界问题的解决,我觉得更要从东西方对立冲突的格局里走出来,也就是从文明的冲突里走出来。前一段时间在报纸、微信上很多问题都是在亨廷顿格局里讨论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走出来。 所以我们这本书讲到要回到古典世界,公元前800到公元前200年,包括亚历山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文明冲突。“西方中心论”也是制造文明冲突的一个基本点。 刘刚:那个时候没有东西方格局,西方这个概念主要是天主教提出来的。西方主要有两个核心因素,教权和海权。像日本人全盘西化,以为在东方打败中国,又打败俄罗斯,就算是一个西方国家,但实际上,一旦你碰到教权和海权的时候,西方人是不接纳的。 他们把你当作西方地缘政治在东方的看门狗,在东西方大格局里是井底之蛙,最后日本人发现自己全盘西化了,在西方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里有作用,但是还是成为不了西方,所以日本就放弃了,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哲学。 他们分析世界各种文化类型,最后总结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只有我们日本文化是世界级文化,因为我们自己原创了神道教文化,又吸收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又学习了西方文化,真正的世界文化只有我们日本人的文化,所以我们这场大战是要为世界文化开辟新局面,真正把世界文化确立起来。 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把文化拼盘当作文化整体,文化不是一个拼盘把各种东西拼起来。在这样的一套文化哲学支持下进行了太平洋战争,实际上是想通过战争的方式突破东西方格局,自己开创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李冬君:日本人很有世界史的抱负,他们要重新构建世界格局。 刘刚:我们中国人怎么从这样的格局里走出来?没有深入去了解西方,他们西方人自己是怎么意识的?他们对“西方中心论”有所反省,但是,似乎还没有走出东西方格局的自觉性。 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没有要走出东西方格局,只是要把西方的元素发挥得更加完美,更加具有普世性。你单方面地发展,越来越具有普世性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最终不走出来,伊拉克、叙利亚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格局摆在那,它就是一个两分的格局,一个制造对立面的格局。 所以,我们这本书的结尾就是走出东西方。这个系列的书,如果还有最后一本,就是要“走出东西方”。 李冬君:从古典出发,然后走出东西方,可能是我们探索的一条解决人类文明冲突的道路。东西方格局总是存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刘刚老师有一个观点是,回到古典时代那是一个理性觉醒的时代,这应该叫作世界史的开始,因为在这之前还不叫世界史。  公元前800年到500年是人类普遍的一个理性觉醒时代,有佛陀出现,有古希腊,有中国,当然伊斯兰是很晚的,它是没有接受那一次轴心期的理性洗礼的。经过理性洗礼之后,人类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拯救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文艺复兴。想要走出东西方,还是应该通过文艺复兴,而不是通过战争、冲突或其它的手段,因为取得共识,取得普世,还是要从文艺复兴开始。 我们中国虽然现在看到了各种危机、紧张,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它的下面潜伏了一种文艺复兴的力量。这种文艺复兴的力量,我觉得,你不要往上看,不要仰视,要平视,因为中国任何时候的文艺复兴都是在民间,而不是在上面。上面都是权名之争,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权,不在乎民间,权利之争有时越激烈,民间的空隙越大。 比如,今天我们在纸的时代,这个名字起得好,回到纸的时代,回到阅读时代,回到文字时代,刚才刘刚老师说你们一年有300场,这300场的力量简直太强大了,300场就是文艺复兴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除了纸的时代还有其他的书店,这种文艺复兴的形式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希望,看到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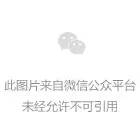 互动问答  观众甲:刚才听到两位老师说古典世界,让我想起中国的百家争鸣。众所周知,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对新文明就会产生迫切的希望。所以在稳定的社会时期就没有对文明有迫切希望,也很难产生文艺复兴。 大家读过历史都知道中国出现过很多乱世,例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觉得自从百家争鸣之后,中国的文化就没有出现像文艺复兴或百家争鸣这样的盛况。请问这是为什么? 刘刚:先秦有诸子争鸣,魏晋有名士清谈,两者很相似,诸子的政治理性和名士的审美人格,各有千秋。实际上我们对魏晋时期的很多东西要重新认识,它不是像我们以往说的那么不堪。 魏晋时期中国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是惊人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世界史的范围里来看。当时两个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东边是汉帝国,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我们看到西罗马帝国在游牧洪流冲击下灭亡了。 在中国,有一场著名的战争叫淝水之战。雷海宗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有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有了秦汉大帝国。淝水之战开始了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大周期,如果中国淝水之战打败了,那么可能就跟西罗马帝国一样,打赢了这场战争中国开始了第二个周期的发展。雷海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认为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周期。 那淝水之战是怎么打赢的?肥水之战是文明的抗战,不是一代王朝的抗战,王朝已经灭亡了,王、谢两家扶持了新的王朝东晋。这种文明的抗战在罗马没有出现,帝国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取代了罗马文化。 但是肥水之战是整个文明的抗战,一路上都有军队抵抗,80万大军到了长江流域进入总战场后就没有几万了,只是看起来声势浩大。因为是全民抗战,每个地方,每个阶段都有人抗战。为什么山上都草木皆兵?就是因为全民抗战。这样中国才保存下来,如果你是一代王朝抗战那就会灭亡。 南宋为什么灭亡?因为是王朝抗战,不允许民间抗战,民间抗战都要被取缔。像文天祥起兵,南宋王朝不让他进城。“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枪杆子里不出政权的合法性,枪杆子掌握在每一个公民的手里才具有合法性,真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是美国。所以你不能扛着枪跑到朝廷来,朝廷宁可亡于外部也不愿亡于内部。 李冬君:所以魏晋南北朝时的抗战是文明的抗战,实际上那个时候东汉打匈奴,把匈奴一直赶到大西北。 刘刚:还有一个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格局打开了,不光在两河流域理解中原文明,因为之前中原史观、王朝史观就是在两河流域的范围,以中原为中心形成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不光是两河流域文化,还有长城那边的草原文化,还有东南一带出海口的海洋文化,这几种文化整合成一种大格局。在古代史范围里,基本上是草原游牧文化和大河文化之间的冲突。  近代以后,海洋文化崛起了,进入中原。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冲突除了政体之争,除了政治因素,背后还有文化因素。孙中山是海洋文明的代表,到现在改革开放也都在东南沿海这一带,说明这一带兴起了。原来大河流域在中原,然后到了运河,沿着运河发展,现在是沿海,在这么大的一个文化格局里,互相调整。当我们面对海洋问题时,我们用海洋文化,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冲突的时候,用草原文化调解。我们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文明抗战。 李冬君:刚才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在乱世的时候中国各种文艺复兴开始了。 刘刚:乱世的时候没有王朝格局,没有专制。魏晋时人们到山里去,是特别自由浪漫的,当时殷浩和桓温对话,桓温是政治家、军事家,有着雄才大略,所以看不上殷浩,觉得殷浩打仗不如他,治理国家也不如他,但是殷浩的名气怎么就比他的大。 殷浩说,我干嘛要跟你比,“我与我周旋,宁作我”!你再雄才大略我也不跟你比。他们的境界不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殷浩比他的名气大。 李冬君:魏晋南北朝也是个性觉醒的时候,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时代,还有南宋时期。  观众乙:老师,在南宋时期岳飞要北上,您说海洋文化兴起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当时国君对北上不是很感兴趣。可不可以扩展一下这方面,因为在座的可能对岳飞的典故比较熟悉,那有没有不一样的野史让大家了解一下。  刘刚:岳飞是从中原南下,社会基础是在江南,当时讨论要不要北伐的时候有两派观点。现在大家比较肯定的声音是主战派的声音,说是爱国主义,当时讲和的都是卖国主义。 主战的代表是岳飞,主和的代表是秦桧。当时宋朝的时候刚好气候进入一个冷周期,在南京都有冰窖了,特别冷,所以北方南下就有动力,而南方是不愿意北上的。打得赢打不赢还不一定,即使我们打赢了,谁待在北方,最多打两年三年,我们就要回家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不一样,游牧文明走到哪里都可以安家,农业文明是要回家的,谁愿意在那待一辈子。。 如果天气变暖了,北方的草原开垦成良田,你分给他一些地,他还有动力去。但是,现在这么冷,去打北方什么也得不到,只是报仇收复国土了,北方人是收复国土了,但是南方人说收复了也不是我的,所以南方没有动力去。往南边走暖和,如果出海,每天都可以赚钱。 观众丙:我不能理解的是古希腊公民社会在物质那么不发达的时代,人性都可以无限地去张扬。 现在一些很权威的报纸上都发表这么尖锐的意见,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他们是不是在用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的东西来引导。 我们中国有13亿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很独立的思想。 李冬君:我们看历史是怎么看的,是有王朝历史和文化江山,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你再怎么喊,文化中国还是按着自己的规律往前走。走了五千年了,没有因为哪一个朝代杀了多少人或是怎么样而断掉。 中国人种还在,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然后来做一点我们每个个人能做的事。不去响应它,不去参与它,不去宣传它,不去转发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坚守,防止文革发生。 刘刚:晚清的时候,清朝要灭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救亡什么的,但是清朝灭亡后,我们中国现在不是还是发展的很好的。 李冬君:是的,我觉得清朝灭亡了,丧权辱国也好,屈辱也好,无论是什么,都是一代王朝的事情。 刘刚:中国还在发展,在近代史里发展。为什么近代史要和晚清分开? 近代史是一个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光荣历史。晚清割地卖国都是一代王朝的事情。 李冬君:清朝坚持不下去就灭亡了,但是我们还是朝着近代发展。 刘刚: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讲中国人,实际上是要分开的,晚清的耻辱并不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一代王朝的耻辱,是王朝灭亡了,中国本身还在发展。 王朝灭亡后,我们发展出共和国,乱世有乱世的发展,顺世有顺世的发展,都会发展。 李冬君:现在都强调个体,我们个体是什么样的?我们个体能做什么?你站在的这个地方是中国,那就是你自己,你能为它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行动。 刘刚:冬君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李冬君:我看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特别激动,我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了。很多人看完之后有很多的评价,说不像历史。 我觉得电影艺术首先是镜头语言,他的镜头特别特别慢,我们现在快得自己接受不了慢了,所以很多人批评他的镜头慢。 但是这个慢镜头在拉长的过程中那么有自信地把唐朝文化慢慢地展示出来。空镜头这么长在电影里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从文化角度来看侯孝贤很有自信。 镜头慢慢地展开给你看,就是让你慢慢地去品味,去欣赏。历史传承的真实性在哪里,我觉得是精神传承,他把唐朝人的精神传承给你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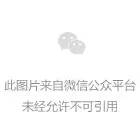 聂隐娘是民间传奇中的人物,是虚拟人物,她说“死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弟子不杀”,就是说她和王朝江山决裂了,她已经厌倦了这种阴谋,她要走向文化江山,所以她不干了,这时候视频就断了,然后她走向了她选择的道路。 这也是侯孝贤的价值选择,他在这部电影里已经预见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从春节前我们两个人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讲,有很多独立书店、独立团体请我们去讲。我一个晚上写了九千多字,写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我说我只是一个外行,不是专业的电影点评,但是从电影里我也看到了文艺复兴的开始。我们这本书也是这样的,是站在世界的角度。 就像刘刚老师讲的,我们要从天下观中走出来,从东西方对立冲突的格局里走出来,然后才能走向一个大同的世界、融合的世界。 我们两个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我们从王朝史观走出来,写了《文化的江山》,从世界史观的角度出发写了《通往立宪之路》,《回到古典世界》也同样是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同一时空东西方发生的历史事件。 同一时空,人类都在建构着什么?所以看中国史一定不能把它当作世界史的地方志来看,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主流部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今天只有我们的历史还没有断,没有断就一定有它内在的魅力。我们复兴国学也好,文化复兴也好,我们要找的是这种没有断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应该断掉的东西,要找那些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 主持人: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今天我们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