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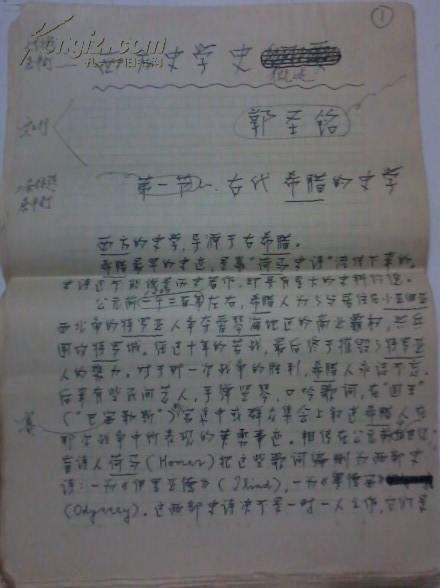  郭先生于1957年调来华师大历史系任教时,我正下放农村劳动,待我在校外转了一大圈,铩羽而归,回到历史系,已经是国家经济灾难深重的1960年年中了。 见到一位陌生的老师,总是那么衣着整洁,腰杆笔挺,言谈举止不紧不慢,端庄方正,有时还稍显笨拙,多少感到有些新奇。接着,就听到不少传闻。说是这位郭先生好不清高,非本组同事绝少来往,礼貌而又矜持;而且孤傲,他写的历史词典条目,竟不容他人改动一句一字。听到这些颇为惊异:从什么时候起,“清高”竟成了一种毛病?“清”不好,难道要“浊”不成?“高”不好,大家都“低”在一起就好了吗?跟种种鸡零狗碎的亲亲疏疏保持距离,不参与家长里短的叽叽喳喳,有什么不好?在那个“无知无畏”的年头,我没有恭逢本系师生共编历史辞典的盛举,却也在别的大学参加过师生“合著”大学教材的“大跃进”,其时,一位“敢”字当头的青年学生就坚持要在“巴黎和会”一章加上“狗咬狗,两嘴毛”这样的生动判语。于是我多少能够想象,对历史人事未识深浅,遣词用字又不知轻重如我等,会跟老先生们怎样的冲撞。郭先生竟甘冒众怨,如此执着和率真,不由我不怀有一丝默默的敬意。 跟郭先生首次直接交谈,还是在两三年之后的一次高考阅卷的午休时间。此前不久,在电影院看到一段插映的古巴短片,说是表现美国社会景象的:在五光十色的繁华大道背后,是破败的穷街陋巷,灯光昏暗中人影幢幢犹如鬼域游魂,爵士乐怪声怪调刺耳揪心,警车呼啸而过,不时划过一声凄厉的枪声,直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这就是美国?眼界开阔的现代青年肯定要失笑了,那时的一位大学教师,而且据说还是专门研究现代世界历史的人,竟然会幼稚到在一段宣传短片面前如此大冒傻气。我问郭先生:你在美国生活多年,美国社会究竟是怎么样的?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浅浅一笑说道:我在美国认识不少美国人,也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很好的人。我听懂了先生的坦诚和谨慎。那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当口,就一个并非毫不敏感的问题,对一个平素交往绝少的青年教师(至少总是个政治积极分子吧?),能讲到这个份上,我很感念先生的信任,更钦佩先生只说真话的勇气。 我之所以对这件小事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不久之后,一个更加荒唐的年头到来了。一代越发愚蠢的人群被煽动起来,我却还没有与时俱进,依旧缺少防人之心,交浅言深,于是屡吃苦头,这时就常常想起先生的沉稳和含蓄来。 对于那时已有四五十岁年纪,颊上烙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金印的先生们,境况就尤其艰难凶险;一言不慎,就会招来不测之祸,一念之差,也可陷自己于不义。1966年8月4日傍晚时分,先生突然被一批年轻学生重新扭回历史系办公室前,被强按在一张高高的小茶几上遭受再次羞辱,说他在下午的全校狂飙横扫之后竟无半点悔罪表现!要如何“表现”才算“悔罪”?要立即灰头土脸,弯腰潜行,急急如鼠窜;先生却怀着一腔不解和愤懑,难以排遣,踱进长风公园,徘徊良久,于是路遇了这批革命小将。施虐者要以被虐者的痛苦取乐,尤其渴求以被虐者的卑怯和下贱来证明自己的强大。郭先生却以一个弱者的凛然自重,拒绝给予满足,在被一再按头逼问中,先生只是发出了一声浩叹:“上有苍天,下有黄土,中间有良心!”我当时也正巧在场,四十年前的这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我注意到,从那时开始,直到文革结束整整十个年头中,先生始终如一,衣着还是那么整洁,步履还是那么沉着,腰杆还是那么笔挺;自不必金刚怒目故做姿态,也没有低三下四自我践踏,更绝不为趋附邀宠去落井下石,没有一天,一时,一刻,出现过一丁点儿下贱相。在那个事事都为制造人格萎缩,时时都在放纵人性退化的岁月里,要能十年如一日地自爱、自重、自尊,需要有怎样岿然的精神定力和人格坚守呀! 这种精神定力和人格坚守,所来何自?多年来我尽管怀着一份默默的敬重,跟先生并没有很多交往,对他的经历和学养更没有深刻了解和直接感受。1971年夏秋,郭先生也来到大丰“五七干校”,才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许先生是以为我这个人心眼还不坏,对我的许多轻率和浮躁的表现又怀着一种长者的宽厚,因而在交往中绝少避忌,让我感受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真实境界。 同在干校的蔬菜班里种菜,也一起二次下放到贴邻的农村生产队里秋收秋种,同住在一家农户的堂屋里;还曾跟另外三位教师一起打起背包,走访大丰、盐城一带的村镇,做“社会调查”,走走看看,问问记记,又时近一个月。在总共半年多的时间里,先生依旧言语不多,一切都处之泰然,淡然,有所交谈,也大多只关乎眼前生活和劳动的日常事物,不过,有几件事却让我心头一个激凌,留下深刻印象。 在劳动间隙的休息时间,先生常常喜欢独处;放下农具,重重地吁一口气,叉腰站到河堤高处,放眼远望。有难言隐痛?有浩渺心事?不得而知,更不便唐突多问。有天,几个人坐在宿舍门口聊天,我说到一位“三结合”的干部如何在“教育革命”问题上前后不一,努力揣摩上意以保证永远正确,先生突然从旁插上一句:“这就叫巧宦。”“哈”,我一拍大腿,“就是这两个字!”我说了一大堆,硬是找不到这么一语中的概括。在步行走访中,我们究竟获得多少革命理论的新印证,已经很惘然了,倒是跟先生一起长时间欣赏农民如何杀猪、做豆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屠手缓缓地走进猪圈,突然弯腰一抄手,提起了那头肥猪的一条后腿,像推小车那样让猪乖乖地自己走到场地中央的作凳旁边,帮手过来猛然抄手提起同侧的一条前腿,“嗨!”的一声,已把它侧躺在作凳上,随即刀进血出,不到半点钟,那条大猪已经在烫水大锅里褪毛,开始露出红润白净的胴体来了。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先生和我看得啧啧称奇!灯光昏暗的豆腐坊里豆香阵阵,热气腾腾。一位点浆师傅俯伏在大木桶边上,一手举着把小茶壶,向桶里慢慢滴注盐卤,一手拿把小铜勺,在浆桶中轻轻划动,让浆液匀匀地流转和翻涌,滴注完毕,桶口蒙上白布,就惬意地坐在一旁静待浆液自然凝结冷却了。活儿做得如此平静精巧,先生同样看得兴味盎然。我觉察到在先生少言寡语平静淡定的表面之下,始终涌动着一种对是非善恶的强烈爱憎,时时饱含着一种关注生民的悲悯情怀。 我们都曾经注意到先生如何写字,常常是举笔在纸页上方摇动有顷,才落纸写上一行,字字如斧劈刀斩。先生常说,史家之笔重千斤,一字之微,都要经得起再三推敲和考验。他的著述和译作,总是那么简约清朗,读起来时时感到一种凝重典雅之美。真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呀!对于那些信手挥洒,摇曳多姿,细细一想却疑点重重的“才子”之作,先生常要哑然失笑,如《李白与杜甫》;至于那种以来历本就可疑的社会名声或权力资源来救济学术之穷困者,先生更是表示不屑,却也有些许无奈。 我也注意过先生怎样读书。翻到上次读过的那一页,攸攸地点起一支烟来,同时目光紧盯着书页,慢慢移动,好长时间,才翻过另一页。在我有限的见识中,先生是这样读书的独一人!我想,这或许就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古训吧!慢慢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跟先生常常是十分短暂而又随意的交谈中,会不时听到先哲的名言隽语,让我振聋发聩:“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每个民族总会得到它该得的领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幅真情激越的明志之联,最早我也是从先生那里听到的。把书读到心里去,从来不把做学问只当作谋生逐利的敲门砖,而是首先把它作为完善人格,进而昌明文化的不二途径;学问,在先生乃是一种生命信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融为一体,功业可有大小,其志则一以贯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表里如一,内外通透的人。 1983年秋,先生应美国国际交流署之邀重访美国。在到达首都华盛顿的当晚,先生电告正在马里兰大学进修的我,在简要说明来访原由之后,告诉我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已被接受为共产党员了。兴奋之情,电话这头的我也清晰可感。我理解先生的这份兴奋:几十年来孜孜矻矻追求民族复兴和社会正义的一腔赤忱,终获承认;几十年来不移不堕,坚守人格,力求完美,终得结果。第二天一早,我如约赶到城里与先生会合,一起高高兴兴地在各大博物馆留连。有趣的是,美方派来全程陪同先生的人,恰是那位一口漂亮京片子的意大利后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博士,他刚刚出版了一部新著:《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我心中暗想,由他来陪同又一位活生生的儒者在美国旧地重游,彼此当有更多心通神会吧。 模模糊糊地以为先生像个真正的儒者,开始只是一些外在感觉:什么都有板有眼,不温不火,淳淳有君子风;随后则感受到一种道德原则:在强势面前不屈不阿,对可教孺子温文敦厚;最后才终于明白先生的文化自觉:信守不渝,且毫不含糊。那时的历史系,每周都有种种名目的集会,散会后常有机会陪先生慢走一程,随便聊聊,前面已经提到的许多让我茅塞顿开的教益,也都来自这种场合。先生对文字改革大不以为然。除了有选择的简化书写以及字母标音尚有情可原之外,全面拉丁化云去,先生斥之为无知妄为,绝对做不得,也绝对做不到;至于竟有某某文化“大家”也来著文高调鼓吹,那就更是迹近曲学阿世了。先生也反对“全盘西化”之类的空泛诉求,以为此类高论大多是既不懂“中”的底蕴,也不知“西”为何物的幼稚冲动。学养浅薄的我,通常只是个好奇的提问者和倾听者,对先生的这类议论难以置喙,只是进一步感受到一种自觉的文化守护者的热情和真诚。在先生的<<九十自叙>>中读到“我一生读书,至今笃信儒学”,正是,正是,这份诚信笃行的文化信仰,正是先生修身、治学、执教,从日常待人接物直至应对重大突变的精神定力之所在。 先生以九十高寿遽然仙逝,一种无奈的愧悔和莫名的悲哀油然而生。惭愧的是,对先生的体察和理解常有愚钝迟滞的时候,也曾不慎唐突;懊悔的是,在可以向先生多多请益的时候,太欠勤谨,忽忽轻放了。先生远去,更意味着一代学人的最后消陨。那一代学人,曾是我们亲近过的唯一拥有完整文化素养的一代人。他们少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稍长又得现代教育培养,经过社会动荡的急浪冲淘,能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本就不多了。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或早早中箭落马,从此沉没,更多的则噤口失声,虚掷学术生命于期期艾艾和唯唯喏喏之中凡三十年。本该接续这学术、教育和文化传统传承之命的我们这一代,那时大多还只是懵懂少年,却在一时风尚的鼓荡之下,转过背去,一头扎进无谓的折腾之中。三十年糟蹋,一片荒漠,传承之命,早就悬于一线,细若游丝。回头重来拣拾,能得几多?先生们垂垂老矣,还做最后一搏,多少抢回几年时光;我们则已早生华发,紧急恶补,终成夹生饭一锅。学术水准的一时下降,经过三二代人的努力,或可停损和复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加大投入多少总有收益吧,譬如,来点《四库全书》式的盛世豪华文化工程也是意中之事。文化人格,学术道德,就不见得是同一回事了。它本来就是靠着一代代学人亲密接触,彼此熏陶浸润,传承积淀而来;一旦沦丧,斯人已逝,接续何在?先生的一幅对子说:“身心健,于愿足矣;子孙贤,此外何求?”那是先生在历尽曲波终保固有的文化人格于不堕,学术劳作也终有所成之后的一种欣慰和旷达。我们呢?如果对文化传统全然无知无觉倒也罢了,偏偏略有所悟,却又只能眼看它绝尘而去,那才叫于心耿耿。如还能跟先生请益,这才是我要向先生坦陈的心声。先生何以再给我最后一教?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