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及北方地区连续出土了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它们分别是:宁夏固原南郊隋唐墓、甘肃天水石马坪墓、山西太原隋虞弘墓、西安坑底寨北周安伽墓、井上村北周史君墓等。这批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大多保存有较为完好的石棺椁、石屏风、石床等石质葬具,在部分石板上雕刻有内容丰富的画像,引起学术界强烈的关注。无独有偶,在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考古发现的一批墓葬资料中,也发现了一批彩绘在木棺板或木质随葬器物上的图像。这两批考古材料的出土十分珍贵难得,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古时期活跃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和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吐蕃人社会生活的若干断面。由于两者都是在作为葬具的棺椁板材上绘制或雕刻画像,我们在广义上或可以将其统称之为“棺板装饰传统”,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共同因素。 上述入华粟特人的石椁浮雕与吐蕃棺板画除了材质的不同之外(前者使用石材,后者使用木材),都是由数块石板或木板组成,主要作用为葬具上的装饰图案,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彰显死者在生前与死后所能享受到的若干殊荣优待。从画面的表现形式而论,粟特人石棺浮雕主要画面有骑射狩猎、商队出行、帐外乐舞宴饮、帐中主人宴饮、丧葬仪式等,虽然各个画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彼此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祈求死者亡灵顺利升入天国,并在天国享受到与生前同样荣华富贵的生活。青海出土的吐蕃棺板画的情况与之极为相似,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由骑射狩猎、驼队出行、帐外宴饮乐舞、帐中主人宴饮和丧葬仪式等不同画面组成,笔者认为虽然其画面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若干场景,但其中心意义同样是反映出吐蕃具有浓厚本教色彩的丧葬礼仪。尽管两者在画面中出现的人物服饰、器皿、牲畜种类、舞蹈及乐器等还有不尽相同之处,具有各自的民族与地域特点,但在图像中所反映出的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却是一致的,而这些传统在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中流行甚广,许多应当是来自中亚与西域文明。 骑射狩猎 安伽、虞弘、史君等入华粟特人的石刻画像中都出现了大量骑射狩猎的场面,动物被骑马的人物追杀射击,正在惊恐逃窜。同样的画面在青海发现的吐蕃棺板画上也有形象生动的描绘。只是前者图像中被射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常见的羚羊、野鹿、野猪、兔子等动物,而在青海吐蕃棺板画被追杀的动物中还出现了野牦牛、长角鹿、藏羚羊等青藏高原常见的动物。 狩猎题材的画像在世界古代各民族中都有流行,我国战国、汉代陶器与青铜器上也出现过此类题材,有的还绘在墓葬的墙壁上。早年徐中舒先生曾撰有《古代狩猎图像考》一文,对我国先秦时期铜器纹饰中的狩猎图像作过精深考订,并从东西交通的角度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中古时期粟特人的狩猎图像应另有其来源,不属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系统。从中亚伊朗考古学资料来看,这类图像题材在年代为5~7 世纪的波斯萨珊银盘上十分常见,银盘上的人物往往头戴王冠,腰悬箭囊和短剑,正在执弓射杀动物,被狩猎的动物有山羊、鹿、猪、狮子、豹子等。画面上骑马人物与被追杀动物的构图方式、骑射者手执弓箭猎杀动物的姿态与中土发现的粟特、吐蕃棺板画上的图像均有相似之处。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波斯萨珊银盘 例如,史君墓石堂西壁编号为W3 的浮雕图像中,画面的上部正中为一骑马手执弯弓射箭的男子,头戴帽,身穿交领紧身窄袖衣,腰束带,腰间悬挂有箭囊,右手持弓,左臂抬起做射箭状,马前有五只动物,其中一只已中箭倒地,其余四只正在惊惶奔跑,种类依次是雄羊、羚羊、野猪和兔子。另有两只猎犬在奔逃的动物两侧,协助主人射杀。这与波斯萨珊银盘上的“帝王骑射图像”意匠完全相同。尤其是在虞弘墓中还刻有人物骑骆驼与野兽搏斗的场面,齐东方先生认为:“人物骑骆驼与野兽搏斗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图像系统,中亚西亚却有许多实例。”青海吐蕃棺板画上往往也在起首位置绘有类似的骑射狩猎图。例如,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 板的起首在棺板左下画一人骑马引弓,马前有三头奔鹿,其中一鹿已中箭流血即将倒地,另二鹿惊惶逃跑。其上为一射杀牦牛的场面,画中有三位骑手正在追杀两头牦牛,其中一头牦牛已中箭,但仍负痛奔走逃避,牦牛的下方,一条猎犬追堵着牦牛的逃路,表现出与粟特和波斯狩猎图像中相同的艺术意趣与图像风格。  史君墓石椁狩猎与商队图 商队出行 饶有兴味的是,在入华粟特人墓葬石刻中,常常与骑射狩猎图像并行的还有商队出行图。例如,上举史君墓石堂西壁W3 号石刻图像的下部,是一个由马、骆驼和驴组成的商队,商队的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腰上挂着箭囊,两匹马的后面是两头驮载着货物的骆驼,骆驼后面跟着一位头戴船形帽的男子,骑马行进,右臂弯曲上举,右手握望筒正在向远处张望,两头骆驼的右上方,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驮载货物并行,其后面为一男子正持鞭驱赶其前行。与这幅图像相邻的石堂北面编号为N1 的画像上部中心位置绘有一帐篷,帐内外有人相对而饮,而画面的下部出现了一个正在休息的商队,中间有两位男子正在交谈,一人肩上还背着货囊,有一人牵着载货的马匹,一人照料着两匹驮载着货物的骆驼卧地休息,后面还跟着两头驮着包裹的驴子。与这类画面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入华粟特人系统的墓葬石刻画像中,如日本Miho 博物馆内的一幅石椁石刻。  Miho美术馆藏石棺床商旅图 青海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 板的情形与上述粟特人的商队十分相似:在狩猎图像的前方,画有一支骆队,中间为一驼,满载着货物,驼前三骑,驼后一骑,前后相继,驼后一人头上缠巾,腰束箭囊,似在武装押运着商队前行。此外,青海郭里木现已流失于民间的一具棺板画的起首也绘有射猎场面,身穿吐蕃服饰的骑手手持弓箭、腰系箭囊,从两个方向射杀牦牛,而在这个画面的上方绘着一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货物上覆盖着带有条纹的织物,骆驼后面跟随一骑马人,头上戴着似“山”字形的船形帽,似为押运货物的人员。 荣新江先生曾根据史君墓及其他粟特人系统石刻画像中的这类图像加以研究考证,认为这就是一个中古时期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的写照(尽管这个商队中种族的构成除了粟特人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墓主人的族属目前有吐蕃、苏毗、吐谷浑等不同意见,我们暂且将这一争论搁置一边,因为如同有的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在不断扩张与征服基础上形成的吐蕃王国,也是由许多民族共同体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苏毗、吐谷浑、党项等民族。在吐谷浑当中,即有类似粟特人的商队。《周书·吐谷浑传》记载魏废帝二年(553 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骆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因此,一方面在吐蕃征服占领吐谷浑之后,吐蕃属下的吐谷浑人仍然有可能继续可以组成这样的商队进行丝路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吐蕃人出入中亚地区的军事征服与领土扩张,而忽略其在丝路贸易中扮演的角色。 联系青海所出棺板上的画像内容来看,吐蕃人很可能也继承了中亚民族丝绸贸易的传统,同样有规模不等的商队活动在“高原丝绸之路”上。有学者曾经指出,吐蕃的军事扩张也具有鲜明的商业目的,其在西域和河西一带的军事扩张大多与控制国际商贸通道有关,同时也将丝绸等重要国际贸易物品作为自己掠夺的主要对象,这与“善商贾”的粟特人虽然采取的方式各异,但却能收到同样的功效。 帐外宴饮乐舞 入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中还甚为流行帐外宴饮乐舞场面。例如,安伽墓后屏六幅图像中自左向右第一幅即为乐舞图,上半部为奏乐合唱图,下半部为舞蹈图,奏乐者演奏的乐器有琵琶、箜篌等,舞蹈者双手相握举过头顶,扭腰摆臀向后抬右脚,正在跳着“胡旋舞”。与之相邻的第二幅图上方出现了主人形象,头戴虚帽,身穿圆领紧身袍,腰系带,足蹬靴,右手持角杯屈右腿而坐,其左前方方形的地毯上坐有三位乐人,分别演奏箜篌、竖笛和火不思。后屏的第六幅图也是一幅宴饮乐舞图,主人坐于一座汉式亭子当中,下方正中一人身着红色翻领紧身长袍正在跳着“胡旋舞”,左右各有数人为其击掌叫好。类似的画面也见于此墓右侧石屏。  安伽墓宴饮乐舞图 青海吐蕃木棺板画中也有不少帐外宴饮乐舞场面,如上面所例举的一具现已流散于民间的吐蕃棺板画上,在大帐外设有一四足胡床,主人身穿翻领长袍、头上缠高头巾,坐于胡床之上,其左侧有人侍立,面前一人正屈身弯腰向其敬礼。 主人右后方站立有一排五位乐人,手中各执乐器正在演奏,面对主人的空地上一舞者头戴高冠,一只长袖高举过头正在起舞,左后方一排四人席地而坐,正在观看表演。在大帐后方绘有一树,树下拴有两匹虽然带有马鞍却已无人乘骑的马,神态安然悠闲。 这种在野外设帐歌舞宴饮的习俗,主要流行于北方游牧民族当中,而乐舞中的“胡旋舞”是中古时期流行于西域胡族继而传播到汉地的一种民族舞蹈。安伽墓中反映的多为中亚人的生活情景,而吐蕃棺板画中出现的乐舞场面从构图方式与表现手法上都体现出了与粟特人相同的特点。现存于西藏拉萨市大昭寺内的一个吐蕃时期银瓶上曾出现有身穿吐蕃胡装、正跳着“胡旋舞”的人物和饮酒大醉的场面,和青海吐蕃棺板画上的画面十分近似,所以我们认为这一传统主要也是受到中亚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帐中主人宴饮 与帐外歌舞宴饮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帐中主人的宴饮图。这类图像在入华粟特人墓葬石刻中表达得非常充分,在青海吐蕃棺板画中也多处出现主人帐内宴饮的场面,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观察分析两者的特点。 首先,是这种帐篷的形制。如在安伽墓左屏刻绘的三幅图像中,第三幅为“野宴图”,帐篷的形制为圆形虎皮帐篷,圆顶,门楣一周及左右竖框上涂有红彩加以装饰,帐中铺地毯,主人在帐内席地而坐。此墓后屏的六幅图像中,第四幅和第五幅图像中都有帐篷设立在会盟、宴饮等不同场合,但形制却各有差别。例如,其中第五幅“野宴商旅图”中出现的帐篷与左屏所刻第三幅画像相同,特点都是虎皮圆形帐篷,门两侧及顶部涂有红彩,门内及顶部设有帷幔,地面上铺设地毯。而在后屏的第四幅石刻中,下方设有一帐,帐顶正视为方形,帐顶似为织物,正中央镶嵌有日月形图案,带有檐、柱,形制显然不同于圆形的虎皮帐篷。由此看来,在入华粟特人的生活习俗中,大概只有设在郊外用于“野宴”的帐篷才是圆形。青海吐蕃墓葬棺板画的最后也是最高潮部分往往都是围绕着中心大帐展开的宴饮场面,帐篷的形制均为圆形,前方设门,门帘可以收卷在帐门上方,门帘和门框的两侧有色彩艳丽的镶边,顶部开设有圆形的气孔,呈喇叭形向上翻卷。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这种圆形的帐篷也称为“拂庐”:“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城郭而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甚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既然是与“城郭”相对应的一种居住形式,看来这种“拂庐”大概也都设在野外,与粟特人“野宴”所使用的帐篷形制大致相仿。 其次,是对出现在帐中主人形象的设计。仍以安伽墓为例,安伽墓左侧屏第三幅“野宴图”帐内坐有三人,门外有四人侍立于侧,可见帐内三人当系地位较高的首领人物。另在此墓后屏的第一至六块石板上,也都刻画出不同场合下出现的主人形象,在人物的布局设计上,居于帐中的主人一般都面朝帐门席地而坐,除了会见宾客之外,还有主人夫妻对坐或对饮的场景,主人的服饰特点往往也最能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在虞弘墓后壁居中部位的石板雕绘中也可见到类似的画面。画面中在大帐中间设有亭台,帐内坐着墓主人夫妇,作相对而饮状,在他们的身后,各有两名男女侍从两两相对,主人和侍者前面的场地上,有六名男子组成的乐队,中间有一男子正在跳“胡腾舞”。 日本Miho 博物馆藏石棺床画像石后屏E 图当中,描绘了一幅在穹顶大帐之下的主人夫妇宴乐图,主人前面乐队正在奏乐,舞者正在起舞。郑岩对此评论说:“此画像石之此部分对于揭示与中亚的连接点非常重要。乐队与飞动的舞人,是6~9 世纪从北齐到隋唐陶制扁壶上反复出现的图像。扁壶及此棺床浮雕舞人的舞蹈称胡旋舞。” 荣新江在分析对比了这些男女人物形象之后认为,他们的身份应是粟特部落中的“萨保”:“从以上这些图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萨保居于中心位置,他所居住的建筑物,有中国式的歇山顶厅堂,也有游牧民族的毡帐,这是东来粟特人分别生活在汉地和游牧汗国当中的反映……这些图像表现了萨保在聚落中生活的场景和他作为首领的核心地位。” 青海吐蕃棺板画上也绘有地位突出的人物出现在宴饮场面或帐篷当中,画面上人物的安排方式与粟特人也十分相似。例如,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 板所绘的宴饮图上,大帐门前左右各立一人正在迎接客人,帐篷的门帘卷起,可见帐内有对坐的举杯对饮的一对男女,男子头上缠有高头巾,身着翻领长袍;女子头戴巾,也身穿同样的翻领长袍。帐外是有众多男女参加的盛大的酒宴场面,围绕这座大帐展开。很显然,居于大帐之中的这对男女地位显赫,许新国将其比定为吐蕃的“赞普”与“赞蒙”(即王与王后),笔者认为他们至少也应当是当地部落中的权贵人物。  郭里木一号棺板画宴饮图 分析比较粟特人与吐蕃人的宴饮场面,它们均是以大帐作为画面的中心,在大帐之内常常绘有主人夫妇对坐而饮的画面,大帐之外都有侍从服侍于左右,帐前均出现歌舞宴饮的人群,类似这样的画面,在粟特人故乡撒马尔罕一带发现的考古遗存中屡有发现。姜伯勤先生曾指出,在巴拉雷克切佩北墙和片治肯特等地所绘粟特人的壁画上,便有这样的宴饮图出现;另在粟特出土的银酒器上,也有类似这样的男女对饮图。此外,中亚一带突厥部落中也多流行帐中宴饮习俗,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因此,我们通过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粟特人与吐蕃人的帐中主人(常常是以男女夫妇对坐的形式出现)宴饮的题材,曾经主要流行于中亚粟特人当中,随着突厥部落的祆教化,在突厥人当中也有流行。但与之同时,这一习俗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当中也曾经同样流行,所以在棺板画中也采用了这些在意境上相似的画面。 丧葬仪式 在粟特人的石板雕绘中,多有丧葬场面,并且出现了祆教师主持拜火祭祀的场景,反映了祆教流行的葬礼仪节,对此前贤论之甚详,本文从略。可以相互比较的是,在青海吐蕃棺板画上,也绘有反映丧葬礼仪的若干场面。 在郭里木一号棺板画的B棺板画面上,棺板的右下一个画面中设有一座灵帐,灵帐的式样与宴饮场面中的大帐篷别无二致,上面覆盖有连珠纹样的织物,顶部也留有气孔。帐前设门,门前有跪地奠拜的三人,与之相对位置上一人正屈身面向灵帐,双手似捧有供品向死者献祭(可惜手部画面已残损而无法看清)。背对灵帐站立着头上缠有头巾的三人,正垂首默哀;而灵帐上方并列站有一排四位女子,领前一位脸上挂着下垂的巨大泪痕,表情极其悲伤,与之并列的其他三位女子也都面呈哀痛神情。罗世平先生认为:“这两组夹侍灵帐的男女人物,是死者的亲属,他们为死者守灵,接受前来的吊唁者。”从画面上还可以观察到,灵帐的下摆随风飘动,露出帐内陈有的长方形物体,是否为盛敛死者遗体的棺具不得而知。罗世平还描述说:“门帘开处,依稀可见类似棺木的彩画线条(因画面过于模糊,不能确认其形)。”如果这一观察无误,灵帐内陈有死者棺具的可能性很大。 另一具流散于民间的吐蕃棺板画上,在木棺中部位置上设有一呈须弥座式的台子,台上置有一具黑色棺木,棺由棺盖与棺身构成,棺的一侧有三名守灵人,面呈悲色;棺台左前方在两根立木之间树立有一裸体人像,一骑手正引弓向其射击,另一骑手反身作射箭状也指向裸体人形;在棺的上方,绘出前来奔丧的一队宾客,衣着冠饰各不相同,队中高树一华盖;棺前一人已下马站定,正面向棺木拱手致哀。 有学者曾经以史君墓石椁为例分析过此墓石刻各画面之间的相互关联,认为“从石椁东壁的浮雕内容来看,画面即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彼此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E1、E2、E3 的底本实际上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因石椁模仿木构的殿堂,而被立柱人为地分成3 部分,但画面的内容从北到南紧密相连,展示了粟特人去世后亡灵升入天国的整个过程”。青海吐蕃棺板画的各个画面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模仿了人间社会生活的若干场景,但笔者认为其核心内容也是围绕死者的丧葬仪式展开。罗世平先生指出,郭里木一号棺板画上的B 板“各画面描绘的是一次葬礼的几个典型情节,吐蕃画家用纪实的手法,再现了一位吐蕃赞普的葬礼”。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粟特人是依照祆教的丧葬仪轨举行死者的葬礼,而吐蕃人则是依照本教的丧葬仪轨举行死者的葬礼,这在画面上显示出明显的区别,但两者希望表达死者亡灵在死后入升天国的祈愿则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中国本土出土的这批入华粟特人的棺椁装饰从形式上看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的某些丧葬习俗,逐渐开始接受中国汉文化的一些内容,但就其棺椁装饰图像所反映出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而言,却仍然保留了浓厚的中亚文化色彩。而青海吐蕃出土的木棺板画,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从题材内容上看,都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之间具有若干共同之点,体现出吐蕃作为当时雄踞亚洲腹地的强大高原帝国受到西域和中亚文化影响而打下的深刻历史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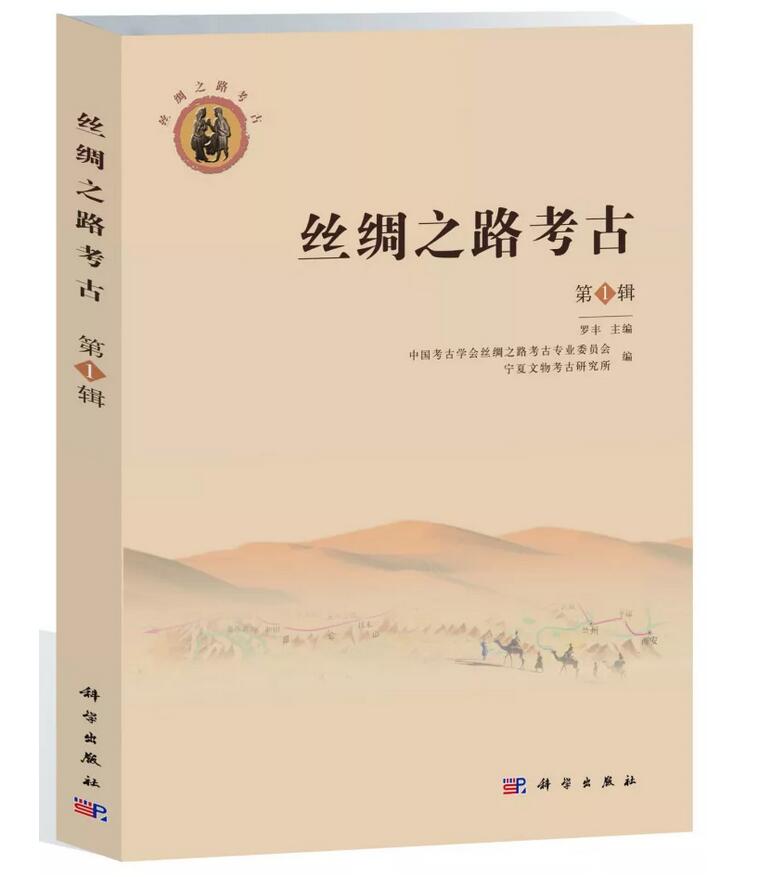 本书是由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筹备出版的系列图书,计划每年出版1-2册。以介绍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的学术著作书评为主要内容。本辑收录论文12篇,书评4篇。 (本文由孙莉摘编自 罗丰主编,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丝绸之路考古(第1辑)》之“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