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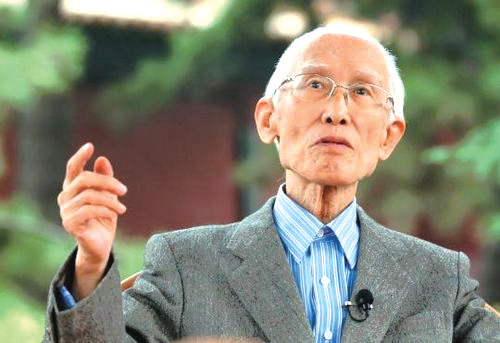
余光中先生曾在一本自选集的自序中说:“许多读者识我的诗,都始于《乡愁》,但愿他们能更深入,而不止于《乡愁》。”
《乡愁》的好处在于克制,不直接言愁,也不铺排情愫,只是在寥寥几段形式整饬的诗句中,通过四个递进的事物: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不着一字“愁”却又将“愁”毫发毕现。在其更多的和“乡”有关的诗歌中,这种“愁”也并不喷薄泛滥,它的内部丰盈且存在时空,并将时空带入事物,带入人本身,不言愁而愁自现。
“暴风雨的另一端,有谁看钟表”
乡愁的本质不是愁,是记忆与阻隔的矛盾,是时和空的共同作用。“时”是不可回的时,“空”是不可抵的空(虽然现实中已可抵,但隔断和追寻已深入骨髓)。因为有旧日记忆,所以心中有“乡”,又因为不可回转且不可抵达,而生“愁”之念。所以,乡愁在余光中的诗中常体现为时间和空间的交杂。
一种是设置时空矛盾:在《春天,遂想起》一诗中,作者忆念的江南前面放置了特殊的定语:“(从松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任伊老了,在江南/(喷射云三小时的江南)”。三小时在时间意义上并不长,但结尾又出现一句:“(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时间上接近、空间上却无法归去的矛盾设置,让情感更为婉曲复杂,增加了“愁”的纵深。
另一种是时空并置:在《嘉陵江水》中,“就那样走下了码头,走上甲板/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年年西望的壮年啊中年啊暮年”。空间从码头、甲板一直延伸到海外,并在尽头处进入时间,而时间几乎贯穿了人的大半生。一边是渐渐远去,一边是渐渐老去,空间的“远”依靠时间的“老”来完成,增添了表述的重量。
乡愁在物里显形并定影
乡愁中的时和空,在余光中的诗歌中常常落地到具象的形象。对这些形象的反复书写,构成了一个个的意象链。作为意象的事物被诗的时空赋予更深的象征和旨归,内蕴了文化记忆和隐秘的情感。在诗中,一个物的名字便是一段深情。
除了用鹧鸪、月亮等常见意象来表达乡思外,余光中还有一些偏好的属己的意象。
坟,它是一种阻隔,也是一种通路。在《乡愁》中,“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作为后面“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铺垫和序曲,“坟”的意象递进了邮票、船票的力度,也增加了“一湾浅浅的海峡”的沉重感。坟带来的绝对的隔绝与“浅浅”形成对比的张力。没有什么比死亡更难逾越,坟墓代表死亡,将乡愁的“愁”推到绝地。
在另一首诗《招魂的短笛》中,作者写到:“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梦见你的母亲”。余光中的母亲是江苏武进人,但和他的父亲合葬于碧潭永春祠堂(“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浪子回头》),在诗人的心里,母亲的坟是应该在她的出生地的。这里的“坟”,比《乡愁》中的“坟墓”更进了一步,它不止是一种隔断,更是一种通路。这种通路,必须在故乡的土壤里,叶落归根,第二年春天才能长出新的叶子。“坟”也变成了连接,连接逝日并促成复活。在故土的滋养下,灵魂回归,母亲变成小女孩,遇见自己的母亲。
在余光中的诗中,坟墓隔绝的总是“我”和母亲,而他的诗中也有很多有关“寻母”的表述。在他的乡愁里,母亲和故乡是一体的,寻母,也是一种寻乡。
余光中的诗中,书写过一些中华的文物。在白玉苦瓜里,有“一个自足的宇宙”,它囊括了中华的乾坤和古今。苦中有乱世:“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也有漫长时间的疗愈力量:“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苦尽数消弭在永恒中,“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白玉苦瓜》全诗都只在写一只白玉苦瓜,但是苦瓜里安放了整个中华。
《唐马》中,唐三彩马有着“暖黄冷绿的三彩釉身”,幽禁在玻璃柜里,身上负载“一千多年前/居庸关外的风沙”。这匹马被赋予不死之身,在中华文化的永恒里奔跑。然而真正在奔跑的不是唐马(唐马是静止的),而是时间。历史在“唐马”身上流逝,旧日豪杰俱往,今日骏马奔驰的地方,已从金戈铁马的战场变为赛马场。“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胡骑与羌兵?不,银杯和银盾”。这是诗人的悲慨,也是历史的变迁。
除了文物,余光中的诗中还有许多寻常事物。诗歌借助常见之物来打通时空,重返旧日温情:一碗香软的地瓜粥,配上豆腐乳、萝卜干……便将人从眼下的餐桌接到在故土的旧日——“古老的记忆便带我/灯下又回到儿时”(《粥颂》)。在答谢柯灵的《宜兴茶壶》中,一把由别人捎回的朋友送的茶壶,因为烧炼自江南沃土,便在壶中开启了一条通道,可以“伸过手去跟后土的上面/她所有的孩子一起握手”。
乡愁是病肠,是血液,是人本身
乡愁在客观的“物”里,但究其本源,更是一种根植于记忆的病症,如作者在《新大陆之晨》中所写:“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病症发源于身体,也作用于身体。在余光中的诗中,“愁”常由外在事物为载体,逗引出藏在身体深处的隐疾。自此,“乡愁”主题便和生命糅合,从一种情绪之“愁”变为切肤之痛。
在余光中的诗歌中,乡愁之“乡”,并不惟一固定。他停留过很多地方,四川、南京、厦门、香港……曾经踏足的地域,但凡哺育灵魂,滋养生命,扎根记忆,便都进入过他的乡愁体系。
在《别香港》中,“如果离别是一把快刀/青锋一闪而过/就将我刨了吧,刨/刨成两段呼痛的断藕/一段,叫从此/一段,叫从前”。时间的分割在肉体上发生作用,离别带来的不止是精神上的愁,更是身体的割裂。
《中国结》则是从墙上的中国结开始,呼应到肚子里的另一个“中国结”:“像是先民,怕忘记什么似的/打一个结在绳上,每到清明/或是中秋,就隐隐地牵痛/会做噩梦,会消化不良”。携带记忆和阻隔的乡愁成了一段病肠,身体便有了空间感。这段病肠的医治,要“探回患处”,慢慢轻轻地解,这患处便是“靠近童年”的“对岸青山”,于是故土同化为身体的部分,乡愁便从“愁”走向“痛”。
这种痛以各种形式闪现,比如海棠。在《海棠纹身》中,主人公发现在左胸口有一小块不知从何而来的伤痕。“直到晚年/心脏发痛的那天/从镜中的裸身他发现/那块疤,那块疤已长大/谁当胸一掌的手印/一只血蟹,一张海棠纹身/那扭曲变貌的图形他惊视/那海棠/究竟是外伤/还是内伤/再也分不清”。如果只看这一个文本,并不能确定这痛是来自乡愁,但是一个人的不同作品是一个互相呼应的系统,在《乡愁四韵》中,诗人以四种事物书写乡愁,其中便有海棠:可见,海棠纹身,便是乡愁的烧痛,伤口看似在皮肤之外,但连接心脏。而中国结和海棠都是红色,如同烧烫血液,在人的体内翻滚。
类似的表述还有“半世纪贪馋的无助/把我辘辘的饥肠/熊熊烧烫,交给了火锅/蜀入了我”(《成都行》),或是用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所有的故土,蜀地也好,西湖、太湖也好,都进入了身体。在这些诗句中,乡愁已不止是邮票,船票等事物、它已经内化,成为了人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