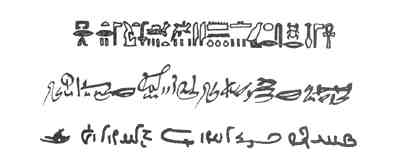 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文中的“文献史料”(Documentarysources)和“文学史料”(Literarysources)的区别。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著作中常常提到的“文献史料”(literature),实为非文献史料(Non documentarysources)和文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著述,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等。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者误以为主要以文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handorprimarysources)或原始资料(Original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著依托于古代典籍,做到无一句无出处,便自可达到信史的高度。所以,我们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著作、授课讲稿和成果鉴定中常可看到、听到这样的表述:某书或本书依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全书原始史料丰富扎实等。但翻开有关史著却发现,所谓“第一手史料”或“原始资料”大多并非第一手或原始性的,而基本上是非同代史家的描述。类似的模糊认识也可在部分现代西方史家的著作中看到。在每年问世的众多西洋古史著作的页下或文后,都整齐排列着大段大段的注释,标明论述中各种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的出处。其中颇具功力的作品可以说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但相当一批史家只追问到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阿等古典作家为止,不再认真地计较这些作家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他们实际上把古典作家的记载同样类同于一手或原始史料,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同我国史家的工作一样,力求在故纸堆中寻找能够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进而取得成一家之言或具有新意的文本解读的学术成就。这就需要澄清几个史学研究的常识问题:什么是一手史料?它和二手史料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一手史料是否等同于历史事实?如果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我们便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还原和解释客观历史的工作,历史势必会变成由一系列误会组成的糊涂账,从而应了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是“我们在死人身上玩的一堆把戏。”①在西方史学概论教科书中,一手史料(限于文字史料)被定义为“一种作品,其成文时间与所研究的时期或题目属于同一时期或几乎属于同一时期。”②这种定义正确指出了一手①②肯特与斯奇内德:《如何研究历史》(NormanF.Cantor&RichardI.Schneider,HowtoStudyHistory),纽约,1967年,第22页。吉尔德哈斯:《历史与历史家》(MarkT.Gilderhus,History&Historians),新泽西,1987年,第2页。严格说来,此处的转引也非一手史料。笔者并没有找到伏尔泰有关论述的原作,完全不知此句的上下文关系。史料与特定历史事物或人物的共时性,却忽略了一手史料的作者和与之共时的历史现象之间所应具有的直接参与或经验的关系。共时史料的提供者可能在空间上完全是历史事件的局外人,如一位埃及人若撰写了同时代的西亚史,他得到的可能一开始就是传闻失实的史料,然后再经过多次转手。这样的史料当然不能算作一手史料。笔者以为,一手史料应指某种特定历史现象的目击者和当事人留下的实物、文字和口头的陈述,类似于司法侦察中做案者在做案现场遗留的痕迹或法律诉讼中所提供的人证、物证和书证。它是已逝过去的原生态的一种体现,为历史工作者寻找并确认历史事实提供了原始的资料和信息。按照这一定义,史前人类的化石及其遗下的石器、骨器、美术作品、居住遗址等实物,文明时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与一次性的客观历史共时同代的各种著述、法律文书、档案文献、公私信件、声像作品、口述历史等均可视为一手史料。例如,汉谟拉比的书信、赫梯法典、梭伦、萨福、提尔泰的残诗、色诺芬的《长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等作品均可列为一手史料。按照这一定义,公元前4世纪问世的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虽然是研究同时代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一手史料,但却不能说是研究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一手史料。同样,李维的《罗马史》是研究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史学思想的一手史料,却不是研究共和时期平民和贵族斗争的一手史料。在这些问题上,《政治学》和《罗马史》均属于二手史料。所谓二手史料,是指非目击者和非当事人对某个特定的客观历史事物的文字或口头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次生的,是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某种描述、解释和判断,甚至想象。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阿庇安的《罗马史》等史著便属于二手史料。希罗多德的《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属于二手史料,而关于希波战争的部分情节却因出自目击者或当事人的口述,则可列为一手史料。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许多内容虽属一手史料,但至少演说词部分,如叙拉古公民大会关于如何应对雅典远征军的辩论词便属于二手史料。所以,一部以一手史料为主的书中可能包含着二手史料,一部以二手史料的书中也可能含有一手史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以共时性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志。我们知道,在史学研究中,收集史料,尤其是收集一手史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比较选题、收集、筛选、分析史料和归纳观点这一研究工作的流程,收集史料是花费气力最大的一道工序,一般要占工作量的六成以上。一部史作的一手史料多,表明作者功夫到家,即使没有制作出新的体系、概括出新的观点,这部史作也可视为一部扎实的好作品。相反,只有高谈阔论而缺乏史料依托的著作,向来不被专业史学看重。所以我们的学术鉴定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明某参评项目之所以优异,是由于该项目史料详实可靠,结论建立在一手史料基础之上。然而,一手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原貌,它虽较二手史料更接近历史真实,或者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的某个部位,但接近不等于同一,某个部位不等于全貌。一手史料和历史原貌完全相左的例子也不乏见。因此评判古史研究成果的标准还应包括作者是否对一手史料进行过认真的考据辨伪,这里才真正体现了史家在史学微观领域的过硬功夫。古代史家对史学研究的这道工序曾有过深刻的阐释。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指出,史家对手头的任何史料,即使是目击者或当事人提供的史料也不能轻信,即便是个人亲历的事件也不能随意征引,均需经过一个认真地调查核实的过程。他说:“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我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①修昔底德还解释了为什么要审核一手史料。他说这是“因为一些事件的目击者对同一事件并没有提供同样的报道,而且他们的报道依他们拥护一方或另一方、或他们的记忆而有所不同。”②显然,在修昔底德看来,一手史料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当事人和目击者会因个人偏好、利害关系、个人立场等主客观因素而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实际。比如,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老寡头和希罗多德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同是批评雅典民主制的苏格拉底与老寡头又不一样;恺撒的《内战记》试图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和派身上,而西塞罗的书信却在战争责任上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在这种情况下,各家的记载因此走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观察位置的远近也会造成对历史原状的印象发生偏差。同一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身处高低远近的不同位置,观察到事实不只是山峰和山岭的数量区别,还可能是山峰和盆地的质量差异。某些历史事件的核心细节,更是某个或某几个关键的当事人或目击者才能看到。因此对于一手史料必需采取修昔底德的处理方法,对每一细微末节进行精心备至的审核。尽管古代史上的所有当事人和目击者已经死无对证,但我们对现有一手史料起码可以做到多问几个为什么。至于那些出自非当事人之手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不知隐没了多少真实的历史细节,造成了多少差错。需要指出,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记忆不同并不只是由于当事人或目击者主观上很难超然、客观上观察角度和位置有所区别的缘故,而且还限于人类记忆的先天缺憾。耶鲁大学教授约翰逊曾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人类记忆的不可靠性。1929年,纽约华尔街上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一位记者访问了9位目击者,其中9人对爆炸瞬间街头的情况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只有一位退役炮兵军官的说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位记者事后感叹道:“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无意识的撒谎者。”③如果说街头爆炸是稍纵即逝的历史事件,多数目击者发生错判情有可原,那么有充分时间观察的历史事件是否就能够避免无意识的撒谎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记忆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除开前面谈到的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个人好恶的影响之外,还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像头发一样生长,像冰雪一样融化消失。关于记忆的这种不可靠性(忘却和变形)其实是每个人都能体味到的。因此,对于大量观念形态的一手史料也必需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记忆具有可靠的一面,特别是那些被记忆者看来最值得记忆的东西,是可能铭刻在脑子里而历久不变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回忆录或口述史学的价值,这一点对于尚有许多当事人和目击者健在的现当代史尤为88史 学 理 论 研 究①②③约翰逊:《历史学家和历史证据》(HistorianandHistoricalEvidence),纽约,1923年,第24~25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2,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2,2。重要。总体上说,古代世界的历史家尽管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任务和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原则,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的一、二手史料的认识(为史料明确分类是启蒙时代以后的事),他们没能开发出严格的史料考据方法。像李维、普鲁塔克那样不加批判地引用他人著作是相当流行的做法。不过也有例外的现象,古代有些史家还是意识到了道听途说的间接证据与当事人、目击者的直接证据之间的差别,并把历史记载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词之上,首创了一些虽很初步却十分可贵的获取一手史料的方法。在这方面,古代史家中最出众的一位是波里比阿。他曾援引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说,视觉比起听觉来得更真实,所以眼睛比起耳朵来说是更精确的见证。①由于强调眼见为实,他还提出最好的历史家应该是那些具有军政经验的政治家,也就是当事人,②而不是既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的书斋里的学者。为了获取一手史料,得到现场的感觉,他不惜千辛万苦,沿着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路线查勘了一次,实际上运用了现代史学利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学补充正史不足的方法。就历史家求真的执着坚韧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言,波里比阿在西方史学史上是很少有人可比的。③《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也认为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最为可信。他在个人著作的开头便指出: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有许多的撰述,所记内容差别很大,“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瑞斯托布斯曾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的历史,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不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④阿里安显然在这时使用了近代史学常用的史料内证的方法。波里比阿和阿里安看重眼见为实和个人亲历的原因,是因为历史家们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往往是自己所关心的某段历史的局外人,不了解历史的内情。⑤在古代信息传递手段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局外人获悉历史内情的难度是极大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作品是这种局限的一个明显例子。《历史》中有大量关于埃及、米底、波斯、吕底亚宫廷内部的活动,也含有不同时期希腊各邦众多人物以及其他小国君主、部落领袖们言谈举止的记述,甚至包括最高军政会议、宫廷密谋、枕边对话等极端隐秘情节的生动刻画,其间穿插着大量现场录音般的直接引语。这就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希罗多德从哪里得到了如此详细的机密信98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①②③④⑤像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塔西陀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悉内情的史家毕竟是少数。所以,在世界上古史中,哲学史、史学史之类的思想史拥有的一手史料最为详实可靠,经济史中工具的历史也有足够的一手史料依托。古希腊古典时代、古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早期的政治史、社会史,叙述性的一手文字史料较多。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I,前言。近现代也有史家对某一事件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如研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问题的索尔兹伯里,但近现代实地调查所拥有的后勤及装备条件要远胜过古代。波里比阿:Ⅱ,62,2。波里比阿:Ⅻ,27,1。息?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一位不懂近东语言的外国普通旅游者,书中的信息提供者则被笼统地称为“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雅典人”、“马其顿人”、“西西里人”,显然是一些地方上的小人物。所以这些密闻不过是些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而已,是不能当真的。但希罗多德身上有一个现代史学不大留意的优点,就是非常老实厚道,对读者实话实说,不像现代有些学者那样端起架子唬人。比如希罗多德就诚恳地向读者交代过自己并不完全相信已收集到的口头传说,“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规则,就是把各国的传统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①在《历史》的另一处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这条原则:“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决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②既然这个原则适用于整个《历史》,那它也适用于希罗多德采访到的有关希波战争当事人的回忆。这种向读者讲实话的做法,是古典史学最可爱的地方之一。它避免了误导读者,赋予读者以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很值得当代史学借鉴。当然,希罗多德所说的:“原封不动”的直录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轻便的书写工具,人们很难同步做到有言必录。因此他的记录多半是在他采访结束后重新加以回忆、整理的结果。既然系事后回忆,总会有失真的地方,如对史料进行加工,用散文体的爱奥尼亚语对史料的内容加以修饰润色,以及进行归善归恶之类价值评估,从而改变了历史信息的原生状态。对历史进行改动,或者换句话说,人为地制造历史,乃是古代史作中常见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史作那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使古代最严谨的史作,也存在有意编造历史的地方。古代史家并不认为这样做同捏造历史是一回事。他们普遍像悲喜剧作家一样,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生动的道白,如情景对话,在公民大会、元老院、仪典、战场上的演说。关于这类直接引语的来源,古代最杰出、最求实的史家修昔底德曾有过坦白,这也是古典史学那可爱面的又一体现。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讲辞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作者在前言中对此坦言:“至于不同人物发表的演说,无论是战争开始前发表的还是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实际讲过什么话了。这既是对我听到的演说而言,也适用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各种传言。因此,这里所举的演说,是我觉得某些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同时我尽可能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③修昔底德的交代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所有古典作品中的演说,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到波里比阿、恺撒、撒路斯特、李维、狄奥多洛斯、普鲁塔克、塔西陀、撒路斯特、阿庇安、狄奥、约瑟夫斯等史家作品中的演说,包括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安葬仪式上的著名讲演,都是史家个人创作出来的,因此最多只能算作二手史料,有些连二手史料也不是。比如密提林、普拉提亚、叙拉古的公民大会的辩论,修昔底德都没有在场,而且密提林和叙拉09史 学 理 论 研 究①②③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ⅩⅫ,1~2。西方古典史学中的这种诚实作风是非常值得当代史学继承的。希罗多德:《历史》Ⅶ,152。希罗多德:《历史》Ⅱ,123。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