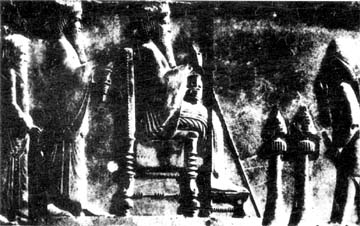 内容摘要:大流士与秦始皇在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为巩固统治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措施。但在为政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两者却表现出巨大差异: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控制较为宽松、经济剥削较为适度、文化政策比较宽容;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则政治统治走向极端专制独裁、经济贪欲恶性膨胀、思想文化统得过死。两人不同的为政治国方略是导致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大流士 秦始皇 治国方略 比较 公元前1000年代中后期,波斯帝国与秦帝国相继兴起于亚洲大陆两端。为了巩固新创的帝国,大流士、秦始皇都进行了改革。大流士在波斯帝国推行了行省制,并实行军政分权,规定贡赋制度,统一币制,修筑驿道等;秦始皇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26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卫、监(实质上也是军政分权)”,“一法度量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始皇27年,“治驰道”,34年,“焚书”,35年,“坑儒”。[1](《秦始皇本纪》) 应该说,两位帝王巩固统一,实行专制的政策和措施是基本相同的。但对两大帝国的历史命运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靠强力建立的松散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的波斯帝国延祚200余年(公元前550-前330年),顺时而立的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公元前221-前206年)就灭亡了。导致两个帝国不同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帝国的创建者──大流士一世与秦始皇的治国方略进行比较辨析来解释上述现象。 一 如何控制被征服地区事关整个帝国的存亡和稳定。为此,除了极力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外,波斯帝国与秦帝国还分别推行了军政分权的行省制和郡县制。大流士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3个行省,每个行省相当于一个被征服的独立国家或民族。大流士治理国家,实行“大统一,小自由”的方针,各行省在保障中央的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享有较多的自治权。这些被征服地区“都保留着它们自己的特性、风俗和法律。各项通行律令对于它们一概都有拘束力,但是并不损害它们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特性,并且保护它们、维持它们,……。有些邦国甚至有它们自己的国王;同时每一国都有它的明显的语言文字、军备、生活方式和风俗礼制”。[2](P230)这说明,大流士一世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是较为宽疏的。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帝国境内各非波斯民族继续保有其多数地方性政策”。[3](P271)中央政府在行使主权时,“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4](P271),在一些行省还“保存有地方的法律(巴比伦、埃及、犹太),地方的度量衡制度,行政区的划分(如埃及之划分为州),租税的不可侵犯性和神庙与祭司集团的各项特权”[5](P606)。尽管大流士曾下令埃及总督,让他修订法律,但根据有关资料判断,该时期埃及法律没有重大改变。巴比伦法律也一仍其旧,“《汉谟拉比法典》仍在继续使用”[6](P199)。日本史学家谢世辉在论及波斯帝国长期延存的原因时首先指出,波斯皇帝“巧妙地利用了旧的机构和各民族的自治”[7](P89)。美国学者也认为,大流士实行了“对隶属民族的宽待与保护政策”,能“宽宏大度地对待被征服民族”[8](P98)。 比较大流士而言,秦始皇对统一于秦帝国之下的山东六国的政治控制则是严密的。郡县制的推行无疑有利于巩固统一,但这一制度毕竟是适应秦帝国统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权组织形式。郡县制特别是郡县下属的乡、里、什、伍编制把人民群众纳入更加严密的统治体系之中,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这种统治、压迫最终激起了被征服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抗。 如何对待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这也是大一统帝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大流士一世十分注意任用被征服地区的上层人士,尤为器重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阶层,给他们以种种恩惠。在帝国的行政机构中,波斯人虽然占据绝对优势,几乎垄断了所有军政要职。但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也吸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在埃及、小亚细亚、巴比伦和其他地区,通常都有本地人担任法官、市长、国家武库管理人。如“在波斯波里斯王室经济中,负责人是波斯人,但会计师却是埃兰人”[6](P96)。在大流士统治时期,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君主通常还都保持着他们的特殊权利”[2](P234)。可以说,大流士吸取了居鲁士的成功经验,有效地罗致了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成功地将这股强大的异己力量和大一统的不利因素,通过怀柔化解为波斯帝国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因此,波斯统治阶级与其所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逐渐合流,他们共同维护着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专制统治。从大流士完成统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被征服地区上层的反抗基本未曾发生,这说明大流士的政策是成功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政策则是残酷镇压和严加防范,基本上没有采取怀柔和利用政策。在统一的新形势下,秦始皇对防止六国贵族死灰复燃倒是颇有警觉性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这种警觉性趋于极端,那么就会将本来即具有强烈反秦思想的六国旧贵族彻底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其成为统一帝国的破坏力量。应该说,这是秦始皇统治政策的一大失误。在其高压政策下,六国旧贵族铤而走险,多次策划了反秦和刺杀秦始皇的行动,而当陈胜登高一呼,六国旧贵族则群起响应,与起义农民联合诛灭了暴秦。 二 与政治上的控制相辅相成,大流士和秦始皇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来维护帝国的统治。大流士很精于此道,他曾进行过法典的编纂工作。《贝希斯敦铭文》中多次提到“国王的法律”,国外权威学者认为这表明大流士时期已经制订了全国统一的法典。[9](P119-134)《贝希斯敦铭文》在言及他的统治方略时指出:“凡忠信之士,我赐予恩典;凡不义之人,我严惩不贷。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上述地区(指二十三个行省)遵守我的法律。凡我给他们的一切命令,他们都遵行不误”[10](P36)。在法律实践上,大流士以法治国,论功过奖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不避显贵”[7](P8),违法者严厉惩处,毫不容情。如吕底亚总督欧洛伊铁司违背中央政令,被处死;某个“行省总督因被告发接受了贿赂,曾被大流士一世下令活活剥去他的皮用来包裹法庭审讯的座椅”[11](V,25),以示法律不可违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以高压手段和严酷立法来维持帝国统治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大流士却掌握适度,执行灵活并有一套完备的司法机构。在名义上,皇帝是最高司法审判者,不过具体审判工作通常由国王委派的亲信或大臣代行。皇帝之下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之下,设若干地方法院,星罗棋布遍于全国。在审理案件时,被告除案情重大者外,审前可保释。审理有一定的程序。案件审理几乎都定有期限,不得随意拖延。波斯的刑罚虽然严酷,但若所犯为单一罪,则依法不能判死刑,加之有完备的司法机构和审判程序,所以在实际运用中处刑比较适度,没有达到“专任刑罚”的程度。此外,大流士统治时期的波斯帝国,“司法界相当清廉,因为贿赂一经证实,行贿与受贿者均是死罪”。[12](P430)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性。 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法治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就曾明言:“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秦始皇吸收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和注重法律教育,这本无可非议。但秦始皇在全面推行法治的实践中,把以法纠恶的观念发展到极端。专任狱吏,取缔私学,轻罪重罚。秦始皇坚信只有重刑才能制止犯罪,在秦律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如,妻背夫逃亡,秦律规定:“当黥城旦舂”;又如,近亲通婚本属道德问题,秦律处以最严厉的“弃市”;再如,“盗马者死,盗牛者加”[13](P233-234),盗一匹马就处死刑,盗一头牛就比常刑加重,这显然是轻罪重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新颁布的刑律,如,“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弃市”、“失期者斩”等,这不仅是轻罪重罚的问题,有的完全是无罪滥罚了。 轻罪重罚,从秦始皇的本意看,是为了加强统治,强化法治,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破坏了法治,使法律原则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再者,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这就造成了民怨沸腾和人民的反抗,这是秦始皇所始料不及的。 在严酷过重的法律下,各种各样的“罪人”在秦代史料中无处不有、无时不见,仅见于史籍的罪犯不下100多万。按秦朝2000万人口计,不到20人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帝国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和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 三 经济上的贪欲是统治者的共同属性。但我们应看到,同属统治阶级,也有节制贪欲和使贪欲恶性膨胀之分。在这方面,大流士同秦始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大流士和秦始皇在统一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克制收敛自己的经济贪欲,使刚刚脱离战乱之苦的人民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大流士对此是有所觉察的。以前,波斯统治者对被征服地区没有规定固定贡税,而是让其以送礼的形式缴纳的,这对被征服地区人民来讲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大流士有鉴于此,便固定了对每个行省应征收的税额:如小亚细亚地区每年纳银1760塔兰特(一塔兰特约等于30公斤);巴比伦尼亚地区每年纳白银700塔兰特;印度西北地区每年纳沙金值银486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行省收入国库的白银12480塔兰特(约合440吨),波斯帝国的人口约为5000万,平均每年每户纳白银40克─50克,每人每年约5─10克[6](P101)。这同古代东方一些奴隶制国家相比,尤其是与亚述帝国向被征服地区无限榨取和直接抢劫比较起来,大流士向各行省征收的固定税额应该说是不轻不重,比较适度了。①除固定贡税外,波斯人民还要负担兵役以及修筑驿道之类的徭役。但总起来说,在经济方面,“波斯所属各地都没有受到怎样的压迫”[2](P234),人民的负担基本上没有超出可以忍受的限度。正因如此,一些被征服地区如巴比伦、腓尼基及巴勒斯坦的居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不但波斯的统治者远较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温和,而且在波斯统治下,税捐徭役负担也较轻”。[12](P433) 秦始皇则对统一后的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他到处吹嘘:“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功盖五帝,泽及牛马;黎庶无徭,天下咸服;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1](《秦始皇本纪》),如此等等。在秦始皇看来,他已泽及牛马,何况人乎?人民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所以他就有权向人民索取一切。因此,横征暴敛就成了秦帝国剥削人民的一个突出特征。 对于秦之赋敛无度,古人曾以“田赋二十倍于古”、“力役三十倍于古”、“泰半之赋”[14](《食货志》)、“头会箕敛”[15](《汜论训》)等概言之。另据当代学者估算,秦代一户五口之家的年收入约6000钱,缴纳各项费用向政府的支出(田租、口赋、户赋、更赋4项开支)达3960钱,约占全年收入的2/3,大大超过了古人所言“泰半之赋”[16](P272)。此外,秦始皇还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兵役,大兴土木,修建了宏大的阿房宫、骊山墓、万里长城。据说,仅修建骊山墓就动用刑徒及奴隶70万人,加上在北方戌边的士卒30万、戌守五岭的40万及其他劳役,全国服役的总人数,估计不下2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10,而且都是青壮劳力,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秦始皇对人民实行重租苛赋,推行繁重的徭役,并且实行种种横征暴敛,广大人民被从生产岗位上拉出来,背井离乡,来到千里之外的边陲和服役处所,这样必然使生产荒废,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秦始皇的这些措施使自己彻底地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人民不可侮,到了一定时期,在一定条件下,长期埋藏在人民心头的怒火就会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 四 在文化方面,大流士以居鲁士为榜样实行宽容政策,尊重被征服者的宗教习俗。他拨款在下埃及的哈尔加绿洲和上埃及的埃德福新建了两座神庙,并下令继续修复其他地方的庙宇。前519年,他按照居鲁士的办法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神庙并继续给予希腊人的圣殿以特权。波斯民族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虽被尊为国教,但只流行于波斯社会的上层分子和部分居民之中。在巴比伦地区仍然流行古代巴比伦宗教,腓尼基和叙利亚的传统宗教,这时也未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公元前494年左右,大流士曾因叙利亚总督向马格尼西亚阿波罗神庙园丁征税、命令他们耕作非神庙的土地,不理会国王关于保护该神庙的指示而训谕当地总督加达塔:“如果你不幡然悔改,你就将感到我内心的愤怒”[10](P124)。这说明,大流士虽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但并不禁止被征服地区居民信奉自己原来的宗教,还有意识地笼络各地宗教界上层分子,利用这些宗教来巩固帝国的统治。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例如在希波战争的紧要关头,希腊最著名的特尔斐神庙竟公然站在波斯人一边,警告希腊人必须放弃希腊,逃到大地的尽头去[11](VII,140-141)。 大流士的文化宽容政策也表现在文字方面。根据现有资料,大流士为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曾将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米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同时,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本地日常事务,各行省办公厅也可以使用当地语言起草官方文件。[17](P417)在埃及、巴比伦、犹太等行省甚至帝国中央的波斯,就发现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和希腊文字被同时使用着[6](P103)。贝希斯敦悬岩上所镌刻的纪功铭文里用了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对照书写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语文并未成为全帝国的通用语文,在政府中并不具特殊地位。诚如美国史家海斯所言:“波斯的帝国是宽大的,他们并不强迫所有的臣民使用波斯语言”[18](P135)。另有美国学者也指出,大流士“一般都允许这些民族保持自己的习俗、宗教和法律”[8](P99)。由于大流士的文化宽容政策,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一般都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而丝毫不受强制。 与大流士相左,秦始皇坚决排斥不利于一统天下和专制统治的异端。他认为,学派、私学的存在是思想混乱、社会不宁的内在根源,“如此弗禁”,势必造成“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为谤”[1](《秦始皇本纪》)等不安定因素。为了保持思想统一,秦始皇推行“禁废私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1](《李斯列传》)的思想控制措施,“言行而不轨于法者必禁”[19](《扬权》)。秦始皇把人们的思想言论统统禁锢在严酷的法令之内,人们完全丧失了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他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最后发展到了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的程度,从而把大批士人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秦始皇思想独尊、文化专制、大搞愚民政策的必然结果。它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事实上,这种残暴的思想文化专制不仅没有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综上所述,大流士与秦始皇在治国方略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差异:大流士的各种政策较为适度,能充分照顾到被征服地区的各种利益;而秦始皇则肆意忘为,无视被统治者的各种愿望和要求,使许多政策措施都走向了它的反面。换言之,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控制较为宽疏、经济剥削较为适度、文化政策较为宽容;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则政治控制走向极端专制独裁、经济贪欲恶性膨胀、思想文化统得过死,从而把下层劳动群众、六国旧贵族及士人知识分子全部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秦朝末年,代表农民阶级的陈胜、吴广,代表下层官吏和城市贫民的刘邦,代表六国旧贵族的项羽,代表知识分子的孔甲,这四种社会势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这些都是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波斯帝国与秦帝国的存亡尚受其他偶然因素的制约。如大流士在位时间较长,达36年(前522─前486年)之久,得以充分施展其行政才能,后继者也较有作为,较少昏庸之辈,完好地延续了大流士的治国大政方略;而秦始皇却壮年早逝,继承人昏庸无能,等等,这些也都是导致两大帝国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 注释: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 [3]拉尔夫、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八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6. [6]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7]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8]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五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9]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9. [10]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2]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睡虎地秦墓竹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刘安.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郭志坤.秦始皇大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17]刘文鹏.古代西亚北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8]海斯.世界史[M].北京:三联书店,1975. [19]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2. Compare The Governing Strategies Of Emperor Drius And Qin Shihuang ----And Disguss the Reasons for the Empire Persian Long Rule and Qin' Quickly Destruction CHEN De-zhe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Beijing Teachers' 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Summary: Founding the united autocratic empire, emperor Darius and Qin Shihuang took similar reformation measur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ir domination. But what was differeis the process of their governing policy: Emperor Darius controlled the conquered area comparatively loosely, exploited the people moderately and was lenient in his cultural policy; On the contrary, after emperor Qin Shihuang united China, his political domination trended extremely tyrannically, his economic greedy lust expanded and his culture rule strengthened. From the above ,we can see easily that it was their different fates -Persian long rule but Qin's quick destrution . Key words: Darius Qin Shihuang Governing Strategy Compare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