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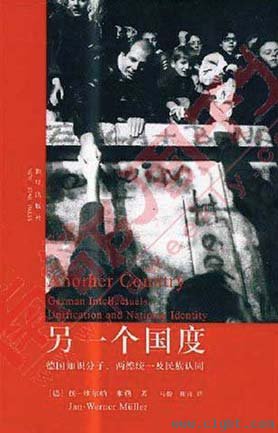 《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  《德国的浩劫》 撰文:李公明 在近代历史上,德国人的国家与民族认同一直充满了激烈的争议,甚至伴随着血与火的教训。十九世纪俾斯麦以战争统一德国,试图使“大德意志”的国家疆域和日耳曼民族的整体认同确立起来,但是这个任务在当时并没有完成。随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潮逐浪而高,连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也被席卷而去。终于酿造出两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的惊天罪孽,一个以深邃的思想贡献于人类的族群竟然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劫难,这是近代思想史上最骇人的长时段事件。 为什么当德国在历经冷战时期的国土分裂、主权受控、民族分崩、亲友睽离之后终于迎来统一的时候,竟然会有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发出反对统一的呼声? 扬-维尔纳·米勒的《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一书起码可以使我们对于那些事情的复杂性和所关涉的政治史与思想史的深度有较深的感受。 从历史分析中揭示知识分子面对民族主义时的迷局 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形的复杂性来源于历史传统与现实的纠缠,也来源于代际冲突与地域冲突的各自丘壑和相互叠压。面对这种扑溯迷离的情势,米勒的论述主题是分析西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的反应,分析有关民族认同的论争。为什么只谈西德而不谈东德,作者认为谈后者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视界和框架,因而对自己的论述对象作了谨慎的限定。 在此框架与意图中,米勒首先以历史分析的眼光梳理出德国知识分子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关于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的思想论争的发展大势。这种历史化分析的方法被他认为是日耳曼学中流行的政治论证研究法,可惜在众声喧哗的论争中却被人遗忘;他紧接着指出:知识分子迷局的真正关键就在他们的历史变化之中。他认为应该追问“知识分子在某些时刻发表了哪些言论,他们是否改变了观点——如果改变了,又是为什么。”总之,“一切评价必须以多面化的历史分析为基础。本来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却居然会被论战各方忽视,以致米勒对这种忽视感到奇怪。 在米勒的历史分析图景和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种思想资源就是对统一的反思和对再造民族国家的警惕,尤其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的超越。在这种历史视野之下,可以说自1945年以后的论争并非仅是此前争论的历史重演,而是生长出怀着对历史重演的警惕甚至是过分敏感而进行的自新和超前想像——对超越民族国家的正义境界的想像。 反思罪责是迈向政治成熟和自由的第一步 关于德国的罪责问题是民族认同论争发生的基本思想平台,反对重建民族统一国家的认知首先就来源于对德国罪责的承认和反省。著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创办刊物、举办论坛、发表演说,成为战后德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代言人。他在《罪责问题》一文中彻底地把罪责问题放在一个任何德国人也无法逃避面对的位置上,他列举了德国人必须面对的四种罪行:刑事罪、政治罪、道德罪和形而上学罪,以此否定那种大而化之的“集体罪责”论——米勒在书中称为“乌合之众化”,其目的是把罪责变得非具体化。实际上,雅斯贝尔斯的反思称得上是义无反顾,以致他无法见容于他的同胞而不得不移居国外。以实际影响而论,他列举的前两桩罪责相应地以审判惩罚和赔偿义务为追究的思想对于司法实践有所推动,而后两桩罪责则深深地触动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影响了一大批左派自由知识分子。他认为,对于历史上的罪责是无法通过赔偿、口头上的认罪或者向作为战胜者的美英法等国表示顺从就可以赎买的;关键是要进行彻底的、真诚的道德自新,要从内心进行忏悔和重建道德精神,从而实现“内在转机”——他和朋友一起创办的杂志就叫“转变”,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命题的重视。这有点像我们过去所讲的“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意味,但是他的利刃不是指向人性中的合理欲望,而是指向外在的赎罪形式。 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米勒明确地表示了赞赏。他认为“1945年后,雅斯贝尔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正确地断言,承认罪责是迈向政治自由和成熟的第一步,而且针对过去的公共交流将最终对德国的政治判断能力做出贡献。”这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无法逃避的责任。以历史的客观性与主体行为者的诚实性的道德态度检视历史,“承认罪责”这道门槛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民族心灵获得真正自由的试金石。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雅斯贝尔斯敏锐地发现在1945年以后,德国人民并没有对宪政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反对极权主义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的思想还没有成为德国人民内心的普遍认同,而这样的思想状况是无法确保德国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雅斯贝尔斯强调的是一种普世价值理性,其核心是“民主人文主义”,只有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德国人民才能真正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成为“作为世界公民的真正德国人”。米勒在书中也指出,虽然1945年以后在西德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像哈贝马斯、瓦尔泽、达伦多夫等这些知识分子一直觉得德国仍受所谓“后法西斯的民主缺失”之累,因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防止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死灰复燃。这既是米勒此书中心论旨的一个叙述,也可以看做是对当年雅斯贝尔斯的忧虑的证明。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时他意识到这种欠缺的含义并非仅仅是思想上的,而且更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在“解放”到来的时候没有进行宪政的、民主的深入教育和广泛讨论,是一种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而吊诡的是,人类历史甚至还更残酷地展示过一种反向的“教育”与“改造”进程,在那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可想而知了。 米勒在分析纳粹德国的历史根源的时候,提到了见证过俾斯麦统一、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F·梅尼克(在本书中译作“迈纳克”),指出他对德意志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坚持迎合了复员老兵和年青一代的文化需求。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是,在反省德国罪责的问题上梅尼克坚持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魏玛共和国与法西斯专制区分开来,他认为给德国自身和人类带来的浩劫并非源自德国民族文化的内部。十几年前读他那本晚年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仅仅是深感于他对德国古典文化的永恒价值的敬意和守望,却忽略了他的另一条思路:罪行的起源是具有普遍性的,其他民族只要有了一定的环境因素和经验刺激,群体性的恶就会发生。 爱国主义必须以民主和宪政制度为中心 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讨论是米勒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走出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迷局的核心命题之一。米勒首先介绍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来源和哈贝马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公民必须批判地反思,然后超越它们的特定传统和群体认同,转向普世价值,而不是屈从于传统的社会预期。”米勒指出哈贝马斯比他的前辈更进一步的是在他的“宪法爱国主义”中,凌驾在社会之上的国家主义“消解在体现着普世规范、保障法治的法治国家之中,消解在旨在促成有效政治参与的福利国家之中”。这就是他所谓的“后传统认同”——实质上这是以民主和宪政制度认同为中心的爱国主义,而与此相对的传统认同无非是对领土、历史、文化、同种同宗等价值的认同。与哈贝马斯的公民交往理论相联系,国家认同的关键是国家的自我否定的反思能力,而且把自由的、由政府提供保障的政治抗议权看做是取得人民认同的必要条件。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米勒的主题:对于一直在思想上超越民族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德国的统一、民族国家的重新认同是一件必须高度警惕乃至反对的事情。尽管统一后至今快18年的历史说明这种忧虑失之于过分的敏感和超前,但是作为一种体现出知识分子天职的价值关怀却仍不失去其内在的合理性。 米勒此书出版于2000年,近年来在德国知识分子论争以外,当下德国政治中左翼思潮的复兴更具有马克思那句名言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那么,什么是目前德国左派政党的理想和实践呢?曾任德国财政部长和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奥斯卡·拉方丹在2007年6月16日德国左派党成立大会上指出,左派党要继承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他特别提到“伟大的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她的遗训是:‘自由,始终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从实践上看,目前德国左派党的中心诉求是重建社会福利国家,它认为过去几年的国家政策的最大失误就是社会福利政策的逐步削减;而“社会福利国家”是最值得人民珍重的。至于自民党表示要用自由战胜社会主义,拉方丹立刻回应:“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自由”——“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模式,我们才聚集在一起!”据评论,德国左派党对于自己的前景非常清晰,并不刻意寻求执政可能,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反对派。或许这也是应对民族主义迷局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图景。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