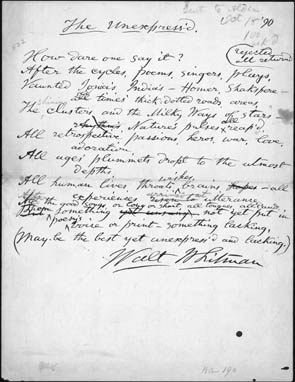 吻,自有约定俗成的文化含义。丹麦哲学家、诗人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一个完美的吻应当具备三个因素:首先,需要男人和女人一起来完成,男人之间的吻是乏味的。其次,男人吻女人要比女人吻男人更符合理想。再次,男女双方年龄过于悬殊,接吻也失去了意义。但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惠特曼写下的吻打破了惯例,表现出巨大的原创性:吻,摆脱了性别、秩序、年龄的束缚;吻,不再是个人的专享,而是上升到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的高度。惠特曼写下的吻与时代迫切召唤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大胆的思想”相吻合,以文学的勇气和力量为“伟大的事业”摇旗呐喊,鼓舞人心,增强意志。以大写的“吻”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和平的主题,惠特曼应是史上第一人。 惠特曼写下的吻,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线索与信任的维系,亲吻的对象,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农奴;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儿子;可以是亲密的人,也可以是陌生的人。惠特曼笔下的人十分多元且自由,在无限的时间和无垠的空间穿梭,个人行为的扩展为线性,线性与线性的交点为吻。人,成为有形的具象;吻,成为无形的意象;人与吻犹如一张巨形网络,共同构建了惠特曼诗歌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惠特曼写下的吻,自灵魂深处对苦难者施以眷顾。“我并不问你是谁,那对我无关重要。除了我将加在你身上的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是。我低身向棉田里的农奴或打扫厕所的粪夫,我在他的右颊上给他以家人一样的亲吻,以我的灵魂为誓我将永不弃绝他。”(《自我之歌》)“我”作为施事者,并不关心对象的身份,“你”人称代词弱化了“谁”的概念所指,而“我”加在“你”身上的内容,决定了情节、情境的走向。接下来,惠特曼进行详细交代,“你”具体化为“农奴”或“粪夫”,人称代词转变成了“他”,“我”“你”“他”实现了沟通、对接,人称的交互现象淡化、消解了底层劳动者的卑微地位,“家人一样”乃为平等观念的倡导、呼吁;“我”做的内容是“亲吻”,“低身”姿态突显“吻”的真实、真挚,这是诗歌段落的焦点,语言描述的中心。在惠特曼高度发达的作为个人语境的意识中,“灵魂”保证了“亲吻”动作的神圣庄严、不可亵渎。这使得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根深蒂固的“主人——奴隶”阶级关系,因为惠特曼写下的吻而瞬间坍塌,并与那场伟大的废奴运动遥相呼应,彼此共振。 惠特曼刻画的“我”寓意“自我”时,“自我之歌”指的是沃尔特·惠特曼,一位美国诗人,一位开拓进取的男人。但是这远远不够,惊悟、憎恶美国不公平、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惠特曼打造另一位“我”,上帝的化身,“伸出了温柔的手,我是那更加全能的上帝,先知们和诗人们在他们最热烈的预言和诗篇中已经提早报道过”,这时的“我”吸纳人类“一切忧伤、劳役、痛苦”,“为了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为了灵魂,我舍弃了整个世界,我走进人们的家,不论贫富,留下了深情的吻,因为我就是深情,我是那给人们带来鼓舞的上帝,带来希望和无所不包的慈悲。”(《歌唱神圣的四方》)此时,惠特曼写下的吻,对象不再是具体性的“农奴”或“粪夫”,而是整体性的“兄弟姊妹们”“人们的家”“神圣的四方”。从此可见,惠特曼从日常的朴素不浮夸过渡到认知的传承固实,从直接的情感表达上升到间接的信仰皈依,表明一种更为内在、深入的冲力已然诞生,给予人的尊严能够获致更加顺利的接受。 吻,传统地说,一旦发生在两个男人当中,往往会变味:吻,不再迷人、迷恋,而是迷失、迷惑,也就是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你用兄弟般的吻去欺骗他”。神奇的是,惠特曼写下的吻,经常发生在两个男人之中,这构成了作家创作诗歌的常态。“瞧这张黝黑的脸,这双灰色的眼睛,这把胡须,我脖子上没有剪过的白胡须,我这棕色的双手和毫无动人之处的沉默态度;可是来了个曼哈顿人,他总是在分手时吻我,轻轻地热爱地吻着我的嘴唇,而我也在十字街头或者在船甲板上回报他一吻,我们遵守陆上海上美国伙伴的礼节,我们两个是那种率真、不管不顾的人。”(《瞧这张黝黑的脸》)“我”作为一个闯入者,从种族的斑斓身体展开冒险之旅,黑、灰、白、棕,混杂交错,再加上默语的样子并不讨喜,整幅肖像构成了诗歌的前半部分,充满荒诞不经的喜剧色彩。分号之后,画风突变,惠特曼使用“可是”转折连词,对一个本土的“曼哈顿人”进行聚焦,他大方、开放地掀起爱之“吻”,稀释了“我”奇诡怪异的形象特征;副词“老是”强调“吻”的持久和流畅,体现出强烈的召唤感,导致“我”也在“十字街头”“船甲板上”报之以“吻”;惠特曼最终将礼节性的“吻”呼应于“陆地上”“海洋上”萍水相逢的美国伙伴,两个男人在“吻”中实现了共鸣与同步,从而为彼此携手在美国大陆开疆辟土、和谐共处奠定了感情基础。 作为一位冲破世俗习见的歌者,惠特曼视两个男人之间的“吻”胜于一切,朴实而珍贵。“你想我手里拿着笔要记录什么?是今天我看见的那只扬帆远航的漂亮而威严的战舰?是昨天的光彩?或者是笼罩我的那个夜晚的壮观?或者是在我周围蔓延的大城市的骄矜壮丽和发展?——不;那仅仅是我今天在码头上眼见的那两个朴实的人,在人群中作为良朋好友分手时的表现,那个要留下的搂着另一个的脖子热烈地亲吻,而那个要离开的把送行者紧紧地拥进怀里。”(《你想我手里拿着笔要记录什么?》)这一次,惠特曼故意避免“我”介入情感,而将渲染的氛围留给两个平等、平行的男人,为写下的吻增添更多的体验性和复杂性。“我”在诗歌中的作用是“记录”,表意上是现实的客观书写,“我”采取设问方式把“战舰”“光彩”“壮观”“骄矜”“发展”等宏大叙事主题拒斥,“——不;”破折号带来语调的突兀急促,“不”调动语气的铿锵坚定,分号显示前后内容的平分秋色,层层相叠为埋下的铺垫和伏笔打造泰山重势。 也许是为了“记录”之故,惠特曼把后半部分处理得十分简洁、纯粹,副词“仅仅”有画龙点睛之意,动词“眼见”有客观写实之意,名词“表现”有还原场景之意,而焦点无疑集中在“亲吻”。这一次的“吻”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是全力以赴,留下的男人主动“搂”离去的男人的脖子,为了方便“亲吻”;离去的男人占有另一半主动权,把留下的男人紧紧拥进怀里,也是为了方便“亲吻”。值得一提的是,惠特曼为了消除误会,使用了“良朋好友”一词,从而表露两个男人平等、纯洁、深厚的情谊理念。 其实,“记录”这充满敬意的“吻”源自惠特曼的切身体验。在“打响无情的战争”南北之战中,惠特曼担任护士工作,“带上绷带、水和药棉”,为战士包扎伤口;“甜蜜的死哟”“美好的死哟”,惠特曼见证战士的流血牺牲,深感生命的甜美宝贵。惠特曼认为:“对于很多伤病员,尤其是年轻人来说,需要某种人性的爱、关心,以及同情和友谊的磁性的暖流,这一些所起的作用反而比世界上一切药物都大。……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心理作用,但我认为这是铁的事实。”有鉴于此,惠特曼把“吻”作为人性关爱和友谊暖流的载体,写入辉煌的诗歌篇章:“我回来了,重操旧业,我奔忙于医院之中,我用温情的手儿抚慰着伤员和伤疼,我坐在不眠的人们身旁度过整个黑夜,有的那般年青;有的那般苦痛,我回忆着甜蜜的历程和悲痛的历程,(有多少士兵用挚爱的双臂搂抱过这个头颈,久久不放,有多少士兵吻过这长满胡须的嘴唇,吻痕长青。)”(《敷伤者》)“我回来了”,既是重归战场的豪言,也是立志“记录”的壮举,“奔忙”表明救死扶伤行为的坚定、恒久,“抚慰”表明护卫伤员的悯爱、痛惜之情,一幅壮烈的战争图景跃然纸上。有意味的是,“有的那般年青”和“有的那般苦痛”作为参差对比,出现了表达上的错位:“年青”与客观年纪有关,“苦痛”与主观心情有关,然而正是“记录”范畴的越界和延伸,使得战争的视野和影响扩大开来。“有多少士兵”,男人的数量成几何级增长;手臂搂抱脖子,嘴唇烙印吻痕,皆为“吻”的经典动作、意象;“久久”“长青”寓意生命永垂不朽。惠特曼写下的吻,获得了巨大的提升、飞跃,由私向公转变,由个人情感的爱转向社会力量的爱。1930年,美国当代诗人哈特·克莱恩通过《桥》中的一节,致以惠特曼最崇高、最诚挚、最肯綮的问候:“啊,从死者中站立,你带来记录和一份新约定,就是那鲜活的兄弟之情。”惠特曼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记录了男人之“吻”的完美和深刻,以生命的体验和探询成就诗歌的主要标志与经典地位。 战争爆发之后,成千上万的男人组成一支武装队伍,为值得信赖的统一国家和民族而战。“战争!一支武装的队伍在前进!迎接战斗,没有回转的余地;战争!不管多少周,多少月,多少年,一支武装的队伍在迎上去。”年轻的儿子“开始血红的生涯”,被赋予使命和胜利,也被赋予死亡和失败。母亲,作为女人登场了,她要完成最后的仪式,惠特曼写下的吻:“教堂尖顶上,所有公共大楼和店铺上扬起了旗,挥泪告别,(母亲吻她的儿子,儿子吻他的母亲,母亲舍不得他走,然而不说一句挽留的话。)”(《诗歌啊,首先是一首前奏曲》)旗帜猎猎地飘扬,组成浩大的场面,战争的力量该是多么具有鼓动性!但是满场喧哗中,出现最感人、最温馨、最寂静的一幕,却是战争的吻别,女人与男人、母亲与儿子,跨越辈分、年龄的限制;“母亲吻她的儿子,儿子吻他的母亲”,顶真、回环修辞手法的运用,将母子、男女之吻,置于柔软、明亮的抒情写意范畴,在士兵即将走向战场之际,“吻”这个甜蜜的名词也随之进入了战场,将战争的残酷性间接衬托出来。惠特曼使用了冷静的话外音,母亲不愿儿子上战场与支持儿子上战场的矛盾冲突心理,原本一分为二,本末竞逐,但是惠特曼写下的吻,最终将两者转化、融合为一,末没有被排除,只是被消融于分裂为二的心理情感之内,“吻”也因此蕴含着更为丰富和饱满的质素。 战争虽然残酷,但是为美国的和平与统一带来保障,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吻”的格调和路径也陡然急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今天请把你绯红的双颊,你的双唇送过来,接受一个国家的甜吻。”(《给新娘一个吻》)惠特曼写下的吻,出现在新世界的“新婚祝词”里,摆脱了传统婚礼的文化含义。新娘是唯一的主人公,新郎、司仪、父母皆缺席了,这些原本该有的礼仪被“祝福来自东方和西方”“敬礼来自北方和南方”取而代之,“合众国”作为实存的国家,成为献上新婚之“吻”的核心要素。 惠特曼写下的吻,等同于死亡,这强有力的生命节奏,以积极、昂扬的心态直面死亡。正是由于大胆、精细塑造“死亡之吻”,惠特曼不但将自己区别于他人,而且使得诗歌的力量和强度达到无与伦比的境界。“我结束了这次奇怪的守卫,在黑夜朦胧的战场上的守卫,守卫那个曾经报人以亲吻的孩子(今后再也不会那样了,)守卫一个被突然杀死的同志,这永远难忘的守卫呀,直到天亮时,我才从凄冷的地上站起,将我的士兵裹好在他的毯子里,把他埋葬在他倒下的那片土地。”(《一天夜里我奇怪地守卫在战场上》)这里,士兵死后僵冷的躯体与生前热烈的接吻两个鲜明的片断并置,死亡与生存的亲密感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力,“我”守卫一夜躯体的行为,使得“埋葬”被赋予强烈的生命认知和尊严。 “我熟悉的那段时间的精灵,今天激动得脸色通红,第二天又苍白得犹如死神,在你离开前请和我接一个吻,狠狠吻我一下,给我留下你盛怒的脉搏——把它们遗传给我吧——把我灌满激动的电流,你走后让它们在我的诗歌里烧焦,起疱,让它们在这些诗歌里使未来的人们认识你是谁。”(《已完成任务的精灵》)战争结束后,惠特曼为千千万万化身精灵的士兵立传,将他们归列“不朽的队伍又回来了,从战场上回来了”,安排他们在和平的首都华盛顿城,“往回家的路上走”,一切皆以军队的标准行进。时间,也是只有一晚,“脸色通红”与“苍白如死神”,也是暖色与冷色、生命与死亡的碰撞、对接,造成强烈的审美认知。最后,“你”和“我”狠狠的“一吻”,生命的脉搏犹如电流一般得以遗传,死者与生者交互确认,实现了无差别性或同一性的最高存在。凭借“吻”与文字的载体,“你”被未来的人们认识,生命的荣誉和价值得以流芳百世。 惠特曼在晚年写下带有遗嘱性质的诗歌《再见!》,“我已经濒于死亡”“我宣布我的后事”,同时《再见!》也带有总结性质,回顾了自由、平等、同性之爱、灵魂与肉体、战争与和平等主题,此外也直面活着与死亡的主题,这是惠特曼所有诗歌中最冷静和克制的一首。“亲爱的朋友,不管你是谁,请接受这一吻,这是特地献给你的一吻,请不要忘记我,我仿佛干完一天的活,该向前走了,一个比我的梦想更为现实,更为直接的未知之境,这种黑多很多,在我周围降下了令人清醒的光箭,‘再见!’”(《再见!》)惠特曼以“死亡之吻”为自己的人生划上句号,“吻”属于单方面献出,没有特定对象,唯一的目的是“记得”,然而注定没有人回复,诗人走向超然卓立。“再见”“吻别”被惠特曼定义为“死了”。 总之,惠特曼写下的吻,超过了任何有写作记录的作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含义上。吻,在惠特曼诗歌中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词语,意义固定单一。恰恰相反,惠特曼写下的吻,满足了人类表达丰富情感的需要,“吻”体现出语言的复调结构,在不同的篇章中,在不同的语境下,“吻”潜藏着繁芜而充沛的意图和意义,并且与传统文化含义出现了偏差、分歧,极具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诉求。锦上添花的是,惠特曼写下的吻,剔除了性欲和色情刺激感官的成分,从而转化成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审美尊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