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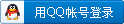  x 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之所以说他“先进”,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所谓近代化,是相对于古代封建主义说的,在郑观应所处的时代,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的改革,这个“民主制”,在那时就是大多数改革家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议会制。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 一、为研究洋务运动而研究郑观应 号称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的历史,是中国早期对外开放进行改革的革新运动史。它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初,上海是其中心地区。郑观应正身处其中,并逐渐参与洋务实业、文教等方面的活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虽不以某些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却是千千万万人的意志及他们的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历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社会事件的同时,必须研究其代表性的人物。 我在从事洋务运动教学研究不久,即选择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李鸿章始终以大官僚的身份办洋务,盛宣怀则是通过办洋务爬上大官僚的高位,此二人虽在改革开放、发展实业等方面起了颇大作用,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各有其致命的局限性;郑观应是单纯的实业家,与中外民间人士交往甚广,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最为广泛深入,所提改革社会的方案也最为全面并触及要害。所以在我所写《李鸿章传》15万字手稿于“文革”中被抄走遗失之后,乃于粉碎“四人帮”后全力以赴地写成出版了《郑观应传》和发表一批论文。 之所以先写《郑观应传》,除因占有资料较为丰富全面之外,还由于我早就知道毛泽东在青年时读了《盛世危言》受到启迪而激起他“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从而竟逐渐成了一代伟人的缘故。 二、郑观应的思想体系 郑观应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涉及各个方面,并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于15年前将其核心概括为“富强救国”四个字。为什么要突出“救国”?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因此,任何一个思想家政治家,都把救亡御侮置于首位,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的道理;怎样就能达到救亡御侮的目的,除少数顽固守旧分子之外,日益增多的先进人士都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其间首先是西方的技艺,这就是林则徐、魏源等所首创的“师夷长技”举办近代工业以求强;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在政治上作与新型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改革,这就是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写下的,对美国实行“三占从二”民主制度“遽成富强之国”的憧憬所萌发的精神。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三者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近代“登于富强之域”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切有志之士为之而探索和奋斗着。郑观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述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这三者”,我曾称之为“爱国的三个层次”,即:大敌当前,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阶层,不管是从爱清王朝出发,还是从爱家乡、爱中华民族之国出发,都是要求抵御外侮的。林则徐将之概述为“民心可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这只是爱国的初级层次。进一步各派在如何才能达到御侮胜敌的目的上有着分歧。保守不变者认为,刀矛弓箭加上固有的仁义道德必能取胜;先进人士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近代中国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和发展新型工业企业,这既可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以致强,又能在市场上与西人角胜以致富,强且富矣,就完全可能达到胜敌的目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高一级的爱国的层次。那些守旧不变之流的主张只有败亡一条路,故名为爱清实为害清,这是显然的。那么,主张引进和学习先进科技者是不是一定能真正达到御侮取胜目的呢?答复是不一定。因为,在近代中国只有建立与新型工商业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才能促使经济更快的持续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而成为工业强国。事实上,洋务官僚是不愿也未能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所以富强目的远未达到。这是洋务运动的悲剧。郑观应却从洋务活动实践中获得超越于洋务运动一个时代的水平的认识,他将御侮、求强、致富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作了系统而有机联系的正确表述。他说: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简短的几句话,把御外侮与振工商以致富强以及改良政治体制以适应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表达得多么清楚!这种符合中国社会前进要求的认识,完全是自觉的,因而不是偶然形成的。郑观应说他于19世纪60年代即开始“究心政治、实业之学”。经过几十年的探索,逐渐将“政治、实业”的关系有机的联系了起来,终于讲出了上面那一段精辟的话,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的高度概括。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谈论抵御外侮必须振兴工商者有之;谈论振工商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者有之,但把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三者统一并有机地联系起来如郑观应这样的论述,实属罕见。所以我说郑观应是“爱国三个层次”统一于一身的先进人物。唯其如此,所以我曾作过“郑观应是民主与科学启蒙思想家”的评价,因为他的上述认识和论述,实际上就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前声。 郑观应的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此书是由他的《救时揭要》、《易言》发展而来,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居于澳门时辑著,1894年初刊五卷本,后经1895年和1900年两次增订。这部书可说是郑观应社会改革的理论著作。另一部名《盛世危言后编》的书,大多收编关于郑氏实业经营、人才培养、风尚改造等来往书信和企业章程、社会救济等事,因此该书可说是郑氏一生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实业的实践的记录,于1909年在澳门家中“郑慎馀堂”(澳门人习惯地称之为“郑家大屋”)编就。这两部巨著虽编著成于澳门家中,但内容却大多与郑观应活动经营达60年之久的上海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说,郑观应的事业基地在上海,生活基础在澳门。但这些著述却反映了全国的事情和问题,并关系到未来的中国。它们涉及到政策吏治、经济财政、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新型人才培养,乃至女教女权、社会慈善福利、社会风气和结构改造、流民犯人如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等等均有阐述且颇多创新,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论述问题最广泛、水平最高者,特别是其中对发展经济方面的阐发论述,质高量多,高人一筹。他认为,市场上与洋商角胜,靠实力;谈判桌上与列强讨价还价争利权,靠实力;军事行动在战场上取胜,更靠实力,“实力”的表现方面很多,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故应将经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一定要加快速度地进行。经济怎样才能很快搞上去?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从改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郑观应都有合乎逻辑的阐述。集中到一点,就是怎样进行“商战”。“商战”,是郑观应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最突出的表现。 三、突出“商战”思想 “商战重于兵战”或“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是“商战”在郑观应心目中的地位的写照。为什么郑观应把商战置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强兵固然很重要,但强兵必须与政治教育尤其是发展经济联系起来考虑。只有富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兵才能真正地强。因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不仅军队有自造的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更能在市场上有廉价的商品与外国相竞争。他意识到:要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他说: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多么深刻的认识!所以郑氏把自强的基点恰当地放在发展工商业以进行“商战”之上。 “商战”怎样才能操胜算?郑观应有一整套“胜算”法。从根本上说,除税收等与洋商平等条件外,决定性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来,即他所说“尤必视工艺之巧拙”。工怎么能“巧”?在科学管理前提下,主要靠先进的机器技术。他在70年代即认识到,用机器生产,“则所出之物日多,而所售之价亦日贱,销路愈畅,贩运愈宏”。他对中国不讲求机器技术的落后状况颇为不满,说:由于不讲求先进机器技术,致使“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以致不敌洋产,漏厄愈甚。因此,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 单纯在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就能在商战中操必胜之算呢?郑观应凭着多年的经验,认为必须不断降低生产管理费用和流通过程中附加于商品的一切费用,才能使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保持低廉的价格,才能在商战中取胜。于是他又提出一系列降低商品价格以加强竞争能力的意见。 首先,完全按照“商贾之道”办企业。郑氏对于“官督”或官办衙门式办企业的做法极为不满,而批评说:“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从而出现滥行“荐人越俎代谋”等种种腐败现象,于是提议各种实业企业“一律准民间开设,……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所谓“商贾之道”,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剥削剩余价值和追逐尽可能高的利润为唯一目的。企业经营者,为了这点而尽可能从原料购买到生产、流通过程减少费用,而尽可能加速资本周转速度。这只有把办企业“视为身心性命之图”的商人才能较好办到。而“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这是经验之谈,可取! 其次,郑观应除主张发展轮船、铁路、电报,以降低流通费用之外,早就主张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以促使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铸造一定分量的主币、辅币除便于交换之外,还可以堵塞外币输入并从铸币中盈利。至于银行,其利甚广,其中“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既可代筹企业资金,又可在“银根短绌情况下”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这样,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而掣肘,等等,为解决商品流通和生产中资本短缺创造有利条件。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及其措施,包括的范围很广,上面的叙述仅仅是一些主要内容,但就从这些来看,已能说明郑观应的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反映他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以战胜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爱国思想和愿望了。 为了达到商战取胜的目的,郑观应始终如一地强调两条,一是人才,二是资本。他一直呼吁:“国之盛衰系乎人”,实业之成败系乎人,借材异域只是暂时措施,一定要立足于自己培养,没有与改革相适应自己培养的人才,不管多么美好的设想,都将成为泡影。所以他把《学校》篇置于《盛世危言》中的突出地位,提出废八股时文,学习技艺等实用之学,改旧式书院为学堂,并身体力行地办电报矿务学堂、招商公学,和在汉阳铁厂办半工半读技术大学,培养大批新型人才。关于资本,郑氏明确认识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展实业必须有充裕的资金。资金哪儿来?国内固然要想办法如设股份公司以集股金,设银行以将社会闲散财富集中起来,用于急需办的实业,但这些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外力,吸引外资,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 四、“策莫善于”“大开门户”办“万国商场” 郑观应在“人才不可缺乏”、“股本贵充足”的思想指导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以臻于富强的目的,除建议类似中外合资性质的“华洋合办”等之外,复大胆提出“大开门户”在边界地方创办类似特区性质的“万国公共商场”的设想,他认为这可以利用世界各国的资力在那里进行建设,例如海南岛就可以首先这样做。他与人书云: 闻东三省西藏各省强邻时欲侵占,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不若大开门户,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廉地方,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准其杂居,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吸收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或藉彼合力以保疆土,免为外侵夺。 又说: 何以云辟边界?我国现在贫弱,民生计拙。中土路矿,外人觊觎,各思侵占,不如将边界之地开作万国商场,任外人懋迁有无,我收其捐税,贫民亦可得其工资。凡西人所到之埠,无不大营宫室,广投资本,各国如均有产业自应公同保护矣。上面两段话有着下述几层意思:(1)“万国公共商场”的地区及于中国四周边境,东南沿海所开商埠是不用说了,东三省、西藏等陆地沿边及不与任何国家“毗连”的“琼廉地方”特别点明,这就是说所有边界地方均在辟为“万国商场”之列。(2)这个“万国商场”的作用和任务,就是要“吸收外人财力”任外国资本家“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或任外人经营“懋迁有无”的商业,这样,国家可以“收其捐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贫民可增加就业机会以“得其工资”,公私两利,中外两利。(3)开“万国商场”前提是为防止“侵占”和“蚕食鲸吞”,其结局则是“藉彼合力以保疆土”或“公同保护”,综此三者就能更快达到富强目的。因此,郑观应颇为自负地说:“就鄙见而论,策莫善于此”者。“除合力保疆土”未免陷于幻想外,确实,“策莫善于此”!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等条件下,舍此绝无可能在较短时间赶上先进发达的国家的。 郑观应是一个有着强烈“富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实业家,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因此,“大开门户”办“万国公共商场”绝无牺牲主权之嫌。郑氏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别强调“法权”操诸我的问题。他写道: 惟最要者,须重订新律,收回治外法权。拟暂照日本律例颁行,华洋一律,毋许歧视。如是,则外人均受治于我法权之下,应无他虞。”可见郑观应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要高速度发展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富强国家,舍“大开门户”辟“万国商场”别无他法,也即所谓“策莫善于此”,但外国人“受治于我法权之下”这一条做不到,那将有“他虞”。故强调外人在“法权”上应“受治于我”。 另外,郑观应担心这种“大开门户”辟“万国公共商场”的非常之举不为保守者们所理解而发生事端。他说“犹有所虑者,则恐蚩蚩者氓,不明其中利益,尚多拘守,或演出土客不和之恶感”。这种对“蚩蚩者氓”的“拘守”者流,不理解“大开门户”办“万国商场”的“利益”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确是如此,在近百年前的清末时代,提出“大开门户”办“万国商场”的设想已属大胆,要求人们认识这一设想的重要意义,更是难以想象。尽管郑观应想要通过“议伸演说”来“开导下愚”,也是难以奏效的。于此益见郑观应眼光远大了,于此愈益显示郑观应的胆识远出凡人之上了。 “曲高和寡”。在半殖民地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条件下,在“蚩蚩者氓”,“拘守”,者流遍地皆是情况下,郑观应的主张是不能付诸实施的。但这不是郑观应的主张不好,而是实施的条件不成熟。一旦条件成熟,其主张实行,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必将有一个大飞跃。 郑观应的思想及其著作是非常有魅力和生命力的,至今读之还颇有新鲜感。之所以能如此,据我看,主要是与他长期从事实业经营达60余年之久有关,与他经常来往于中国两个对外联系的大窗口上海、澳门有关,他当过洋行买办,担任过近代有数的几个大型企业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企业的帮办、总办等重要职务,在实践中体会和认识到办实业乃至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笔之于书。这是同时代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