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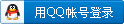  x 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 作者:夏东元 一 盛宣怀(1844—1916年)是大家所熟知的洋务活动的骨干分子,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他虽不象李鸿章那样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且控制运动的全面,却基本独揽了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督理权。而洋务工商业的经营,既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也是盛宣怀赖以发迹的基础。 盛宣怀的经历,在清王朝中是颇为特殊的。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之后,多次报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但后来却平步青云,继1884年一度代理天津道后两年,1887年正式任山东登莱青道,1892年调任天津道直至1896年。此后即到清朝廷中任职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约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进入内阁当上了邮传部尚书。不经科举正途而做到这样的高官,在清王朝中是仅见的。这是什么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盛宣怀在洋务企业经营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实力,为清王朝提供了财源;他与洋人打交道,特别是1900年“东南互保”的活动,造成了使清王朝“转危为安”的印象。这使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成为“不可少之人”,扶摇直上是必然的了。 盛宣怀是善于抓紧时机和要害的。1870年入李鸿章幕后,正遇上全国人民起义被镇压,外国资本主义加强军事、经济侵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洋务运动由以办军用工业为主转变为办民用工业为主,也即所谓以富求强“强与富相因”。盛宣怀选定了创办和经营近代工业企业以为晋身之阶。李鸿章曾说盛宣怀的野心是“办大事”、“作高官”。(李鸿章:《致潘鼎新函》,光绪三年五月十九日,《李鸿章致潘鼎新手札》第一○三页。)这是一针见血之论。盛宣怀知道,欲“作高官”,象他那样非正途出身的人,必须“办大事”作为奠基石。这个“大事”,在当时莫过于办近代工商业这个被视为“富强之基”的事业了。因为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自强运动,而自强的基点又是放在作为“致富”的近代工商业上。这个被清政府看作关系拯救统治的事还不是头等大事吗?盛宣怀适逢其会,他虽未参与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近代军事工业的活动,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 在那时,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发展的途程是很不平坦的。不仅技术人才、机器设备和资金等来之不易,而且旧的顽固势力的反对也是很大的阻力。面对这种情况,畏难而裹足不前者比比皆是。盛宣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聪明才智之士,莫不避难就易,避险就夷。皆各思安坐而致尊荣,不肯历患难而希勋业。”他称这为“富强大局之弊”。(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盛宣怀《致黄花农观察》,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丙申思惠斋亲 笔信稿》。)言下之意,他盛宣怀是为“富强大局”迎着“难”和“险”而一往直前,并以此“希勋业”而“致尊荣”的。历史的事实也确如他说的那样行进的。 洋务工业企业主要是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务等四类,这些企业虽不都是盛宣怀创始,但后来却基本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盛宣怀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据他自己说,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即遵奉李鸿章“面谕,拟上《轮船章程》”。他随即草拟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条纲领。(盛档:盛宣怀拟《上李鸿章轮船章程》底稿,同治十一年夏。)这是轮船招商局章程最早的雏型,成了后来章程定稿的基础。招商局开办之初盛宣怀担任管理漕运的会办,但几经曲折,到1885年当上了督办。1875年“海防议起”,清政府为了求富和军事上燃料、原料等需要,派唐廷枢到直隶办开平煤矿,派盛宣怀到湖北与汉黄德道李明墀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盛宣怀先后带领洋矿师马立师、郭师敦到湖北广济、兴国等处勘探煤铁矿藏。并于1878年1月购得大冶铁矿山。该局经费主要是户部拨款,虽终“以炼铁难筹巨款,半途中止”(盛宣怀《致张之洞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七日。见《中国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七五八页。),但却为1889年张之洞筹办汉阳铁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张之洞称盛宣怀为“勘矿首功”,(张之洞《致上海盛道台》,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张文襄公全集》电牍一五。)是符合事实的。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时虽未让盛宣怀参加进来,但1898年因经营不善经费难继而招商——盛宣怀承办,也到了盛的手中。上海机器织布局系彭汝琮于1878年创始,不久失败,于1880年由戴恒等人接办,盛宣怀并未插手,但1884年总办郑观应离局赴粤,由盛接理,有着实际的控制权,1893年焚于火后重办华盛厂时,即由盛宣怀督办了。至于电线,自1880年津沽设线始,就是盛宣怀经营的。接着是津沪、闽浙、长江乃至两广、云贵、四川、西北、东北等遍及全国的电线,从招集股金、购置器材、勘架线路、人才的招聘与培养等,都是盛宣怀一手经理的。甲午战争以后,盛宣怀督办铁路公司,掌管全国重要干线的筹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国通商行;控制全国不少省分的煤铁等五金矿藏的勘探和开采;办起了南北洋公学等学校。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盛档: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的贪馋者,是恰当地刻画了他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资产阶级的本性。盛宣怀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活动的。 据上所述,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经营,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盛宣怀督办或实际控制和参与经理的,因此盛宣怀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研究盛宣怀在洋务企业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从一个角度研究了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和发展规律。 二 “致富”和“分洋商之利”,是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的主要目的。凡是参加洋务活动的人,无论是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还是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不同动机,但在“致富”“抵洋”这点上却是一致的。李鸿章说,办轮船招商局“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办纺织厂,是要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抵敌洋产”,“力保商民自有之利权”,(李鸿章奏稿,《洋务运动》,第七册,第四五三页。)始为洋务派后来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薛福成说:办招商局不仅收回内江被洋商夺去的权利,且“渐可驶往西洋诸埠,隐分洋商之利”,(薛福成:《应诏陈言疏》,《庸庵全集》卷一。)至于郑观应在1873年即说过:“泰西轮船、机器、大炮之精,泄天地造化之奇,为军国所利用,以此致强,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势必雄跨四海”。(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他敏锐地看到长江上“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的情况,而坚决要求“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郑观应:《论商务》,《易言》上卷。)强烈追逐利润以冀办成“大事”的盛宣怀,当然与洋商的侵利是对立的,他在1872年初夏倡议办轮船航运之初即说:“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他告诫那些深怕敌不过洋人的人说:“今人于古人尚不甘相让,何夷狄之智足多哉”(盛档:盛宣怀拟《上李鸿章轮船章程》底稿,同治十一年夏。)。电线的架设也是为了利商御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人即企图在中国设立旱线,因人民反对而未成。盛宣怀是由中国自己设电报以保利权的积极主张者,他说:“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盛档:盛宣怀拟《电报局招商章程》底稿,光绪七年。);对于洋人的觊觎,只有自己办电报才能“遏其机,而杜其渐”(盛档:盛宣怀等《上李鸿章禀》底稿,光绪八年。)。其他如煤炭的开采,金属矿采掘与冶炼,也都有抵制或减少洋货进口的意图。总之,洋务派办近代民用工业企业,是抱着自己“赢一分之利”,即“少溢一分之利”,也即“分取洋人一分之利”的总目的的。 然而,办近代工商业以“致富”与“抵制洋商”的总目的虽同,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却不尽相同。其间官本官办还是商本商办,就有不同意见,而这是关系到企业成败和能否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问题。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在市场上胜过洋人;要胜过洋人,必须价廉物美;要做到价廉物美,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企业,而这,只有商本商办才有可能,官本官办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封建统治下的官办必然要按官的意志办企业。盛宣怀从“办大事”出发,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正确一边,坚持商本商办的。 轮船航运开始议建,盛宣怀即提出招集商股和“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纲领性意见。他说:“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在官这一方面,应该是“筹国计必先顾商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扶持他们使“不致弛废半途”。因为“倘商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对国家是很不利的。只有商有利了,也才对官有利,官商两利,就能做到“利不外散,兵可自强”。(盛档:盛宣怀拟《上李鸿章轮船章程》底稿,同治十一年夏。)但这个意见遇到了阻力,不少人主张官本官办,例如创办主要成员朱其昂就是领官款办轮船航运的主张者。盛宣怀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报告李鸿章说:朱其昂对于办轮船航运虽有不少是“切而不浮,轻而易举”的好见解,“惟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本,其稍有异同之处”。(盛档: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同治十一年夏。)并附呈“清折”表达了“集商本”以商办的见解。 继1880年津沽电报官线之后架设津沪电线时,盛宣怀本着“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原则拟订了详细计划:先由官垫经费银二十万两,用商股十万两归还官本之半,“嗣后成本官居其半而利息出入全数归商,以示体恤而广招徕”。商本十万两提长年官利一分,余利悉作公积金;官本十万两不提分文利息,如果十年之后官本不提回的话,才“与商本一律起息”,但“仍不取息外盈余以分商利”。盛宣怀之所以这样“顾商情”,是因为他认为:“电报原为洋务军务而设,但必先利商务,方可行远而持久”。(盛档:盛宣怀拟《电报局招商章程》底稿,光绪七年。)这也就是说,“顾商情”实际上是为洋务军务;如果商务不能持久不敝,为洋务军务的目的也要落空。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观察比较,到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时,盛宣怀的商股商办更为明确、坚定,并带有理论性。1889年张之洞从两广调督湖广,将他拟在广州创设的铁厂带到湖北,因要利用当年盛宣怀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基础,乃请这位“勘矿首功”参议。1890年盛宣怀拟订了一个招集商股办铁厂的章程。张之洞对此表示异议,他对李鸿章说,盛宣怀“所拟办法,与鄙见不甚同”,认为“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张之洞:《致京李中堂》,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张集》卷一三四,电牍一三。),而坚持官办。盛宣怀集商股商办的意见被否定了。但他坚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他把商股商办的主张直接通到庆亲王奕□那里,说明其好处:(1)集商股办铁厂,“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这就加强了竞争能力,使人们“不买他国之铁,以杜漏卮”;官办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故各国煤铁矿皆系商办而无官办者”。(2)因为“商办者必处处打算”,故工厂一定设于与原料、燃料产地相近之处,并且还会考虑到交通运输条件的方便,因这可以大大减轻成本,“如鄂中铁矿就大冶江边开煤设炉,必较洋货价可大省”。(盛档:盛宣怀《致庆邸禀》,光绪十六年十月。《东海亲笔信稿》。)他批评张之洞将铁厂不设于大冶江边而设于汉阳这种“舍近图远”的做法,即使铁厂也能建成,但“远运本重,必不能敌洋料”。这亦如官办的“船政之造船不敌洋厂,粤局之铸钱不敌洋钱也”。(盛档:盛宣怀《禀庆邸》,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东海亲笔信稿》。)盛宣怀的结论是铁厂“官办必致亏本”。于是提醒清朝廷,趁铁厂筹建未久赶速改变计划,他说:“如果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轻运费而敌洋产”,是可以办到的。不仅如此,而且“官可有益无损”:未发之官本可不再发,“已发之官本一百万两责成商人分年缴还。需用钢轨悉照外洋价值不准稍加”。(盛档:盛宣怀《禀庆邸》,光绪十六年十月。《东海日。《东海亲笔信稿》。)真是一举数得。改归商办如果张之洞那里很难说通的话,他对奕□说“可否求钧署(按指总理衙门——引者)托为西洋熟习矿务者之言以讽之,或尚及挽回”。(盛档:盛宣怀《禀庆邸》,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东海亲笔信稿》。)这里盛宣怀要借洋人的力量来改变张之洞的不合理的做法,是买办性的表现,但希望由官办改为商办以期达到战胜洋料的迫切心情,却是积极的可取的。 商办主张之所以积极可取,不仅在于铁厂和轮船、电报等企业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 第一,将社会上闲散的对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起着有利作用的资金收集起来,经营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而发挥作用。在洋务企业举办之前,一些买办、商人将其积累往往投于外资所办的企业,据郑观应说,七十年代初,洋商在长江航行的轮船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他们都“不乐居华商之名而甘附洋商之尾”,(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着有利的作用。洋务企业创办了,许多人都来投资,朱其昂、其诏兄弟和经元善这些商人、钱庄主,对轮船、电报都有不少资本投入,1881年上海电报局成立时,经元善一人的资本就占八分之一;翰林院编修戴恒和龚寿图这些仕绅官吏,将其封建家族的积累也投于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即各投资五万两,以后还有增加。拿买办说,徐润说他对招商局的投资先后两次“徐姓共认股四十八万两”,(《徐愚斋自叙年谱》第三七页。)“因友及友”所招股本也不少。唐廷枢说自己“期功之亲友共有八万余两,戚党又二十余万两”,唐、徐“两姓经手已居大半”。(盛档:《唐廷枢、徐润致郑玉轩、盛宣怀函》,光绪七年二月初九日。)郑观应在太古任买办时即对轮船、布局、电报有投资,1882年专任招商局帮办后,则更多的把为太古服务的揽载行等资本转移到民族工商业中来。买办、商人、仕绅、官吏等人投资于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就意味着他们逐步摆脱同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卷进中国民族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就意味着促进了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集商本以商办的洋务企业成效是比较显著的。招商局成立前,长江轮船生意本为洋商所占,其中旗昌居于统治地位。招商局成立后,因有政府的漕粮、资金等支持,加入竞争后,使旗昌难于招架,“议必归并,方可息争”。当时旗昌所开之金利源股本达二百万两,商局只有数十万两,力量悬殊,旗昌料商局“无力并之”,又“故悬其价以相胁”。岂料“商局毅然为之”。归并之后,商局增加轮船十八号,行栈码头六处,“局势一振”。迫使太古、怡和于1878年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1878至1881年三、四年间,招商局“得收水脚一千三百余万两,除支用修船、官利及提存保险外,净得赢利二百余万两”。到1882年,商局“欠款渐轻;而轮船三十号皆已汰旧更新;码头十余处,亦复扩充。”盛宣怀面对这种情况而满怀信心说:“嗣后必获得赢利”更多,“不费国家一钱,而江海之间轮船三十号以张国威;华人载货之资每年收百万不入洋人之手,以杜漏卮。论国计,则收回已失之利权,而官帑仍无毫末之损;论商情,则成就公司之创局,而民股实操子母之权”。(盛档:盛宣怀拟《轮船招商局始末》底稿,光绪八年。)盛宣怀对于商局成绩虽不免有夸张之处,但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增加、营业不断扩大和分洋商之利等情况基本属实。 电报局也有同样的情况。 “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见盛档:盛宣怀《电线设立情形》,光绪二十八年。)这在设电线之初就明确了的意图。盛宣怀就是在这个“意图”指导下创办电报的。兹列举线路的具体设施来说明。自津沪电线改归官督商办后,1882年接办了苏浙闽粤等省陆线,次年办长江线。1885年因“海防吃紧”,设济南至烟台线,随又添至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方;1886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吉林至珲春陆线;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南接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乃由九江起设至赣州以达庾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起设线至襄樊,次年又添设襄阳至老河口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电线得有两线传递,庶无阻滞之虞”。以上都是为军事、商务上的需要而设立的。其他次第设立的如武昌至长沙、长沙至湘潭、醴陵至萍乡等线,则主要是为了商务。至于更多的支线:山东掖县之沙河至胶州,胶州至青岛;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徐州至台庄,安庆至芦州,徐州至宿迁等,也主要是为了商业上的需要。(见盛档:盛宣怀《电线设立情形》,光绪二十八年。) 事实上电报在军事经济方面确是起到作用的。例如:1882年中国军队在壬午兵变中的成功,“实赖电报灵捷”(李鸿章:《商局接办电线折》,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李书》奏稿卷四五。);1887年漠河金矿的创办,“一切雇募矿师、购办机器、招募商股等事,均赖安设电线”(黑龙江将军恭镗等奏,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第三八三页。),而矿厂成立后亦赖电报沟通了与市场的联系。 由此可见,盛宣怀所积极倡行的商本商办,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起着抵制的作用。 三 盛宣怀所推行的商本商办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起的抵制作用,是经过激烈斗争和反复较量而取得的。仍以轮电二局为例来说明。 对轮船招商局,盛宣怀认为“按万国公法,凡长江内河商贾之利,国人专之。”但洋轮已入内河,在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清政府无力把侵略势力驱出国门,那只有走经济上与之竞争的一条路,盛宣怀坚持“彼客也,我主也,但有反客为主之机,断无喧宾夺主之理”(盛档:盛宣怀《轮船招商局始末》,光绪八年。)的原则,与两个劲敌怡和、太古轮船公司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自1877年归并旗昌以后,怡、太不断地削价争揽,时“战”时“和”。“和”的表现即“齐价合同”的签订。这个合同,招商局与怡、太在洋务运动的1878、1883、1893年签订过三次,盛宣怀亲自参与指导签订的主要是第三次,故以这次为例。 1890年第二次六年“齐价合同”期满,怡和、太古尤其是太古,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提出多占分数的狂妄要求。太古在奢欲得不到满足时,汉口太古将水脚先行滥放,“始则七、八折,继而五、六折,三、四折,近日竟跌至一折或五厘”。(盛档:汉局《施肇英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怡和虽不到太古那样“滥放”的程度,但也间有“跌至一折”的。招商局对此也不能不相应的跌价。但盛宣怀认为,招商局不能盲目跟着跌下去,一定要有一个限度,他规定至少要“收四成至三成五”(盛档:汉局《施肇英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不能再低于此数。如果怡、太硬是只收一成水脚,那就让给它们装载好了,但这决不能长此下去的,因为开办公司就是为了赚钱,怡、太这样低的水脚,“仅作上下脚力尚且不敷”,怎么能不拖垮呢?果然不出所料,不多天汉口“太古洋人知亏耗过巨,意欲加收水脚,客帮不允,反多口实。”而上海太古又“甚不合意”,颇有微言。所以汉口“太古可谓弄巧成拙,作法自毙矣”。(盛档:《施肇英、董葆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盛宣怀致书诸董事:决不能在貌似强大的敌人面前气馁,宁可每月少收十余万两,也决不屈服于太古。他很有信心地说,只要“振作精神”,讲究策略,必“能争胜怡、太”。(盛档:《盛宣怀致梅西函》,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当太古“坚执长江一定二十七(分)、天津三十一(分)不减分毫”时,盛宣怀表示“断不能允,毋庸再议”。对于怡和“分数彼要比去年冬(指1890年冬——引者)议多三分”,亦“断不能允”。他说:“宁可亏本再斗,决不能为大局失此体面。”但盛宣怀也没有把话讲绝,他对谈判代表陈猷说:“如有可顾全我体面之法,我稍吃亏,尚可商议,此弟立定主见不可动摇也”。(盛档:《盛宣怀致陈猷函》,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五日。)这种斗争灵活性,得到进行交涉的局员唐德熙、陈猷等人的支持,他们也认为,“若不得江津七十七分(按指长江、天津两航线相加的分数——引者),决计不立合同。……我局既已减至七十七分,必须守定此数,不可再减,以观动静。”他们相信,愈迁就则距离愈远,只要坚持下去“暂不与谈,料其必来迁就矣”。(盛档:《唐德熙、严潆、陈猷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事实证明盛宣怀斗争和谈判方针是正确的,终于迫使怡和、太古坐下来谈判而签订了合同。 在谈判中,盛宣怀善于利用矛盾和讲究斗争艺术。当1891年怡和企图多占便宜,提出无理要求时,局员们想联合太古共同斗怡和,盛宣怀及时指出,“恐太古也不是好人”,怡、太既都非好人,故“不可不小心”的“时备戒心。(盛档:《盛宣怀致陈猷函》,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盛宣怀再三叮嘱:“既防太古明与倾轧,也须防怡和暗中损我。”(盛档:《盛宣怀致施子卿函》,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盛宣怀等人都懂得:“向来太古轻视怡和,而怡和负气不下,须待怡、太两家有意愿和,议定头绪,乃可与商局合拍”(盛档:《沈能虎禀李鸿章》底稿,光绪十七年。),然后坐下来谈判才有效果。盛宣怀抱定一个原则,即宁可向客家迁就,也不向怡、太迁就太多。他说:“遇有太古暗中损我,则尤当自己与客人暗中迁就。总不可比怡、太分数太少,以长他人之气焰。”(盛档:《盛宣怀致陈敬亭函》,光绪十九年四月。)总之,盛宣怀充分利用了怡、太之间的矛盾和权衡了怡、太与顾客之间的轻重,以做到对轮船招商局有利。当怡和骄狂太甚时,则联合太古“将脚价稍减一点”,使怡和“无能施其伎俩”(盛档:《唐德熙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当太古跌价争揽时,又联合怡和,“每人以一、二船贱价租与潮帮以累太古”(盛档:《唐德熙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如怡和、太古联合起来对付招商局,则采取迁就客家以拖累它们的策略。这些手段发生了效果,使局、怡、太签订的合同基本上是平等的。1893年执行新订的合同以后,招商局股票价格很快从每股四十两上下涨到一百六十两。 轮船招商局对外抵制是通过斗争达到目的,电报局也有类似情况。在设立电线开始不久,早于1882年盛宣怀就明确说:“若各国另设沿海水线,则海口皆通,□□乎有入江之势。从此我有机要,彼尽先知;我有官书,转须假手。反客为主,关系匪轻。”他认为中国非“争先人一着”地“自行设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盛档:《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光绪八年。)盛宣怀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与英国大东、丹麦大北两电报公司为主的外国电报企业进行斗争的。 1880年中国设电线前后,大东、大北都在沿海设海线。大北在吴淞并设有旱线,它在厦门之线也已上岸。中国电报局成立后,援照同治九年关于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海线界限的原议,进行交涉。1883年前后是谈判的紧张阶段,盛宣怀这位电报局督办当然处于交涉第一线。交涉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是拆除丹国吴淞旱线和厦门上岸之线。在那时,英国大东公司正由上海至香港设海线,它援丹国吴淞旱线与厦门上岸之线为例,坚持要从福州上岸。盛宣怀清楚地意识到,要阻止英商海线在上海进口上岸,“不得不议拆丹国旱线,以保中国自主之权,并以服各国商人之心”。在福建,他认为“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故既需即时拆除大北吴淞至上海之旱线,也必拆掉它厦门上岸之线。(盛档:《盛宣怀禀闽浙总督宪何》,光绪九年三月十七日。)而对于大东公司则按此原则议立合同,在其亲拟的合同稿中规定:“大东公司所设海线只能由吴淞口径达香港,所有沿海各处,无论已开未开口岸,一概不准添水线。所过口岸,亦不得分设线端,亦不得援照上海与旱线接头递报,以归中国自主之权。”“中国电报局由上海至吴淞设立旱线一条,与大东公司海线相接。所有旱线悉由中国自主”,“中国允许大东海线做至吴淞口为止,与中国旱线头相接。如大东须趸船,即泊吴淞口近口处所”。(盛档:盛宣怀拟《与英商大东公司订立合同议稿》亲笔底稿,光绪九年。) 与大东公司议立合同的同时,即和大北交涉,拆除其吴淞旱线和厦门上岸之线,允许其在上海附近之南汇羊子角设趸船将线头置于其上,福州则设于川石山。但大北商人只同意拆除吴淞至上海之旱线,不答应拆掉厦门上岸之线,说“厦门线端系由海滨岸边由地下直达屋内”,不应与吴淞旱线一样拆除。盛宣怀反驳说:厦门“虽与私立旱线有别,然已牵引上岸”,显违同治九年原议,我如果同意不拆,即无以拒大东线端上岸,他说:“若以丹商线端在厦上岸可不理论,恐他日英商水线延及福州、汕头,亦必援照由地下引至洋房之内。届时难以专拒英商。”(盛档:《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九款》,光绪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坚持了厦门上岸之线与旱线一样的拆除。谈判结果基本上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办理,从而维护了电线的主权。盛宣怀曾概括地叙述这种对外抵制维护主权的情况说: “先约丹国将已造上海陆线拆去归还中国,其水线端皆止许至吴淞为止。丹有厦门海线,年久不复能拆,英商援以为请。其香港至上海海线,经过福州亦准于川石山设一线端为过脉,仍不得入福州。我电局并与香港总督平心理论,亦得于香港设中国电报局,而拆其僭造之新安陆线,大费唇舌始克立定年限,会订水线相接合同。其他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皆与各该国订立条款至详且慎,不使逾尺寸。”(盛档:盛宣怀《电线设立沿革》,光绪二十八年。) 综观盛宣怀集商本以商办和轮电等企业经营情况,确是有积极的一面的。 四 在盛宣怀集商本商办洋务企业确有积极进步一面的同时,也已表现出颇大的消极反动面,这一面的源头在于他“办大事”是为“作高官”,他因这,而利用商资抵制洋商与洋商争利;但也因这,而必然排挤商人侵夺商权。官夺商权就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清政府的意志办事,并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这就意味封建性买办性对企业渗透的日益加强。我曾在《论盛宣怀》一文中说过,盛宣怀“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以凌商”。(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用商力”但又“凌商”,是盛宣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致命伤。现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说明盛宣怀“用商力”而又“凌商”,从而导致他向反动方面发展的逻辑过程。 招商局创办时,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最早的轮船章程稿就是李鸿章指令他草拟的。由于这种身份,所以他在开始即企图操纵局务。1872年夏间,唐廷枢、朱其昂到天津与李鸿章的代表津海关道丁寿昌商谈轮局筹建问题,盛宣怀恰好陪同刘铭传“作沪上之游”(盛档:《盛宣怀致朱其昂函》,同治十一年夏。);接着因患足疾到常州家乡养病,“杜门不出”(盛档:《盛宣怀致朱其诏函》,同治十一年夏。)。丁寿昌一再致书盛宣怀催促他“刻日办装北上,以便面为商酬,迟恐此局一定,未便另添总办矣”(盛档:《丁寿昌致盛宣怀函》,同治十一年夏。)。这就是说,你盛宣怀不来天津,商局总办一席可能不是你盛某而是别人了。但盛宣怀这时并不很想任轮局总头目,因为在创办人中对于官款官办还是商本商办仍有分歧意见,他要看看是否按自己的意见办事,抱着等着瞧的态度。下面一封给丁寿昌的信很能代表他当时的思想,故录之: “中堂传谕:宣怀如愿出为综理,即日办装北上,以便面为商酬,迟恐此局一定,未便另添总办,等因。宣怀现因足患湿气,一时未克来津,想云甫、景星诸君万难久待。谨先缮呈节略两扣,伏祈垂察。并乞密呈中堂。如蒙采择,宣怀不敢自耽安逸,必当遵饬先行合同和衷商办,稍有头绪,即赴津门面禀一切。已事之商榷,较诸未事之空谈必有胜者。倘以所请概难准行,恐无以扩充即无以持久。宣怀材疏力薄,深虑无裨公事,与其陨越于后,不如退让于前。明察如我公,必能为我斟酌出处也。”(盛档:《盛宣怀致丁寿昌函》,同治十一年夏。) 从这封信可看出:(1)要盛宣怀“即日办装北上”去竞争首届“总办”,是李鸿章的“传谕”;(2)盛宣怀不是不想去当总办,而是必须按照他所拟“节略”中的商本商办主张去办,他才“不敢自耽安逸”的去干,因为他坚信只有他的这套主张才能使轮局不断“扩充”和“持久”;(3)他的商本商办主张“如蒙采择”,他愿意实践一段时间再去天津汇报和商谈。因为“已事之商榷,较诸未事之空谈必有胜者。”盛宣怀是讲究实际的,他认为如果第一个民用企业“无以扩充”、“无以持久”而失败了,“致富”、“分洋商之利”等目的固然不能达到,自己的名誉也会扫地的。后来招商局经营方针基本与盛宣怀的意见一致,或者说实现了盛宣怀的主张,因而赢利丰厚,不断扩充,“持久”也有把握,他当然想来掌权了,但权已掌握在商股代表唐廷枢、徐润手中,盛宣怀乃屡次提出辞职。 盛宣怀的名义是管理漕运的会办,但实际是李鸿章派他来掌握全权的。如果无总办或督办之名,却握有实际的权力,成功了他应推为首功,失败了,处于第一线的唐、徐任其咎,真是一举两利。但这个如意算盘没有达到。唐廷枢、徐润既为商总,他们当然要按照商办原则经理企业,“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们请政府“免派委员,除去文案名目,并免造册报销”,一切按“买卖常规”办理。(盛档:《唐廷枢、徐润、张鸿禄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这使企业办得很有起色,得到众商拥护,使官难以插手。盛宣怀未能握全权,却想派亲信参与内部事务,他通过朱其诏荐亲朋于局,得到的答复是:“实缘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渠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盛档:《朱其诏致盛宣怀函》,同治十二年。)盛宣怀对此非常不满,在他看来,自己在“局中(被)视为无足轻重之人”(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亲笔底稿,光绪五年。)。这话也确有些近似。 议并旗昌时,盛宣怀正在湖北勘矿,徐润说:“当初议时,唐景翁、盛杏翁均不在局,只余一人主持,三日之内已将草约主决。”(《徐愚斋自叙年谱》第三七页。)盛宣怀颇有怨言,他事后向徐润发牢骚说:“忆去冬吾兄亲来武穴,议办归并旗昌之举,弟即说,筹款不难,而特以船多货少洋商争衡为虑,故于秣陵、上海之行,晨夕与诸公再三辩论,逮至所虑各层,吾兄与某翁均有解说,乃始毅然请于幼帅,以定此数。弟复虑局面过大,未可以弟不谙商务之人空挂虚名,致误实事,故即禀请派人更换,不蒙允准。正月间,驰抵上海,即欲妥筹整顿,乃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且旗昌一切布置,均不及会商而已定矣。”(盛档:《盛宣怀致徐润函》,光绪三年。)话虽然不少,但说来说去的中心意思在于“无权”。什么“空挂虚名”故“禀请派人更换”;归并旗昌“一切布置均不会商而已定”;“所虑各层”唐、徐不虚心听取而“均有解说”;“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等等。归根到底是官与商的矛盾,如果大权握于他盛宣怀手中那他就不会有意见了。 不久,朱其昂去世。盛宣怀玩了另一花招,他“坚请督办”。招商局开办时,没有督办,只有代表官方的朱其昂、盛宣怀两位会办。朱其昂死后盛宣怀为什么要“坚请督办”?当时有人说他有两个目的:一是“鉴于此局之难支,自求脱卸”,请别人来当督办;二是“鉴于工商之有成,故求拔擢”,请派他盛宣怀自己来当督办。这二者都有可能性,我看后一个可能性更大些。盛宣怀曾向李鸿章解释,说前者是求退,后者是求进,二者都不是他的本意。这是不是真情呢?下文向李鸿章讲清楚了。他说: “今昔情形不同,得失关系尤大。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刻勉,反觉遇事疏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职道在局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此局外人认为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倘再粉饰因循,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职道居今万无中立之势。”(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亲笔底稿,光绪五年。) 这里实际讲了两个意思:一是“任事诸人”很不理想;,二是他盛宣怀在局“无足轻重”,诸事“绝未一语会商”。还是一个“权”字。所谓“无中立之势”,实际上是他盛宣怀与唐、徐“无中立之势”。或则去唐、徐我盛某来大权独揽,或是留唐、徐我盛某扬长而去。其真实意图当然是“大权独揽”。他借“或谓”的口吻向李鸿章表达这个意思说:“奋身独任其艰难,未始不可挽救全局。南洋大臣谓军营中常于营官内拔一人为统领,正名定分,何各不相下?”盛宣怀对这话进行解释说:“商务宜联以情,非如营务可以绳以法。等而齐之,则名不正者事不成;驾而上之,则心不降者气不协。故中立不可,进更不可。”(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光绪五年。)盛宣怀与唐、徐到了“各不相下”的程度,“等而齐之”不可,“正名定分”的擢为督办以“驾而上之”,唐、徐必不能“心降”“气协”的。因此,“坚请督办”即是去唐、徐而任盛宣怀为督办。这也就是盛的所谓“本意”。其实,这件事朱、盛等人早就酝酿了,请看以下事实。 第一,1876年旗昌股票跌至七十两左右,随后又曾骤涨至一百○三两,唐廷枢、徐润二人在七十两一股时买了一千六百余股,而朱其诏一股未买,其原因据朱其诏说是“因雨之分咐并嘱福昌不动手,以致一股不到手。”朱气愤地告盛宣怀说:“虽财运之不通,实雨之误我,气极!”朱其诏乘机大发怨言,说:“局中事宜全仗景翁、雨翁,诏亦不过随声画议。”但尽管埋怨自己在招商局无权,却对盛宣怀的要辞去局差“力劝……暂缓”。(盛档:《朱其诏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年五月。)朱其诏的“不过随声画议”,与盛宣怀的“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如出一辙;而“力劝……暂缓”辞差,就是要盛宣怀斗争下去为后来“坚请督办”的准备和步骤。 第二,从光绪三年朱其诏与丁寿昌的一段对话看,也可明显看出“坚请督办”的酝酿过程。 丁寿昌问:“五人(按指朱其昂、朱其诏、盛宣怀、唐廷枢、徐润——引者)意见如何?” 朱其诏答:“因公不合间或有之。” 丁:“归并旗昌后生意如何?” 朱:“太古、保康减价争衡,恐难收利。” 丁:“既如此,五人更宜同心竭力做去,不可稍有懈心。至于告退之说,一概不可。唐景翁何制军要留闽,沈制军似已答允。……如放其去,杏翁能兼其任否?” 朱:“局中银钱,当时曾说盛、朱筹官款百万,唐、徐招商股百万,此时唐、徐尚未交卷,曳白而去,未免贻笑。”(朱其诏以此事请问盛宣怀:“任其曳白而出耶?抑并欲照前章程仍倩其专责揽载耶?示我主意为祷!”)(盛档:《朱其诏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 从这段丁、朱的问答和朱向盛的“请问”,可以看出:(1)官商间的矛盾确实不小;(2)朱其诏想趁闽浙总督何□要留用唐廷枢之机夺其总办权。权夺到什么程度?让其“曳白而去”的干脆离局,还是保留一个“专责揽载”?这要由盛宣怀来定夺。至于唐廷枢这个总负责人走后由谁来接替?显然是盛宣怀了。丁寿昌下一个问话可知。 丁问朱其诏:“闻人说局事杏生有独办意?” 朱答:“不但杏生无此意,且吾等均有脱卸之意。”(盛档:《朱其诏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 朱其诏的话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为什么?(1)“杏生有独办意”,丁寿昌一定是有所据而云然;(2)朱其诏是“力劝”盛宣怀“暂缓辞差”的,怎么又“均有脱卸之意”呢?(3)朱其诏的《致盛宣怀函》中,在丁寿昌的“闻人说局事杏生有独办意”句旁特地加注:“吾弟(指盛宣怀——引者)闻之可□(勿)问。”叫盛宣怀“勿问”其事,实际就是示意正中下怀,造一点“独办意”的舆论也并无坏处。 从上述一系列事实看,盛宣怀的“坚请督办”,即是他自己企图当督办无疑。 正当盛宣怀“坚请督办”尚未到手的时候,发生了董□翰、王先谦等人弹劾招商局盛宣怀营私舞弊案。盛宣怀很庆幸他居于会办之职而推卸罪责于唐廷枢、徐润说:“招商局事权悉在唐、徐二人,众所共知。……若舍唐、徐而问及鄙人,犹如典当舍管事管帐而问及出官,岂不诬甚!”他称这种对他的弹劾是“莫须有之奇案”。(盛档:《盛宣怀致胡雪岩函》亲笔底稿,光绪七年二月初八日。)李鸿章的观点当然与盛宣怀一致,他打算派员查帐,以便借口对付唐、徐。但这遭到唐、徐的抵制,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招商局是商股商办,与官无涉,如果说因商局借用官款而来干涉,那我们只要“官帑依期分还,帑息陆续缴官”就行了。并声明“嗣后商务归商任之。盈亏商任,与官无涉。并乞请免派员查帐之议。”他们进一步指出,“官商本是两途,名利各有区别,轮船揽载是为利,非为名,生意一端未有利不敷而能持久也。……夹杂官商,实难全美”。(盛档:《唐廷枢、徐润、张鸿禄禀李鸿章》,光绪七年。)弹劾案未能归罪商总,却集矢于官方代表盛宣怀,盛宣怀不得不于1882年暂时离开招商局。他赶走唐、徐的目的未达,自己却被撵了出去。 然而,盛宣怀的离开招商局是以退为进,他有李鸿章作后台,正在伺机将唐廷枢、徐润挤出去。这个时机果然等到了。1883年上海出现金融倒帐风潮,唐、徐等特别是一直主持局务的徐润亏欠了巨款。李鸿章派了徐润的死对头盛宣怀到招商局查处整顿。盛宣怀卷土重来,落井下石,他借着官势欺压徐润,搞得他“家产荡然,生机尽矣”。(盛档:《徐润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徐润在事后说明此事原委之余而申述其被欺压的原因说:“润既挟孤直之行,素无奥密之援,致奉参革;兼以泰山压卵,谁敢异言,致润有屈莫伸。”他指责盛宣怀那样对付他“其居心尤不可解”。(《徐愚斋自叙年谱》第三九页。)徐润说自己“无奥密之援”,可谓一语中的,但说盛宣怀的“居心尤不可解”就糊涂了,其实是很可解的,那就是盛宣怀“利用官势以凌商”,于1885年攫得了他多年谋而未成的督办之职。而且不久即升任山东登莱青道,“似官而为官”了,此后官阶不断高升;官阶的高升又促使他更快地成为大资产阶级代表。“办大事”“作高官”的宿愿实现了。“无奥密之援”的徐润,则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但他一直被盛宣怀歧视着,当1891年徐润亏欠案了结之后,谢家福向盛宣怀推荐徐为招商局总办,认为总办一席非徐莫属并以去就相争。盛宣怀非但耿耿于怀地说,“弟从前去差,皆雨之去我也”,而且斩钉截铁地说,我与雨之“两人不能再合”,“再合”还是会出现“太阿倒持”的局面的。从而批评了谢家福“于雨之以去就争”的“错误”态度。(盛档:《盛宣怀致谢家福函》,光绪十七年。)显然,盛宣怀把1884年前商总徐润掌权看作是不正常的“太阿倒持”,而将他这位官督办掌权才看作是正常现象。 盛宣怀既把官督办握企业之权看作是正常的现象,这就是排挤商人管理企业,反对商办,实际上实行了商本官办。权力归于督办了:由原来“商总为商局主政”、“总局分局栈房司事人等,由商总商董挑选精明强干朴实老诚之人”充任(《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一四三页。),改为“用人理财悉听(督办)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一五六页。)。这样,洋务企业就日益增多地渗透买办性与封建性。因为清政府就是买办性日益浓厚的封建专制政府,代表这个政府的“官”去操企业之权,只能是使这些企业买办性封建性加强,民族性日益减弱。例如:招商局因大借洋债而遭洋人控制,仅1885年借汇丰三十万镑,就使英人对商局有监督财务经营之权;三家“齐价合同”固然是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不足为盛宣怀病,但合同作了“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盛档:《招商、怡和、太古订立宁波、长江航线合同》,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规定,则是与外商联合垄断以扼杀民间航运;封建勒索报效仅1894年西太后“万寿庆典”招商局就报效五万二千余两,1899年至1903年四年中,竟从折旧项下“垫支三十八万余两”(《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二七五页。)报效银;电报局从它的第三年起至1902年,清政府无偿的提去银一百四十二万元。等等。洋务企业向官僚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了。到1911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以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为标志,利用官的力量,也即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后台,将轮船、电报、铁政、铁路、矿务、银行等大企业联缀起来对国民经济开始实行垄断,形成为初具规模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了, 由此可见,盛宣怀利用商本办企业的同时,挟官势以凌商的发展的过程,就是他由积极面为主逐渐转向消极反动面为主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由民族性很强的资本主义日益增多地渗透买办性封建性从而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个逻辑过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日益加深下植根于盛宣怀“办大事”“作高官”的一个本质。他为此而坚决主张集商本不惜与官僚们发生矛盾;为此而与洋商的侵利作斗争;为此而“利用官势以凌商”侵夺商权;也为此而与洋商妥协、扼杀资本主义的民族性,引向官僚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198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