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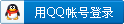  x 陈独秀对苏俄经验的接受、反思与超越 作者:王福湘 人类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风雨苍黄之中,产生了一代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引导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知识份子。他们由于理论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歧,曾经形成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的可悲格局,终于两败俱伤,出师未捷身先死,其领军人物陈独秀和胡适都是失败的英雄。逝者如斯,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术潮流也与世浮沉,自由主义的呼声颇有压倒共产主义之势。有人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后一句预言还有待时间验证,前一句断言其实并不太准确。就二十世纪上半叶来说,对中国社会思潮和历史进程的实际影响之大,先后转向共产主义的陈独秀和鲁迅的确都要超过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而陈比鲁犹有过之,其结局虽都是悲剧,但陈独秀命运的悲剧性则显然无人可比。目前学界对鲁迅和胡适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陈独秀的研究却跟他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关于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若顾及全人和所处的整个时代,想一言以蔽之,那么,也许还是借用鲁迅的话较为确切,即:陈独秀一生都是「革命的前驱者」1,他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和先驱,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和启蒙思想家。他毕生致力于变革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别注重从制度上探索中国和人类的未来,勇敢地进行政治革命的直接行动。他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最光辉的旗帜,最优秀的楷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最正确的代表。 一 像接受维新思想和从事启蒙运动一样,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经验在时间上也是属于近代中国先进知识份子中最早的一批,而且,他的思想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自我否定和更新,始终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中。陈独秀早在1920年2月题为〈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中就使用了「与时俱进」一语,说明「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时移事变,教育要「与世界一齐进步」2。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态度,最能体现陈独秀与时俱进的精神。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4社会主义学说流行和共产党执掌政权的「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5。〈贫民的哭声〉等文毫不含糊地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之后,他的启蒙和革命活动重心从知识份子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军阀政府的逮捕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东来,加快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步伐,1920年5月陈独秀即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继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接受了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和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用来研究人类和中国的社会及其发展进化的历史,探索中国政治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从1920年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后到北伐战争前的几年里,写了许多文章,作了大量讲演,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蓝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驳斥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且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说,他把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转变成了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旗帜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没有变,革命的道路即理论方法武器手段变了。他认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其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是经济制度的革命6,而改革社会制度的手段就是阶级战争。他这样概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 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而「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7,即「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份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8。他又根据列宁的著作,把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两派的对立归结为:前者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后者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前者是真马克思派,共产主义,后者是修正派,改良主义;而「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9。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理论上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是依靠共产国际即苏俄帮忙的中共领导人。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但在行动上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和苏俄顾问的错误指挥,导致国民革命失败。这次失败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血的教训和共产国际嫁祸于人的行径使他首先踏上反思并进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艰苦而漫长的历程,他仍然是「革命的前驱者」。 二 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及其衍生形态的复杂性,由于二十世纪中国、苏俄和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在陈独秀身上又很明显地表现出人类认识自我和认识环境的局限。这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进,苏联的成功和失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人性的变化和矛盾,总之,现代中国和世界的一切人事,都呈现为或短或长的过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一切都在运动中,联系中,矛盾中。当事情的真相还没有充分暴露或正在逐渐暴露的时候,当科学研究还没有把人的本质完全揭示出来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就难免犯错误,简单片面机械,或出现曲折和反复。陈独秀全盘接受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当成导师和朋友,称赞他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包含了这类时代的局限。他在树立了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新观念以后,还保留着启蒙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等原有观念,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历史性变化的问题,即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地域性及个性的关系问题,思想上不无矛盾。他在强调阶级性党派性时,否定全民性国民性的存在,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却又说老庄以来的虚无主义是国民性堕落的根源。陈独秀作为革命前驱者和领导者,更多地关心政治经济问题,做的工作多,犯的错误多,思想矛盾也多。他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对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有的话,这个阶段实行甚么样的政制,思想是模糊的,犹疑不决的。他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对民主的性质、价值和意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以至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归属于资产阶级,有时又把民主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认为前者是少数人的、形式的、虚伪的,后者是多数人的、实质的、真正的,更未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贫穷的陈独秀却有时间。而且,他的「世界识见」异常广博,经历更非一般人可比,尤其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苏俄内部材料。他不背家庭包袱,一身轻松干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先交卸了职务,后开除了党籍,成立托派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关了五年,出狱后积极宣传抗日,却被王明、康生诬为汉奸,从此穷途飘泊,寄居四川乡下,靠北大同学会照顾艰难度日,于1942年病逝,比鲁迅晚六年。这是极为宝贵的六年。他把监狱当成研究室,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几年,一息尚存,依然著作研究不止。从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以后开始的革命反思,经过狱中的深思熟虑,产生了飞跃,又总结了国内外特别是苏联的最新经验,愈来愈彻底,终于达到那个时代的理论前沿。陈独秀至死也是「革命的前驱者」。 在长达十五年的反思里,陈独秀不断逐步否定前一阶段所接受的斯大林式布尔什维主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寻求中国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可贵的思想贡献,从理论上和宏观上解决了建设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世纪难题。 三 抗战初期,陈独秀作了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甚么而战?〉、〈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命题。他用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作用来解释现代国家和国民精神的盛衰强弱,提出中国二千年来停滞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新观点,「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脚色的,也终于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份子,……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10他深知资本主义制度含有缺点与罪恶,但根据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状态的比较分析,确认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在内部经济政治不成熟和外部影响尚在等待的条件下,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而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引用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加上一句:「在中国更是如此!」11他相信「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但在具体研究了几个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之后,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又在深入研究了苏俄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指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民族工业,决不能学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学为体的洋务派,也「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2坚持真正的唯物史观,使陈独秀不仅得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的结论,并且更彻底地认为13: 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这些远见卓识,也已为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所确证,不只对中国,而且对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有重大意义。在经历鲁迅所预言的「中国式之乱」后,中国终于重新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比陈独秀晚了半个世纪。 四 陈独秀对民主与专政问题的反思开始最早,时间最长,文字最多,思想最深刻最前卫。这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认识过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亲身经历体验了官僚主义领导集团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扼杀党内民主的灾难性后果,从1929年起奋起批判反民主的官僚集权制,指出14: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谟克拉西」,以所谓「铁的纪律」等借口为武器,「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像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15他引用列宁的话来证明党内民主的重要,也仍然以列宁的话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说:「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他又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是「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才是我们的「前途」16。他同时认为,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17 在托派活动期间,陈独秀围绕着「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中国托派中反对国民会议的极左派主张辩论,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思想突破。突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实现的。他在狱中继续研究国际政治和中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关键就是民主问题。同狱内外托派成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在清理和否定自己前一阶段的某些错误。他更加强调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关联中国无产阶级命运,「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警告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18。他对《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作了更新的解释,赋予了更深刻更崇高的意义。当时在狱中照看他的托派成员濮德治回忆,陈独秀认为今天大讲民主科学,并未过时,反而更加需要。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陈讲了他对人类社会民主历史的研究,「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做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而奋斗。」陈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批评托派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总之我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人类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陈独秀认为,他把民主与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并未违反阶级分析的原则,「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益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苏联就是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样式,还自诩为马列主义。马列地下有知,想会慨叹呜呼的。」19濮的回忆文字会有出入,但基本传达了陈的思想。他在狱中写过一篇〈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作为反思民主问题的理论成果,发表在托派机关报《火花》,指出: 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级的内容与形态。……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他改变了以前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看法,肯定「我们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20。出狱前他还写了一篇〈孔子与中国〉,从高扬民主的观点继续五四时期对孔子礼教的批判,从中国近代史上民主运动失败和尊孔潮流高涨的逻辑联系中揭示礼教反民主的本质,重申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21出狱后,他根据历史事变的实际发展,继续反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22,在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中,终于将「吾辈」即国内外托派包括他自己以前关于民主问题的见解「彻底推翻」,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具体的意见,其中他对民主政治的内涵作出了新的明确的界定:「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23「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24对以前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价值,不但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为之摘掉了「资产阶级」帽子:「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即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25与此同时,他去掉了以前涂饰在「无产阶级民主」头上的虚幻光环,指出其基本内容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致性:「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26「『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27「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28他总结了斯大林独裁的反面经验,从而论证了所谓「无产阶级独裁」的虚假性。独裁即专政,不过专政为中性词,独裁含贬义。陈独秀用词上的变化显示出前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他说29: 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因而有了新的飞跃,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高度和历史深度:「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他告诫他的托派年青朋友:「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30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否定了他以前相信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超越了马克思,或者说修正了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结论是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为依据的,并且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所确证,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理论与实践真正紧密结合的基础上,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在逝世前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深刻性和创造性,不但已经被历史证明为真理,且对后人极富启示意义。陈独秀从整体的过程中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并上升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为人类知识积累贡献了宝贵财富。 五 陈独秀晚年对鲁迅和托洛茨基的态度也是他反思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的积极成果。 鲁迅那封著名的至今仍有争议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虽是他病重时由冯雪峰主动代庖,但鲁迅既然同意署名发表,就应该算为鲁迅的文章,信中内容也都是鲁迅认同的思想。「事实胜于雄辩」,问题是鲁迅并不清楚斯大林反托和大清洗的真正事实,而用斯大林的苏俄的「成功」来说明托洛茨基「晚景的可怜」,倒颇有点自己反对过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式的历史论」的气味。最严重的错误是搬用斯大林诬陷苏俄托派为帝国主义间谍的谎言的逻辑,明白地暗示中国托派「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接着严厉地警告:「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31这就坐实了前句的暗示,为王明之流造谣诬托陈派为日寇奸细提供了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救国时报》在报导鲁迅的信同时发表的社论开端,连篇累牍地大骂托陈派是汉奸匪帮,甚至在陈独秀释放以后,还要求国民党政府,「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乔等等汉奸匪徒」32。鲁迅这封信被他们反复登载,引以为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独秀在监狱中得知了鲁迅这封信,反应之强烈是情理之中的。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回忆,陈「大发脾气,问我们为甚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33但在鲁迅逝世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短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非常冷静和公正地评价了鲁迅,肯定《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所以作品「特别有价值」,陈对鲁迅与政党的关系极具洞察力: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 他还「真实的鲁迅」以「人」的本来面目:「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最后,针对当前现实,颇有共鸣地指出:鲁迅对抗日联合战线政策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34 「独立思想的精神」,也就是反专制的精神,正是陈鲁二人最基本的共同点。陈独秀对托派的态度也最能体现这种精神。他在得到托派各种重要文件,特别是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后,「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35,于是毅然决然转向托派,并担任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一面开展「国民会议」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一面宣传托氏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主义。他跟托派成员不停地争论,经过艰苦的长期的狱中反思,终于在出狱后和托派断绝了组织联系,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努力宣传抗战。他向托派成员郑重宣告36: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进一步的反思,使他彻底认清了「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谬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37他致信托洛茨基,断言中国托派「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份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38其实托洛茨基就是陈独秀所批判的极左派,所以,这封信也是向托氏宣布他和托派在思想上的决裂。把陈独秀致托氏的信和鲁迅答托派的信加以比较也很有意思,同是对托派的否定和批判,陈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进行理论的分析,得出科学的评价,鲁以斯大林的谎言为依据,进行主观的推测,得出荒诞的结论:两人反托派的反法竟完全相反。 陈独秀晚年在极端困难的生存条件下,用提纲式短文写出〈我的根本意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这也是他反省自己革命一生的经历与功过的理论总结,是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言。这种价值重估是「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着理性的批判态度,既不迷信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权威洋教条,他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如胡适所言是「终身的反对派」39。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的革命道路上,陈独秀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最后的价值重估也是一种接受,而且最富科学性和前瞻性。他永不倦怠地探索真理、实践真理的思想和行动,无论其成败得失,都已化为不朽的精神的光焰,照耀我们在为真理而斗争的人生路途上与时俱进,奋然前行。 注释 1鲁迅:〈《自选集》自序〉,载《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456。 2陈独秀:〈新教育之精神──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页97。 3陈独秀:〈随感录〉,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页525。 4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页364。 5陈独秀:〈纲常名教〉,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页515。 6陈独秀:〈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页315-16。 7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演讲〉,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页470、477。 8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页378。 9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页253-56。 10陈独秀:〈民族野心〉,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490-91。 11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498-99。 12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15、517、519。 13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62。 14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2。 15陈独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121-22。 16陈独秀:〈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147、156。 17陈独秀:〈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285。 18陈独秀:〈几个争论的问题〉,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334-35。 19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61-64。 20唐宝林编:《陈独秀语萃》(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页203-204、266-67。 21陈独秀:〈孔子与中国〉,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389。 22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55。 23同注13,页560。 24陈独秀:〈给连根的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47。 25同注22,页555-56。 26同注24,页547。 27同注13,页560。 28同注24,页547。 29同注13,页560。 30同注22,页554-55。 31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载《鲁迅全集》,第六卷,页588。 32〈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捣乱后方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救国时报》,1938年2月5日,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3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页207。 34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430。 35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96。 36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432-33。 37陈独秀:〈致郑学稼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28。 38陈独秀:〈致托洛斯基〉,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31。 39陈独秀:〈致S和H的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页567。 王福湘 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着有《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并发表论文多篇。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总第八十七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