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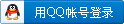  x 孙中山庚子惠州起义的性质和特点 作者:周兴梁 1900年10月6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注:关于惠州起义爆发的时间,历来有10月5日、6日、8日三种记载,本文取孙中山的说法。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0页。)是辛亥革命运动准备阶段真正举行的有鲜明特色的第一次起义。黄兴后来认为“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0页。)是有道理的。孙中山组织发动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及依靠会党和外援的做法,都给往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以深远的影响。 一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力图以武装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最早尝试。这次起义以兴中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一次具有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清军事斗争。此乃惠州起义的第一个特点。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注:《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6、509页。)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创立兴中会开始,不仅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而且还将反清武装起义作为实现民主共和纲领的主要手段,坚决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895年的广州起义计划流产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多次强调中国应改行共和政体,并计划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1897年8月,他在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中指出:“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且吾主张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为先导者”。(注:宫崎寅藏著、P·Y译校:《三十三年落花梦》,大达图书供应社1902年刊行,第35-36页。)他在谈到起义地点的选择时指出:“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故“弟以广东为最善……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广东惠、嘉、潮三府”,不仅“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而且其地“因与台湾密尔,便于接济军火”,尤“可作起点之区”。(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184页。)当时兴中会的领导人与会员几乎都是广东人,在早期有名籍可考的286名兴中会员中,广东人为271人,占会员数的95%。(注: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可见,兴中会实际上是一个由广东华侨人士、知识分子与会党成员组成的革命团体。再加上进入近代以来,广东人民具有强烈的进取性与爱国心,及悉力毕虑期驱异族,建民治,为全国创的光荣斗争传统。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将兴中会起义的地点选在广东,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1900年夏秋间,列强的侵略罪行引发了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孙中山当时“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联军之进北”;(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4页。)主张“吾党决当立义军,遂行夙昔之志望”,“由是经营奔走无虚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把握时机加紧了广东惠州起义的筹备工作。孙这期间打算在广东乃至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1900年6月初,他在请求法国驻日本公使哈马德为起义者提供“武器或军事顾问”时,指出这次起义“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该月上旬,他在离开横滨前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9页。)同年7月,他在新加坡接见英国官员斯韦以顿等人时再指出:“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们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而没有这个行动,中国将无法改造”。(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5-196页。)孙等还在致香港总督卜力的政见书中,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建立华南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各省设立“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我们从孙中山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发动惠州起义的目标,是要在华南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此外,我们从惠州起义前后他人的言谈中,也可以看到孙中山发动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是民主共和。1897年10月,日本人山下秀实主办的《台湾新报》曾报道说:兴中会党人“总以背叛清国,革去旧政为名目”;该会渠魁孙文在“欧洲煽惑清国人及外国人捐资入会……查其用意所在,欲使清国变为合众民主国”。(注:《逆党批猖》,《台湾新报》第316号,1897年10月1日(中文版)。)据谢缵泰记载,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博士于1900年7月21日说:港督卜力赞成并支持孙等“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还记载说,8月间福罔县知事曾向外务省报告:“孙逸仙及其党徒的计划,以江苏、两广等南清六省作根据地宣布独立,作共和政体。渐次向北清张扬,推倒爱新觉罗氏,支那十八省合从(纵),东洋大共和国创立”。(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1册,台北1971年版,第270页。)惠州起义失败后的1901年春,美国《展望》杂志的记者林奇在见过孙中山后报道说:“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211页。) 综观惠州起义前后孙中山的言行和其他各种记载,我们有理由肯定他领导的兴中会发动这次起义之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以民主共和思想为指导,起义者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战——正是惠州起义的最大特点与可贵之处。这说明它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武装斗争。 当然,我们也别忘记1900年10月下旬,孙中山曾写信给刘学询,应允刘“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称谓由足下裁决……兵政一人弟自当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02页。)这是他出于救急策略考虑的权变之计,目的是为争取刘以财救济惠州起义的革命军。当时在台湾的孙中山不知惠州起义已败,一心想到义军急需饷械接济;而原指望的台湾军火援助全落空,委托日人中村弥六代菲律宾所购之械又是一堆废铁;无奈之下,他只有寄望刘学询“速代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关于这点,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已说得很清楚:孙“知道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80页。)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当时思想上对采取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尚未作出最后的抉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发动惠州起义时,明确地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将爱国救亡与推倒清廷连在一起。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和斗争水平,不仅高出农民阶级广大群众,而且也高出资产阶级保皇派。他们在20世纪到来之际高举共和革命的崭新旗帜,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引着国民去进行新的救国斗争。 二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之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和绿林。这是一次形式上会党起事气氛颇浓,而在性质上又完全别于旧式会党起事的新型武装起义。此乃惠州起义的第二个特点。 孙中山本人及其创立的兴中会,同会党有着很深的渊源与交往。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6页。)会党出身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曾指出:当时南方的三合会“以广东最盛”。(注:肖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1935年北京出版,附录第6页。)孙中山生长在三合会非常活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创立兴中会始就注意联络会党的力量以为己用。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会党具有反清传统,“会中的口头语就是‘反清复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197页。)他们在反清的问题上与兴中会有着一致性,便于兴中会实行联络。其二,会党是一支有现成组织的冲击力量,有联络利用的价值。1898年,孙中山在同宫崎寅藏谈及此时指出:“这起义必须有三合会的支援,只要跟三合会取得联络,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军”。(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其三,兴中会内有一批会党的骨干分子,具备联络会党的畅通渠道和便利条件。孙中山早在广州博济医校读书时就结识了“具反清复汉思想”的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引为知己”。(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4页。)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时,郑与其他一些会党成员加入了兴中会。他们成为日后兴中会联络会党的得力干部。 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有粤、湘、鄂同时大举的起义计划,一度对广东的三合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都进行过联络工作。1899年冬,兴中会、湘鄂哥老会和广东三合会的首领曾在香港举行重要会议,议决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后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被康有为收买为自立军的主力,粤、湘、鄂同时大举之计划无由实现。孙发动惠州起义所依靠的主力军,就只有广东惠州与嘉应州一带的三合会,及新安县的绿林。兴中会将起义地点选在惠州三洲田,固然有该地与香港的新界接壤,便于兴中总会的人员联络与物资接济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会党方面的原因:(一)该地及其东南毗连的海丰,“皆系会党出没之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且新安县的绿林首领黄耀庭等部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二)起义的总指挥郑士良既是惠州的客家人,又是本地三合会的首领,在当地的三合会员和客家人中有号召力;(三)该地在两县交界、地处偏别和山深林密的地势,有利于会党隐蔽与聚集力量。 为保证分散的三合会员能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郑士良在起义前特地把“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的好友黄福,从南洋婆罗洲请了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党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命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由于起义的头领和群众大多是三合会员,所以联络发动的办法也是采用会党传统用的手法。两广总督德寿在起义后向清廷奏称:“奴才伏查逆首孙汶以漏网余凶……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旗帜伪书大秦国及日月等悖逆字样。各匪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这表明参加惠州起义的不少会党首领及会众的认识水平,尚与孙中山所设定的奋斗目标有较大的差距。这次由革命党组织发动的起义还保留有颇浓的会党气氛。 然而需着重指出的是,尽管这次起义还有较浓的会党味,但它同以往的旧式会党起事相比较,毕竟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应当看到,由于近代广东具有风气之先的优越地理位置,一部分会党首领在与海外联系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具有较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如郑士良等就曾受过西式教育,认识到“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孙中山史料专辑》,1979年广州版,第321页。)兴中会员进行的宣传工作,也促使参加这次起义的部分会党成员产生了一些民主革命意识。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组织发动了起义,而且还取得了起义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引导广大会党群众把自己的斗争,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合在一起。粤督德寿曾对此惊呼:“逆党主谋,意图大举”,“军火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实非寻常土匪可比”。(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有的起义者在给香港报纸的信中,宣称自己是“大政治家、大会党……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权……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起义军的军令所出及一切举措,“悉以西法为准绳”。(注:参见上海《万国公报》卷145,总第19939页。)他们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从未有屠戮妇稚、焚毁乡村等事发生,其粮饷等取于乡民,均照时价给钱,“村民多燃爆竹欢迎,或以酒食慰劳,大有箪食壶浆之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页。)由于广大乡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起义军很快由最初的600多人壮大到2万余人。以上事实证明,兴中会依靠会党为主力发动的庚子惠州起义,已具有民主革命的内容,它摆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口号和自发暴动的原始状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而组织进行的一次武装起义。 惠州起义的史实告诉我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注重武装斗争。他们在从事革命之始就联络发动会党力量来举行武装起义,并力图将旧式会党的反清斗争引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他们选择利用会党这个现成的组织来作为武装起义的冲击力量,是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及其本身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这种做法是必要的和无可非议的。会党在惠州起义乃至以后的多次起义中,虽然暴露出其散漫落后的一面,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他们不仅充当了革命派历次武装起义冲锋陷阵的主力军,而且还联络、影响和带动了一部分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起来响应与投身民主革命斗争,从而促进了辛亥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 三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和兴中会在本身革命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望于外部条件、尤其是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援助而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完全依赖于海外饷械的接济援助,也是惠州起义的一大特点。 1900年夏,各国列强利用义和团事件趁火打劫,纷纷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孙中山认为这时局之变极有利于兴中会发动反清起义:(一)清政府在入侵的八国联军前面,“和战之术俱穷”,“威信扫地以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211页。)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为党人举行起义提供了大好时机;(二)清两广总督李鸿章受英国人运动,一度有宣布两广“独立”之意。他的幕僚刘学询曾为此函请孙中山“速来粤协同进行”;时何启也受港督卜力鼓动,找陈少白拉拢兴中会“辅佐”李搞两广独立。孙当时“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77页。)(三)当时的日本政府及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妄图利用兴中会之活动来向福建扩张,对孙的起义计划伪表同情,许以起义之后可相助。孙认为这些因素对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是十分有利的,而菲律宾独立军的驻日委员又应允将上年所购之枪械供起义之用,我们正可“趁机而起,建立义军,实现夙愿”。(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75页。) 孙中山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始终把惠州起义的接济工作放在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上面,而对英日等国分裂两广、福建的阴谋缺乏必要的警惕。他那时完全依恃外援,当然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原因来说,孙中山当时把近代社会的一切罪恶——包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内,统统都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认识不到造成近代中华民族灾难的总根源就是帝国主义,因而对其怀有幻想和易于轻信。就客观原因而论,孙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其革命活动的经费,全需依赖海外华侨捐助;其武装起义的军械,也全仗从外国购买和输入。他寻求外援是迫不得己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乃至以后一段时期,都对帝国主义怀有幻想,没有提出鲜明的反帝主张和相应的对外政策,而是寄望日、美、英等国能援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为践刘学询之约,孙中山于1900年6月中偕同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多人,由日本乘法国的烟狄斯号轮抵达香港海面。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后孙、李合作尝试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落空。同一天,孙中山在“佐渡丸”上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以郑士良为主将,近藤五郎、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派“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并“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3、221页。)将起义地点由广州改为惠州,起义后队伍向福建厦门进军,以便接应孙本人届时由台湾携械潜渡内地,亲自督师北上。这就是惠州起义的方略大要。 此后,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日本的援助上面。9月上旬,他在东京拜访了时在内阁任职的犬养毅,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是月底,他化名吴仲从日本抵达台湾,旋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开展工作,并与台湾总督儿玉的代表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取得了联系。孙后来回忆说“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199页。)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政府和儿玉等根本就没有援助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的诚意,他们允诺接济孙领导的起义居心叵测——妄想趁机实现其将厦门乃至福建置于日本控制下的野心。为达此可耻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于9月29日,即孙中山抵台后的第二天,以“有碍外交”为由指令儿玉:“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必须严格阻止我国人援助其事”,并于10月初禁止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诚等45人在中国登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6-247页。)另一方面,它又要后藤新平告知孙说,厦门“台湾银行分行”的地下室“有二、三百万元银币”,起义军应“到厦门去”,“既然在干革命,把这些钱抢走好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8页。)并谓他本人保证日本政府对这件事不会过于追究。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套。日本当时对厦门的骚乱比对广东的起义更有兴趣,他们正在寻找制造事端的借口,以便趁火行劫“接管”厦门。假如孙中山的起义军真的占领厦门,并敢取用日本台湾银行分行金库存款的话,那就将中日本当局的奸计,会为儿玉出兵厦门提供一个口实和幌子。 由于孙中山满心指望台湾方面的援助,所以他在惠州起义爆发后要郑士良指挥义军向闽南方向挺进。这样一来,郑的起义队伍就远离了原先计划配合起义的新安博罗之江公喜部和梁慕光部,及广州邓荫南、史坚如所联络的响应力量,而成了长途跋涉作战的孤军。这大大有利于清军集中兵力来堵截这支义军的主力。就在起义军与清军苦战前进的10月中旬,日本政府实行了改组,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重申“既不许儿玉协助中国革命,又不许日本武官投效于中国革命军,并禁止军械出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至此,孙既无法取得台湾方面的军火等接济,又不能从日本方面取得任何物资援助。他只得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带信给在三多祝待援的郑士良,信中指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页。)郑接信后被迫于10月22日解散义军,后自率数百名骨干避往香港。山田良政则因归途迷路,被清军抓获遇害。一度轰轰烈烈的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惠州起义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的原因,这就是当时革命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兴中会的革命力量还过于弱小,而清廷的反动势力却相对的强大;而起义者的军械等准备未绪,依靠的外援完全落空,及为此而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舍近(广州)求远(厦门)战略,致使几处的起义队伍没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等,则是导致这次起义很快就失败的直接原因。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表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在中国首倡民主共和,发动依靠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坚持以武装革命斗争作为反清的主要手段,是选择了一条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正确的民主革命道路。其次,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宣传作用,扩大了民主革命派的影响,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的历史转折点。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