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不太熟悉蒙古语的人来说,在十几年以前,“德都蒙古”还是个很陌生的名称。但对于操蒙古语者而言,都知道这个名称与“阔阔淖尔蒙古”(kökenaγur mongγol)以及汉语的“青海蒙古”,其意义是相同的。虽然“德都蒙古”名称在民间一直流行,但文字层面大量使用则是近三十年的事情。70年代以来,其出现频率逐渐增加,首先,在文化学术领域,很多本土蒙古族文人在文章题目或是书籍题材中,将本部落名称大都写作“degedü mongγol”,即“德都蒙古”。特别是一些民间传统文化整理研究作品[1],一直以来基本都使用了“德都蒙古”,而其汉译名称或者版权页的汉文标题往往写作“青海蒙古”,这早已是约定俗成的模式了。与此同时,偶尔也出现“上蒙古”或者“德都蒙古”等意译或音译的汉文标题。80年代还有文章试图解释“德都蒙古”名称起源问题[2]。1997年,白斯嘎拉编《degedü mongγol-un teüken surbulji bičig-üd 》(德都蒙古历史文献),汉文名称为《青海蒙古文献集》,是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史料集[3]。2004年,青海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编有论文集《degedü mongγol-un sudulul》(德都蒙古研究),版权页汉文名称为《青海蒙古研究》,收有文学、语言、民俗、宗教、法律及历史研究文章,这是第一次在综合研究领域冠以“德都蒙古”名称的著作[4]。类似的还有西北民族大学所编《西蒙古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中与青海地区蒙古族相关的研究著作。近年来,一些相关汉文学术文章也开始使用“德都蒙古”名称[5]。在行政领域,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属下的党报《柴达木报》蒙文版,于1989-1991年专设《德都蒙古》栏目,1992年又以《德都蒙古与未来》为题,开展有奖征文活动,曾设有《德都蒙古今昔》、《德都蒙古文化》等栏目,对此地方和省级年鉴中亦音译其名称作了介绍。除此之外,直到本世纪初几年,鲜有其他行政机构使用之。2000年以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些部门组织的活动中开始出现音译的“德都蒙古”名称,到了2012年,以“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德都蒙古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实施为象征,海西州政府官方文件正式使用“德都蒙古”名称,于是,这一名称的蒙古文和汉文语音形式最终趋于一致,社会关注度也骤然上升,还有人把“德都”作为商标注了册。2014年,海西州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编撰的《德都蒙古历史文化丛书》[6],是海西地区第一套关乎本地区蒙古族历史文化多领域的汉文丛书,不仅通过国家出版部门的审定,编写者在《前言》中从历史角度阐释了“德都蒙古”的涵义,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定义,其中论及的三阶段分期方法开始被一些部门的相关事务中引用。本文可看做是《前言》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一、 史料记载 关系到“德都蒙古”名称的来源及含义问题,首先可观察到两点。一是使用范围和使用者的广泛性;二是可依据的史料记载和历史渊源。就使用或流行范围而言,今天,青海蒙古族不仅在国内蒙古地区,甚至到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地区时,也常常被年长的人士称作“德都蒙古”人,可见其地域和使用者的广泛性。根据一些游记记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其他地区的蒙古人或者外国的探险家,到青海与蒙古人接触时,称此地蒙古人为“德都蒙古”人,亦显示此称呼流传已久,其起源自然比这更早了。 在文献记载中,能够与“德都蒙古”相联系起来的名称是藏文《新红史》(deb thar dmar po gsar ma)、《汉藏史集》(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v byed chen mo vdzm gling gsal bavi me long zhes bya ba bzhung so)等史书中出现的“stod hor”一词,意为“上部蒙古”,指的是蒙元时期蒙古高原以西的蒙古部落,主要是中亚的伊儿汗国。虽然还没有发现与之对应的蒙古语,但肯定译作“degedü mongγol”(“德都蒙古”),不容置疑。“hor”(霍尔)一词,在印度指游牧部落,后来在藏语中泛指北方民族,蒙元时期主要指蒙古族,后来又以源自称粟特人的“sog”、“sog po”(索布)来专指蒙古族。为什么把西部蒙古称作“上部蒙古”,可能源自蒙古人自己的称呼,此或许与古代蒙古人的方位概念或以西为尊的习俗有关。蒙古语里“西”叫做“baraγun(书面) / baruun(口语)”,与“右”通,“东”叫做“jegün (书面)/ jüün(口语)”,与“左”通。而“右”也叫“jöb”,即“正”或“正方”,又与“上方”通,即“degedü”。因此,西部蒙古时而被称作“德都蒙古”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蒙古包里的布置安排中最为明确,古今都是一致的。今日之“德都蒙古”,在词源上应该与之相关。但如何与青海蒙古相关联的,还需做具体考察。 目前已知的青海蒙古历史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都蒙古高僧松巴·堪布·益希班觉于1786年用藏文编撰的《青海史》(mtsho sngon gyi lo rgyus tshangs glu gsar snyan zhes bya ba bzhugs so)。这是专门写青海及青海地区蒙古族历史的史书,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有一段关于青海地区及相关族群分布和分类的极其重要的记载。曰: de la snying nas dad pa byang stod kyi sog po o rod tsho bzhi dang / bar du bod chen gyi a mdo dpa' ris sogs dang / smad kyi sog po mon gwol phal cher yin… 从内心信奉(宗喀巴)的是:北方上部蒙古的四卫拉特;中部大藏区之安多华日等;下部索布蒙古大部分…[7] 益希班觉的这一分类法,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是“上部”、“中部”、“下部”三种,是一种地理或地域关系的组合。第二层面是“上部蒙古”、“中部大藏区之安多”、“下部蒙古”三种,无疑是基于族群和群体社会关系的组合。综合二者,既是三个区域分别属于三个群体,可谓之“三部”或者“三区”划分法。 三个群体也很具体,分别是“四卫拉特”、“安多华日”和“索布蒙古大部分”。益希班觉称“四卫拉特”属于“上部蒙古”,自然与蒙古语的“degedü mongγol”(德都蒙古)对应;又称“索布蒙古大部分”属于“下部蒙古”,当与蒙古语的“dooradu mongγol”(道日德蒙古)对应,二者之间是“大藏区”之一小部分安多北部地区的藏族部落。益希班觉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上部“德都蒙古”以及与之对称的下部“道日德蒙古”,在文献记载里尚属第一次。 益希班觉所指“德都蒙古”究竟有何含义呢?因他在另一部巨著《如意宝树史》('phags yul rgya nag chen po bod dang sog yul du dam ba'i chos 'byung tshul dpag bsam ljon bzang zhes bya ba bzhugs so)中,对于西藏地区和康区做了传统的区域划分,并分章节作了详细说明[8],所以,此处是完全针对青海蒙藏地区以及其余蒙古区域的。从“上部蒙古的四卫拉特”一句看,益希班觉起初似乎把整个西蒙古卫拉特联盟成员均包括在上部“德都蒙古”范围之内,与蒙元时期的西部蒙古“stod hor”(“上部蒙古”) 类似。但众所周知,后来的“德都蒙古”并没有包括青藏高原以外的卫拉特各部落。这要么益希班觉所指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要么他的“四卫拉特”本来就是对青藏高原的卫拉特蒙古而言的。笔者倾向于后者,因为,17世纪以来,各地卫拉特人习惯性地自称为“四卫拉特”,这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中也有反映。所以,此处的“四卫拉特”,实际只指青藏高原的卫拉特蒙古,并无矛盾之处。也就是说,青藏之外的卫拉特部落并没有包括在“上部蒙古的四卫拉特”当中,这可能与益希班觉提出这概念时候的18世纪准噶尔部落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势有关。由此可知,益希班觉是第一个提出青藏高原蒙古族为“德都蒙古”以及相对应的“道日德蒙古”概念的人,其“三区”划分法,是以青藏高原卫拉特蒙古及其生活区域为顶端的一种分类方式,它既包含地域关系,也包含了族群和群体以及宗教文化关系。 那么,益希班觉的“三区”划分法又源自何处?把地理区域划分为上、中、下的思维方式,蒙藏民族皆有之。在青藏高原,特别是对于所谓“大藏区”,西藏各个时期史书中都有略有差异的“三区”划分法,而上部阿里三围(mnga’ ris skor gsum)、中部卫藏四如(dbus gtsang ru bzhi)、下部朵康六岗(mdo khams sgang drug)之“三区”为传统分区法,是比较固定的。但在其中融入蒙古族政治、文化、宗教元素之后,其特点性质有了较大的差异。考察青藏高原的政治、经济、地理结构关系及演变历史,可发现蒙元时期对青藏高原的“三道”行政区域划分方式具有一定的关联或参照价值。蒙元时期全国实行行省、道、路府等行政区域划分。在西藏及藏区的行政区划中,直接使用意味“路”或“道”的蒙古语“čölge”,藏语音译为“chol kha”,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松( dbus gtsang mnga' ris skor gsum )、朵甘思(mdo khams)、“朵思麻”(mdo smad),分别是上部卫藏阿里三围一区、中部康六岗一区和下部安多一区,共三个区域,藏语称“chol kha gsum”,即“三道”。“三道”划分,既是地理区域分布组合,也是部落群体和文化区域分布组合。经过几次变迁之后,“三道”分别由“乌思藏纳里速古鲁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地方机构来进行管理,属宣政院统辖。益希班觉为一代蒙古族博学大师,除佛学之外,精通诸学,写成佛教通史《如意宝树史》,其中专设蒙元以来佛教史篇章,对于蒙古帝国历史、元朝时期的“三道”行政区域历史自然是有研究的。其将18世纪整个蒙古族区域一分为二,中间加入部分藏区,在形式上与“大藏区”的“三区”划分法和蒙元时期“三道”区域划分法类似(如下表)。但更重要的是,以自身所处的青海地区为中心,以蒙古区域为主体的“三区”组合法,具有很强的蒙古群体意识色彩,而且将蒙古地区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区域相链接,既是清代多元一体政体结构的现实反映,也体现了蒙元时期以来的蒙藏政治、宗教思想意识的紧密联系与历史延续性,又体现了族群群体结构变化后的区域现时新局面。
于是,专指青藏高原蒙古的“上部蒙古”,即“德都蒙古”称呼被各界所接受,并广为流传,成为含义明确的固定名称,而此后蒙藏史书中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用法,都应是益希班觉概念的承袭了。1892年卡尔梅克蒙古人巴嘉氏巡礼青海、西藏后写成《西藏行记》(baγ-a dörbed nutuγ-un baz-a baγsi-yin töbed oron-du yabuγsan teüke)一书称[9]: ede aru mongγol-i doodu mongγol , čayidam-un mongγol-i degedü mongγol gejü nereyiddeg gen-e. (塔尔寺的喇嘛们)称外蒙[等]为“道日都蒙古”,称柴达木蒙古为“德都蒙古”。 ene degedü mongγol gedeg ulus-un γarulγ-a-ni, güüsi nom-un qaγan-u albatu jigi, čuγ qorin dörben qusiγun biden gen-e. čayidam-un γajar-tu bayidaγ-ni wang-un qusiγun, baraγun, jegün, tayijinar, körlüg köked, qaraγčidud, šang-un qusiγun eyimü 8 qusiγun bayidag biden gen-e. bisingki-ni köke naγur-ača abuγad časi gömbüm bolon labrung-un γajar-iyer tangγud dotor-a bayidaγ jigi. 这些德都蒙古人源自固始法王之庶民,自称共二十四旗,柴达木地区有青海王旗、巴隆、宗家、台吉乃尔、柯鲁克、哈拉克沁(盐池)、香旗等八个旗,其余在青海湖岸及以远的塔尔寺、拉卜楞等地方,地处唐古特人中间。 yerü-dü degedü mongγol bolon aru dooradu mongγol qaγad bolon noyad-ud čuγγar ču ejen qaγan-ača jalba abdaγ gen-e. “德都蒙古”和外蒙等“道日都蒙古”都从皇帝那里领取俸禄。 益希班觉记载出现一个世纪后的这一不经意间的记录,仍符合原定义的基本含义。称“德都蒙古”既是“源自固始法王之庶民”的24旗,“道日都蒙古”既是外蒙等其他蒙古地区,与益希班觉所指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德都蒙古”等同于以和硕特为中心的青海卫拉特,包括和硕特、土尔扈特、喀尔喀、绰尔斯、辉特诸部落,这反映了清代青海扎萨克体制中的部落结构关系。若从“固始法王之庶民”这一整体性考虑,实际上是29旗。而且,就卫拉特蒙古部落及固始汗后裔而言,还有分散在西藏、甘肃、四川等地的卫拉特蒙古,亦应包括其中,从而可构成以青海地区为中心的“德都蒙古”历史地理、民族群体文化关系之全景图。 二、历史源流 17世纪,卫拉特蒙古出现在青藏高原,并不是一部分蒙古族群体的孤立行径,它与蒙古族在这地区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蒙古人在青藏高原的历史足迹可追溯至成吉思汗时期。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灭西夏之后青海地区已被纳入蒙古帝国势力范围,1240年阔端派兵入藏,不久在萨迦班智达号召下吐蕃各部归顺蒙古帝国,蒙古军队、游牧部落涌入青藏高原,其中不乏部分蒙古语族群体。1956年青海诺木洪等地出现的干尸,从体质面型以及衣着、马具、弓箭随葬品可看到蒙古武将的整体形象。同时还出土元朝元统、至元、至正纸币等随葬品等,无不显示元朝在青藏高原实施政治、军事、经济统治体制的完备基础。而新近在都兰县出土的特征完全相同的干尸,其随葬品更加丰富,特别是用具上发现记有使用者或者是制造者名字的回鹘蒙古文[10],而且为夫妻合葬,更加证明蒙元时期的青海蒙古人具备坚实的经济技术、文化基础和家庭单元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绝非处于极少数人能够维持的状态下。由早期的游牧社会式分封制到设置“总制院”、“宣政院”、“宣慰司”、“宣慰使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等上下机构的设置,说明在这里的蒙古人统治阶层,社会区域也具多样性。后来在明朝,光是青海西北地区专设边区“四卫”、赤金蒙古卫等来分别管辖,也说明这一点。因其直接管理机构为属宣政院统辖的各路宣慰使司,故可统称“宣慰使司蒙古”,分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中央政府时期,共约120多年。区域范围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等地,元亡后,相当一部分融入当地社会,或者隐姓埋名,或者与其他民族群体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族群,其历史延续至今。如,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一些土司,甘、青地区的土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等族群主流,西藏的霍尔三十九族等,当属这一类型。 明朝在青海西北部设“西宁塞外四卫”等,主要安置蒙古族及属下游牧部众。16世纪初,东蒙古右翼鄂尔多斯等部进入青海并收服“四卫”,后又被土默特俺答汗部统辖。土默特部与西藏反对势力格鲁派结成联盟,强盛时期,势力扩展至今日青海、甘肃边区、西藏东北部,史称“西海蒙古”,直至17世纪30年代被喀尔喀部却图台吉占据,历经130年的历史。 卫拉特,也就是益希班觉所指“德都蒙古”,是最后进入这一地区的蒙古族群体。1637年四卫拉特联盟联合击败喀尔喀部却图台吉后进入青藏高原,与原有的“西海蒙古”遗民一并被并入其统辖,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以四卫拉特右翼自居,并继承蒙元时期忽必烈与萨迦派以及俺答汗与格鲁派的福田施主合作模式统治青藏高原。在完全被纳入清朝统治体系之前,为“青海卫拉特联盟”(青海八台吉)及西藏“和硕特藏王”并存时期。1720年代,纳入清朝政治体系之后被称“青海额鲁特”,除部分分散于西藏、甘肃、四川等地之外,其主体为今日青海蒙古族,已有370多年的历史。 综上所述,蒙古人在青藏高原的历史,截至到近现代约有三个时期,六个阶段。如下表:
三个时期虽说各有各的历史背景、过程和时代特征,但是,相互间存在内在的联系。益希班觉所定义的“德都蒙古”,实际上是前几个阶段的延续,其名称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承性。鉴于这样的内在联系,在编辑《德都蒙古历史文化丛书》时,我们又扩展其意义范畴,重新作了如下定义,即“‘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广义上包括历史上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则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卫拉特蒙古族以及甘肃、西藏等地区的部分蒙古族。” 如果按照历史上积极活动的地理范围而言,“德都蒙古”所涉及的有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今日仍可寻找到不同时期的后代。只有广义的“德都蒙古”,才能够网络这些,才能看到青藏高原蒙古人历史的全貌(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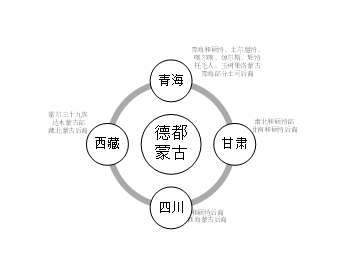 三、 积极意义 如上所述,“德都蒙古”名称的出现并非偶然,具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就从益希班觉的记载算起也已流行了两个多世纪,使用范围也相当广。但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一段时间被忽略了。这与青海蒙古的历史文化本身未受到足够重视或未被广泛关注有关系。如今青海蒙古历史文化得到重视,出现了解其历史,把握其文化特征的实际需要,于是,“德都蒙古”这一名称再次被关注,重新成为一大亮点,这不能不说有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德都蒙古”一名称成为了一种鲜明的符号,为使社会各界和各个领域的人们认识这一群体,发挥着作用。对于它的积极意义,可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探讨。 首先、“德都蒙古”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前面所探讨“德都蒙古”名称的历史背景和含义问题,从中也可体察到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德都蒙古”也和其他蒙古游牧部落一样,在不断地“分散——集中——分散”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是蒙古族游牧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一过程自最早的森林百姓联盟到西部蒙古联盟,再到高原游牧群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大变迁,都是蒙古游牧社会,乃至内陆欧亚游牧社会内在的“平衡”这一基本运行规律机制所导致的。“德都蒙古”名称,正好反映了这一部分蒙古群体在地域和族群结构上的变化及其显著特征。通过它可更好地了解区域和民族、群体间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历史面貌。观察其历史演变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或典型。 其次、有坚实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由于“德都蒙古”之“德都”(degedü),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文化因素,无论是百姓阶层、还是贵族阶层,或是宗教阶层,或是不同区域的群体,人们都可从各自的角度领会或阐释它,使其广泛流传提供了纵横各方面的条件和空间。特别是本土的蒙古族群体,更多因其褒义的含义而欣然接受之,今天已经成为应以为自豪的美誉和符号象征。 其三、具有现实意义。在学术界,无论是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甚至是明清史研究,都不能够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被各方所忽略或边缘化。对于它曾在历史上为多元一体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十分积极的作用,对于青藏高原以格鲁派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的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等等,没有给予充分的研究和评价。甚至青海蒙古族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也未被广泛所宣传和发扬其精神。原因很多,但缺乏一种鲜明的符号特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德都蒙古”一概念或许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的一个切入点和连接线,从而达到促进服务现实和未来发展的目的。 余 论 细细观察今日“德都蒙古”文化,呈现多样性。除了现当代色彩之外,具有鲜明的蒙古传统文化特色。其传统文化中,北方游牧民族特征尤为浓厚。在看似很强烈的藏传佛教信仰现象表层下,却是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文化行为模式和礼仪习俗。其传统格言警句大都以“腾格里”信仰、大地敬畏、祖先崇拜、英雄主义为主题,无疑是内陆欧亚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所决定的原始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如,祭敖包、祭火神等祭诸神仪式是德都蒙古人信仰的基本方式,是北方民族固有信仰的延续。以《汗青格勒》为代表的大量英雄史诗的流传,应该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形成初期,英雄辈出状况的记忆。而部落联合对抗恶势力为体裁的很多史诗,描绘的则是草原游牧部落大联盟时期的宏大历史画面。德都蒙古所流传的《格斯尔》,与藏族、土族、卫拉特、阿勒泰、图瓦、布里亚特《格斯(萨)尔》形成一条清晰的《格斯(萨)尔》文化走廊或南北交流通道,自然形成于南北深度互动时期。《巴音颂》祝颂活动是把历史叙述、祝赞形式和祭拜活动融为一体的仪式形式。从其庄严的氛围以及祭拜成吉思汗这一主题看,很可能源自黄金家族祭拜祖先或宫廷祭祀仪典,其起源可追溯至12-13世纪。对于15世纪以来的卫拉特联盟时期,德都蒙古人更是记忆犹新。和硕特为卫拉特之核心部落,是“四卫拉特汗”之部落,在卫拉特群体中有着较高地位。17世纪中叶,迁居青藏高原后,七十余年主导地方政权,吸收高原诸民族宗教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高原蒙古民族群体,经过清代多元一体的体制及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形成了今日之德都蒙古及其文化体系。 从北亚到中亚,再到青藏高原的漫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变迁过程中,德都蒙古人扮演过信仰“腾格里”的“森林百姓”、崇尚英雄的草原游牧民、诞生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成员、蒙古帝国共同体成员、西蒙古部落联盟成员、封建清王朝的游牧庶民等等不同的社会角色。所属的都是一些重要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区域,这些对于整个内陆欧亚游牧社会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德都蒙古历史文化的原点也在其中。这也是今日之德都蒙古文化以北方游牧民族传统文化为根本,呈现多样性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各个时期,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以及所创造的文化,随着游牧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不停地做出选择,最终以历史时期较长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基础,沉淀或传承下来的既是今日德都蒙古文化的基本元素。为探究构成德都蒙古历史文化体系的多种元素及其根源,可根据其历史源流以及文化类别诸特征,勾勒出历史上相关联的各类文化形态或文化区域关系网(如下图),构建其历史文化完整体系,从而丰富“德都蒙古”名称的内涵,加深人们的认识,使德都蒙古文化在区域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学术领域真正拥有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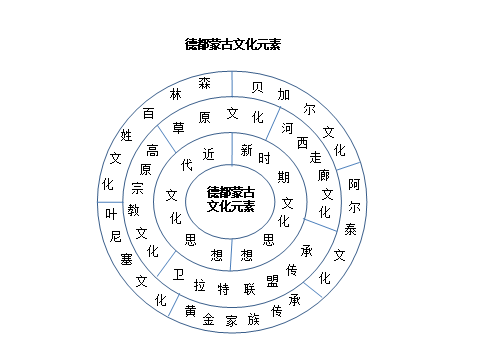 文献参考: [1] 如,齐·布仁巴雅尔等编.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蒙文)[M].非正式出版,1986. [2] 高·策仁多吉.德都蒙古一词之我见[J].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5:6.//德·哈达宝力.德都蒙古一词之由来[J].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5:6. [3] 白斯嘎拉编.青海蒙古文献集(蒙文)[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4] 青海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著.青海蒙古研究(蒙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5] 贾晞儒.“德都”蒙古族文化简述[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7:3. [6] 斯琴夫、青格力、僧格主编.德都蒙古历史文化丛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做修订后2016年第二次印刷。 [7] 松巴·叶西华角著.青海历史(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6. [8] 松巴堪钦著.松巴佛教史(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 [9] Сказание о хождении в Тибетскую страну Мало-Дербетского Бааза-бакши., Калмыцкий текст с переводом и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оставленными А.М. Позднеевым. 1897.由本人注解的回鹘体蒙文版即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关于这一新发现,将另文专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