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翀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商周时期的书艺有着一个从契刻到刻划,再至书写的认识过程,尽管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指龟甲契文、铜器铭文、陶器刻划文字等不是纯粹的书写材料,但无论承认与否,这个认知过程也逐渐慢慢显露出来。特别是陶铜玉器上的朱书或墨书文字开始进入到书法研究者与古文字及古史研究者的视野内,这样的材料应当对大家的认识震动不小。像1987 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一件陶器上,就残存有 6 个朱书文字。文字笔锋挺拔,起笔与收笔处锋芒鲜明。表现出毛笔所特有的弹性,说明商代的毛笔已具有良好的性能。其实,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殷墟所出土的白陶墨书“祀”字上,也呈现出这样的用笔特点。比起殷墟出土的这些商代晚期的文字来,近年出土的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中陶缸上的朱书文字(图1)更引人注目,这是出于时代更早的缘由。尽管我们也认同发掘者所认为的书写工具当属毛笔之类,然从书写的流畅性以及字体的结构来看,只是表现出当时毛笔制作的较为成熟性,若以书法作品而论,似乎还存着一些不足之处。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 稍晚之时,河南洛阳北窑的西周贵族墓地所出土的伯懋父簋(M37:2)上的墨书却是极具水准。(图2)同出铜戈以及铅戈之上也带有墨书,可惜并未公布详细资料和清晰图片,我们也就只能对伯懋父簋上墨书作为重点考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伯懋父簋的时代在西周康王时期,内底存留墨迹,“器内底部原被土锈掩盖,在去锈时发现一侧有墨书铭文‘白懋父’三字。西周早期的墨书,实为珍品”。(图3)发掘者之一的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三字“笔势劲韧遒美,字形整肃均齐,笔画中肥而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白’前缀尖而下部浑圆,中间横笔微带弧曲。‘懋’字笔画起止多显锋露芒。‘父’字左笔露锋向下疾行而又弯钩上收,运笔圆熟自如,末笔藏锋而重捺轻收”,可谓是看出西周书者——姑且将在铜簋上作字之人成为书者,或者是原初书法家——行笔的笔意。因笔者持续关注西周金文的笔顺问题,也就对这件铜器格外有兴趣。至少在单字“父”上能够看出行笔笔顺,首笔必然是竖弯钩(为表述方便,暂且以楷书的笔画名称意代之,以下同),因行笔过程最后略疾速,形成一个比较尖锐的挑勾。这时的笔锋若非中锋才能够落下次笔,于是就须有重重的一顿,以此来纠正笔锋。所以,次笔一定是“父”字右侧的横折。其横折段的起笔处浓浓的首部,可以理解为顿笔之用,收笔也能以回笔藏锋处理之。前后不同的书写处理方法呈现出不一样的样态以及视觉效果,也多少因为用笔材料性质而引起。横折收笔处的笔速显然没有首笔行动得快,所以不甚尖锐;应该是笔锋自然离开书写载体——铜器,形成略略的一个偏锋,所以就圆转回来,为末笔撇竖自然的起笔;也可看做次笔与末笔的承接是形成了形断而意不断的圆弧。从书法操作意义的角度来看,仅有墨书三字的这件铜簋于书法史上的价值能够超过有着长篇铸刻铭文的铜器。对于这个墓群的主人,我们也不妨可以做出一个有趣的猜想,这是爱好习字的一家人,才会在随葬的青铜器上选择书写而非铸刻的“铭”文。器主伯懋父很有可能就是卫康叔之子康伯,为武王的侄子,又曾率领殷八师征东夷,其本人在成周城内周王所居住的地方王城中活动。M37长3.48米、宽2.58米,深4.8米,看起来不是很大,却仍然属于北窑墓地西周早期墓葬群的中型墓,只是可惜墓葬曾被盗扰三次,信息损失严重。但从器主身份与墓葬规格而言,对于认识“伯懋父”墨书多少也有所裨益。纵然器主与墓主并非同一人,但墓主也是具有一定等级的贵族,且与伯懋父簋关系甚深。 伯懋父簋上的墨书仅有三个字,相比大量的长篇铜器铭文来说,在文字学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对于商周书法而言,却是极为珍贵的,因为“所谓墨迹,实际上包括墨书和朱书两种文字遗迹,它们代表了当时书写的原貌,艺术价值不一定很高,但对书法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的意义在于是当时所写,是即时性的,并未有转来转去的失真情况,“当时用笔的痕迹仍历历在目,生机勃勃,它的价值是十分值得尊重的。对于书法研究真迹的确是最好最理想的方法”。因为伯懋父簋墨书的存在,使得进入早期书写史的材料中,不再只有商代甲骨、周代金文那么简单,只是固态化的痕迹,“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商周时期还有另外一种使用毛笔的书法艺术形式”。在先秦书法史上,商代甲骨、周代金文多是一种将“死”的状态,不具备“一次性”书写的性质,存在与当时书法情状走样的程度。如果把“写”问题引入金文、甲骨之中,以此为视角看待这些以往常见的商周“书法”材料,它们却与伯懋父簋墨书有着截然不同的分野。当然在甲文、金文本身的制作(涵盖契刻或铸造)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尽管二者存在着一定的文字发展承续关系,但区别就是区别。金文是属于写划,甚至在见之于钟鼎彝器之上的金文形成之前有一个写的“纸本”,即便是“写”在范模之上的,也存有不少笔意。而甲骨这是刻写,属于先于写之前的契刻,或者在写刻之间偏重于刻。故此,从书法艺术上讲,甲骨契文更偏流于印石篆刻之间。日人藤枝晃曾议论道,“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多采用流利线条的铭文,与几乎是由坚硬的直线构成的甲骨文竟然出现在同一时代。这主要取决于所用材料的迥然不同。甲骨文必须刻写在平滑的龟甲和兽骨上,而且空间非常狭小。其内容往往是只供皇帝和贞人看的,不能让其他人随意看到,因此需要尽量省略字形。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即便是由于某种过失,让别人偷看到了也无法知道其含义。这一点与符牒相类似。与此相反,铭文则必须统传万世,让子子孙孙阅读并引以为尊。甚至可以说,与实际使用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多呈屈曲状,以便产生装饰性效果。铜器铸造出来之后,铭文便出现在坚硬的铜器上,决不会是铸造出来之后才镌刻上去的,制成铸范后再镌刻,在技术上也无法达到要求。因此铸造之前,文字的原型早已被镌刻在铸范的毛坯上了。因为是用柔软的粘土来制造范型,用一把竹刀就可以轻易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两种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的殷代文字”。 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en)虽然没有对“甲骨文书法”有过专门的研究,但她对此研究有着较大的贡献,对甲骨文没有一定笔顺情况的问题有所发现,但她则将其归结为刻手缺乏文化之故而没有按照惯有的笔顺。(图4)这是个文化误解,主要是因为艾兰不熟悉中国书法艺术所造成的。用笔的次序,主要是因为载体本身及书写工具的特性所致,以及特有的生理限制因素,例如人的手腕不肯能全角度的旋转。契刻而生成的甲骨文,必然在用玉刀或是铜刀上刻制,多少不依照毛颖之笔的书写规律。所以,甲骨上的契刻所形成的笔画痕迹,也就是世所称的“甲骨文”是不能够称之为“书法”的。当然,甲骨文是有一定的书法意蕴的。但是,具备书法意蕴与真正的书法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人藤枝晃说,“铜器铸造出来之后,铭文便出现在坚硬的铜器上,决不会是铸造出来之后才镌刻上去的,制成铸范后再镌刻,在技术上也无法达到要求。因此铸造之前,文字的原型早已被镌刻在铸范的毛坯上了。因为是用柔软的粘土来制造范型,用一把竹刀就可以轻易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两种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的殷代文字”,就是看到了这样大差距。铜器上的铭文与龟甲上的契文之间的差距是内在的,是巨大的;于书学较为陌生的古文字学者对此多会有所忽略。 在契刻以前,甲骨文究竟是否先用毛笔书写做以底本?这个问题迄今尚无一致的意见。董作宾认为是先写后刻;陈梦家认为是直接契刻上去的;陈炜湛、唐钰明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一般是大字先写后刻,小字直接刻写。但是,无论怎样,甲骨文多以契文称之,可见用刀契刻是制作的主要方法,虽然在安阳殷墟也见有朱书的卜骨(图5),但出土量绝少,且写完亦未曾加以刀刻,出现这种情况用“刻手漏刻”的说法解释恐怕不够圆转。而认为有多种笔法存在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殷商朱书墨书存在着‘丰中锐末’式、‘藏头护尾’的‘玉柱篆’式和‘头粗尾细’的‘蝌蚪文’式三种笔法。以第一种最为原始,技巧含量最少,西周初年以后使用日渐减少,后基本上被人们所抛弃。当代有些学习甲骨文书法的人还在刻意地追求这种笔法,说明他们对书法的认识能力还需要提高”。其次,甲骨文与金文是有截然地分别,“由于甲骨文最终形态绝大多数是契刻而成的,且契刻时往往先直划后横划,因此甲骨文的许多象形线条出现了平直化和拆断的现象,使原字的象形意味受到影响。金文则不同,通常是在铸器以前先用毛笔写出墨书原本,然后按照墨书原本刻出铭文模型,再翻出铭范,最后往范中浇注锡铜溶液,铜器与铭文便同时铸成。因此,铭文能够比较好地传达出墨本的形态和韵致”。容庚先生亦有论,“铭文间有方格,殆为书写之便。如师趛鼎,克鼎、廣簋、番匊生壶,大鬲皆有阳文方格。然铭文往往跨于方格上。大克鼎前半有格而后半无之,颂壶器有格而盖无之。 西周铭文器物的数量大增且长多是因为铸铭方法的改进,“铸铭方法的不断改进致使西周铭文字数得到迅速增加。铸造铭文时,有采用‘直接在范上刻铭’的方法,成的铭文即为阳文。有的则采用在‘铭文范模上刻正阴文,翻出反阳文范,嵌于范中,铸出正阴文 ’的方法铸铭。这两种方法都有许多缺陷。而后发明的在‘范上按字或按行贴泥片,刻成反阳文,铸成正阴文 ’的方法,铸铭时可‘不限铭文字数’也‘不需预制铭文范模’,这种铸铭的方法是西周青铜私文书字数增多的主要原因”。罗森考察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墓出土铜器后,认为“器型、纹饰和铭文都完全符合周中心区的样式。当时东南地区的人们不太可能熟练书写适合青铜铭文的字体。该器的铭文似乎表明,这件青铜器是在周中心地区铸造的,或者,如果它是在东南地区制造的话,应是由周中心地区迁移到那里的工匠所铸造的”。这一说法有颇为可采的地方,在我们看来,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商周书写的权力性,反过来说,这种书写权力又使得铜器铭文的书法性十分微弱。伯懋父就有征东夷及北征的战绩的,其人亦多在成周城内的周王所居的王城活动。簋上墨书是否伯懋父亲自提笔而书不得而知,但即便是笔工书写,也是受到了伯懋父或是其子孙的授意的;再退一步讲,当时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员多是具有等级身份的,据三字墨书的痕迹状态而言,并不存在不识字的工匠誊写现成的粉本可能。 从更为丰富与广阔的铜器铸刻铭文而言,尽管铜器铭文这种“书法性”很微弱,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书艺”的存在,这一点与文明初期的刻划文字完全不同。也正是存在着这种书艺,使得伯懋父簋墨书的出现并非偶然,呈现出大量书写操作的实践现象。只是类似的作品多不存在,就显得伯懋父墨书看起来横空出世一般,但如同出的戈上墨书例子一样,其并不指向于“绝少”的现象、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种例子较少,却能看出其书写氛围的浓厚。甲金文字多少与后世的书法有着相通之处,比如避复,即重出字形的避复这种“书法”现象的出现。徐宝贵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其认为,“古代铭刻的形式之美属于书法艺术的范畴,它不仅有其独特的审美要求,而且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在同时同地所铸所刻的同一篇铭文中,一些重复出现的字就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种变化称作‘重出字的变形避复’。这种‘变形避复’不是铸铭者随意所为,而是为了追求一种审美要求所做的艺术加工。事实上,古人的这种审美情趣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代”。与后世书法作品不同的是,商周文字本身就处于文字发展的初期,且字学与书学尚未分流,故此“避复”的具体方法更多,也更复杂,可以通过偏旁移位、增删,乃至偏旁替换等手法来起到避复的作用。对于第三种做法,更是需要古文字学的支持,如人女互训这样的例子,就是人字旁与女字旁可以互相借代的。这种避复的运用,一则是因为所处时代偏早,字体演进与书写变化合流而致,另外也是因为商周时期所谓铭刻是处于预制模件块范铸成的大背景之下,用正书反书作为避复手法即是明证。这在后世的纸墨书写时代是所不可想象的,也很难付诸实现。受后者的影响,在避复之时,金文整体字体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至少是在以笔顺为代表的书写过程,因为无论如何,在制作的实际程序中,这些并没有完全被视之为“书法作品”,而是模件制作。也正是由此,古文字家基于本身行业的眼光,做过如下判断,“铜器铭文的书写者,为了避免重复出现的文字形体上的重复,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甚至采取破坏文字形体的完整性,使文字形体出现讹变。过去研究古文字的学者认为这种形体讹误的字是由于书写者一时疏忽和范坏所造成的,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这里所谈的对文字形体完整性的破坏是以避复求变的审美要求为理据的”。说到底,铜器铭文是模件制作与书法意味的综合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抵触。 所谓毛笔之于书法,是工具之于作品的范畴,但二者最初的关系并未如有人强调的那样广而化之,“毛笔的材质、工艺、形制及其使用方法,处处蕴含并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这样的说法总不免过于空泛,但却是因为是这样的软性毫颖,故能够存在一定储墨量,在一次蘸墨过程中的墨色变化,以及顺锋逆锋以及铰毫所引起的下墨顺畅与否则是中国书法的神秘之处,以能由此而产生图像化的意味。这种图像化意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了,然而较之隶变之后时期,先秦书艺还存在一个书体与字体相互混杂相互影响的情况,这对于字体的变化甚至是相当敏感的,“器形、纹饰、字体三者之中,对时代变化反映最敏感的是字体,其次是纹饰,器形又次之。因此,我们确实有时可以发现某一件铜器的器形与花纹具有较早特征,其铭文字体则较晚,而相反的情况从来未见”,这种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书写的考察。 商周时期,因为考古材料的丰富和突出,而艺术史或是图像文化史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亟待加强。如商周时期的甲金文字是中国书法的渊薮,现今书法是中国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任何涉及中国书法史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上追到商代甲骨文、西周的铜器铭文。可是,这时候的甲金文字与后世“书法”或是书写究竟是何关系,再如这样的文字痕迹可否构成关于文字的图像文化场景。这些问题无论是考古学、古文字学、甚至是书法史都不曾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再退一步说,这时的中国并未出现独立的书法家,商代甲骨刻手固然书艺超群,但史不传名。回望西周的书法,也是在制作于钟鼎彝器之上的铭文,并看不到商周时期的某位书法家慨然自由的书写,如果这时真有这样自由的书法家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所谓的先秦书法艺术将会是一个“无艺术家”时代,这比所谓假托史籀、李斯之名的时期还要耐人寻味和错综复杂。在“前艺术家”的先秦书法史中,之前所提到的考古学、古文字学甚或书学都很难全面地予以阐述,如借助图像学的相关方法加以解说也许能会析缕内中奥妙。毕竟这时的甲金文字,不会强于在简牍毫素等材料上的“一次性”书写完成,反而是具有很大的制作意味;更何况还有相当多的图像文字,考古文字界亦将其称之为族徽文字。由此可见,铜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图像的意味,如族徽文字,以及极度象形的文字。这点固然不能够成为图像文化发达,蔓延至文字之上的证据,因为中国文字有着特殊性,即它本身的自有的构件,如刘敦愿先生所言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铭文资料特别丰富,文字未曾实现拼音化,结构相当特殊,书法又成为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丛文俊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论析》引入更重要的一个概念,“篆引”。并在其后所著的《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系统化,“我们合篆、引二字,以‘篆引’为专用名词,用来衡量古文字象形符号系统之内各种书体的式样特征、风格美感、彼此间的关联及发展变化等。其中篆代表大小篆书体线条的等粗、排列组合中德等距等曲长、式样的转曲摆动之类似图案花纹的特征,引代表书写的转引笔法”。丛文俊提出的“篆引”概念相当重要,他使得先秦书法讨论摆脱了只在青铜器铭文遗存上的研究,更加深入到背后的书写活动,“大篆书体是汉字脱略古形之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规范式样,也是‘篆引’的前期形态,它的形成,在商末周初的金文书法中即已露出端倪”。然而,遗憾的是在凹陷铜器的铭文中,这种特点比较微弱,只能依靠书法家的经验感觉。更为遗憾的是,这样的经验之论中的正确性多少被人忽略。而伯懋父簋墨书所显示的证据却是显见的,可以更被较为容易地观察到。 依据篆引的概念再来看待伯懋父簋墨书。它毫无疑问是一幅杰出的作品,尽管只有三字,但竟然有种晋唐帖札的意味。藤枝晃曾议论道,“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多采用流利线条的铭文,与几乎是由坚硬的直线构成的甲骨文竟然出现在同一时代。这主要取决于所用材料的迥然不同。甲骨文必须刻写在平滑的龟甲和兽骨上,而且空间非常狭小。其内容往往是只供皇帝和贞人看的,不能让其他人随意看到,因此需要尽量省略字形。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即便是由于某种过失,让别人偷看到了也无法知道其含义。这一点与符牒相类似。与此相反,铭文则必须统传万世,让子子孙孙阅读并引以为尊。甚至可以说,与实际使用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多呈屈曲状,以便产生装饰性效果。铜器铸造出来之后,铭文便出现在坚硬的铜器上,决不会是铸造出来之后才镌刻上去的,制成铸范后再镌刻,在技术上也无法达到要求。因此铸造之前,文字的原型早已被镌刻在铸范的毛坯上了。因为是用柔软的粘土来制造范型,用一把竹刀就可以轻易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两种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的殷代文字”。说到这里,应须先行做一个概念上的辨析,什么是书体,什么书法。秋子说,“文字是记录语言,传载信息的符号但又具有艺术性质的本艺术形态。书法则是书法情意、旨在审美的创造的复艺术形态。书法的形态规定是书体,文字的形态规定是字体。书体是站在书法学的角度,主要以风格形态为标准;字体则是站在文字学的角度,以体制形态为依归”。所以,秋子将甲骨卜书定为独立的书法体系,“甲骨卜书不能视之篆系书法(文字)。它已从本质特征上构成一个自立的书法体系和文字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论断极具启发,但还不够大胆,应该再进一步剥离之,应将甲骨契刻的文字排除书法的书写系统之外,当然这些契刻文字具备一定的书法意味,甲骨文也是书法的必要给养,是必须注意的字体之一。但是,要将其称之为“甲骨文书法”是否合适,则需要做一讨论。甲骨契文的这一书写的天然弱性是因其材质所致,有学者更为细致地分析道,“甲骨文的特殊性,就给甲骨文书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渠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然而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能否进入书法系统,成为成熟的书写确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严格地说,甲骨刻辞只是商周时期的一种特殊的俗体文字,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字体,刻字的人为了提高刻字速度,创造和使用了一批简体字,调整了某些文字的形体结构,改变了毛笔字的笔法,并将笔画中的曲笔改变为直笔,从而造就了甲骨刻辞独有的特点……龟甲兽骨比较坚硬且有纵横纹理,这就要求契刻的文字字体必须相对简易,笔画宜用直线而不宜用曲线,毛笔书写容易而契刻较之困难些,因而部分笔法不得不作改变。刻写载体的限制,使得用刀契刻的甲骨文字体与当时用笔书写的通行文字有明显的差异”。 那么,殷商时期有没有书法。答案是肯定的。启功先生说,“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就已有朱、墨写的字,殷代既已有文字、保存下来,并不奇怪,可惊的是那些字的笔画圆润而有弹性,墨痕因之也有轻重,分明必须是一种精制的毛笔才能写出的。笔画力量的控制,结构疏密的安排,都显示出写者具有精湛的锻炼和丰富的经验”。启功先生的这几句话既肯定了殷代有书法论,也向我们善意的提醒,什么才是殷代的书法“作品”。如果狭义以笔法论之,甲骨契刻肯定不是。因为那是刻法,而非笔法。如一些学者说“就我个人看来,甲骨文创作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书家有‘法’不依,或懒得依。甲骨文书法创作还是有‘法’可依的,顾名思义,甲骨文书法是以甲骨文字为表现对象的,因而正确写出甲骨文字,应就是甲骨文书法的基本大法”。这就是将书法的笔法和用字的法则混为一潭。那什么是笔法呢,孙晓云这样探索过,“以右手‘经典’执笔法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令笔画纵横自如的方法,既是‘笔法’。运用这种笔法,即是‘用笔’。严格地说,用笔法写成的字才是‘书法’。难怪起初怎么会叫‘法书’呢”。这下就明白了,甲骨契刻文是没有笔法的;又因没有笔法,那么所谓的“甲骨文书法”就成为一个不太成立的伪命题。事实上,甲骨文字是迟在1899年才被世人所知,而在甲骨文字缺席于书学达千年之久,却并未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缺少甲骨文字的前提下,中国书法已然发展的甚为完备。陈彬龢在讨论早期书法与文字中也是将其排除在外的,“凡古代文字之刻诸石或勒于金者,各有特殊之格,此属自然之结果。甲骨文字、瓦当文字、木刻文字亦有其特种之姿致也”。我们对他“格”与“姿致”两词的使用应该予以重视。更何况若使用笔法,则一定出现笔顺。因为书法之所以称之为书法的一个前提就在于软性毫颖,也是因毫颖的缘故才会用中锋侧锋的变化,笔顺在这种意义上调整笔锋要比笔画间架结构重要得多,但是甲骨是没有笔顺的。艾兰的发现,是难得的窥视,但是囿于东西方文化的误解,使她并不能再进一步发展。我们对于甲骨的书法判定可能过于严格,但对于整个书法史研究来说,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至于说罗振玉、董作宾诸老使用甲骨文字进行书写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甲骨学者的学外遣兴之作,实际上他们在这样书写之前是受到了以“永”字八法为系统的书学熏习甚深,退一步讲是书法技艺与甲骨学识的结合,“雪堂先生有高深的文学素养,并熟悉甲骨文字,这二者的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利用有限的千余甲骨文字辑成众多条楹联,使甲骨文字的研究由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的领域,延伸到书法艺术的领域”;但绝对谈不上到了“能于清润朗健的意态中写出金石气来……通过宣纸效应的书法来成为抒写性情及美感韵味的艺术珍品”,而是本身先行具备书法造诣,对甲骨文字书写的应用,“清末的金石学家大多在书法上有很深的造诣,所以甲骨文字出土后,很快就被应用到书法创作中”。而柳学智先生所提出的“甲骨学书法”,其表述概念最初就将填朱或填墨与甲骨墨书、书写与契刻等不同层面的名词混淆起来。靳永认为要成功地对甲骨文书法进行“还原”和“改造”,在用笔、结字、章法三个方面都要进行探索。请注意这里是甲骨文书法,细读靳文,实际上以使用原有的“八法”系统书法技术对新文字材料的再创造。我们不应该因为提倡上古文字学的重要性而妨害书学的发展。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再次重申,甲骨文肯定具有一定的书法意蕴的,但有书法意蕴和是否是书法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与治印有些近似。如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言,“商代甲骨卜辞一般有卜人具名,可以说这批卜人便是最早的篆刻家。但不是印章,不算数”。再退一步讲,书于龟甲卜骨的七十四例可以被纳入“书法”视野之内,但相较于庞大的契刻之文却是极为少数的。 反观青铜器上的金文,却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书意。这并不是厚金薄甲,而是跟金文的制作工艺有关,“金文的创作是先把文字书写在软胚上制作模具,然后用烧熔的铜液浇铸。在金文刻范和铸造的过程中,对原来书写的笔画虽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出书写的笔意”。我们进一步再观察金文的具体书写可以看到,“在楷书的规范点画尚未形成之前,‘捺’亦做‘波挑’。有关于‘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周代青铜的铭文,类似‘捺’的笔划比比皆是,这无疑是毛笔书写留下的痕迹;其余笔划经过雕刻、烧铸,已完全失去笔触。可见‘捺’的特征是太突出了,几经折腾还保留着。”更绕意味的是,这样在泥版上而书与后世简帛时代的握卷而书,在姿势上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一致。这并非是厚此薄彼,厚今薄古;而是金文、甲骨文字制作所使用的书写工具使然,使得铜器铭文上最大可能的保留的书法特性,“西周青铜器铭文,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墨书底稿的笔画起止提按等运笔形态,也保留了原墨书底稿字形的间架结构,也就是说,西周青铜器铭文文字字形,其书法特征亦达到了与原墨书底本形神肖似的地步”,“金文因为浇铸的需要,需用毛笔先行书写, 制为模范, 再行铸造,故青铜器也是一 种变相的毛笔书写材料”。这其中又因西周铜器铭文字数开始增多,被关注度也就随之提高,以至于本来甲金文字应属于交错时间存在,甚至是共时性发展的状态,在书法史上却形成了商甲周金这样带有线性发展的粗大线条式的印象。 研究商周书法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个危险,即研究对象于制作前后多少会沦于程序化、文书化,削弱书法作品的意境。这一点又与后代写经抄书及刻帖的活动近似。当具备“笔法”的书写进入文书领域,不可或缺都会经历这种考验。“赵体(笔者按:即赵孟頫书法)像颜体和欧体那样,自十四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版刻所采用的主要书体之一。一旦成为印刷体,就不可避免程序化……”。这一危险,中国的学者或多或少都被强大的史学及文本世界影响着,反倒是外国学者看得真切一些,尽管在某些立论上在史学坐标不那么确严。像安阳玉器朱书的材料,学界早有公布,但只限于释字的工作,而放弃了最为本位最应该考究的书写观察。纵然如此,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认识上的一个危险,即认为西周时期的“书法”仅仅是金文——这里指青铜器的铭刻文字——一种形式。造成这样危险思维的原因可能很多,如金文出土较多、很早就予以著录、软性书写载体的不存等因素。但必须指出的是,西周的人们应该是有类似纸笔性质的书艺,书于铜器或泥范只不过是其转变形式,如茹家庄 毛笔,当然是中国书法中最主要的工具。书法家沈尹默曾讨论过,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皆源于是软毫的笔。“虽然还没有发现属殷商时代的像埃及芦苇笔之类的物品,但在卜辞中出现的‘聿’字,在古铜器文中出现的手中把笔的形象文字,可以了解此时已有笔存在,其笔形状也与今日的相似。制造笔的原料,也可从卜辞中的‘聿’(很明白下脚是篆字毛的倒文)字发现,可以想象是用毛作笔,足以知道殷代就有了毛笔。铜器款识文鲜明的笔迹,亦能作为毛笔存在的证明。如说秦之蒙恬初造毛笔,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始用兔毛。秦以前的石鼓文字,也可明显地辨认出使用毛笔的痕迹。另外,周之毛公鼎、散氏盘,用毛笔的痕迹也很清楚”。但讨论还不够,略显空泛;而通过考古工作则幸运地发现战国时期的毛笔实物,曾先后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湖南省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十五号楚墓、湖北省荆门县包山二号楚墓所见到了三例先秦毛笔实例。特别是信阳一号楚墓,时代属于战国早期,更为惊奇的是以一件书写工具箱的形态出土,“箱内装有12件修治竹简的工具,有铜锯、锛、削、夹刻刀、刻刀、锥和毛笔等”。这件信阳一号墓的毛笔,长为23.4、笔杆径0.9厘米、笔锋长2.5厘米,可见已然是讲究笔锋使用,特别是笔杆直径与长度之间比率可以更为自然地捻动于拇指内侧。这可堪是毛笔字(Brush Calligraphy)称之为书法的堂奥。虽然“笔毫系用绳捆缚在杆上,笔头仍套在竹管内”看似平淡无奇,但同出削却是鎏金之作,纹饰华丽,而书写工具箱在这时即可看做是书写系统的物质表现,是知此时的书写系统已经异常的发达及完备。这离我们所讨论商周书法尽管还有一段时间距离,但据王学雷对古笔的整理,发现晋唐之前的毛笔发展的时代革新并不剧烈,只是存在制作品种与书写要求上的区分。尤其是汉代能够替换笔头的束帛笔,更能看出汉代人对软性毫颖的追求,那么更早的商周人们就不追求这样了么?于是,高蒙河带有推测性质的观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即使在用刀契刻的甲骨上,也有一些卜辞文字明显是用毛笔书写的……这些甲骨上的书写文字,风格与契刻的甲骨文不同。一般是字大、笔肥,与金文的风格接近,多书于甲骨的反面。看来,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商周时期还有另外一种使用毛笔的书法艺术形式。……最初的毛笔很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日常使用的书写绘画工具。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早在史前或至少到了商周时代,就已使用了用天然兽毛制作的毛笔”。所以,将我们所能见到龟甲兽骨上的契文直接称之为“书法”是不合适的,“甲骨文的两头尖的单线,完全是由于刻划而成,根本就不是当时书写的本来面目”。换言之,利用甲骨契文推想当时的书写本来面貌显然要比伯懋父簋上的墨书困难得多。 无论是甲金石刻,还是纸上的翰墨风流,都似乎在传达着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有时间性的,痕迹是能够传之后世,但当时书写过程却是一种即时性。“在陶土上刻写,中国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为期至早;牛骨、龟甲、象牙、青铜及竹之用于铭刻和书写则可上溯至商代;以石、玉、丝帛及某种金属作为书写材料源于周代初期;书写于木简则始于汉代。某些坚硬耐久、不易磨蚀的材料,主要用于永久性的记录与纪念庆典的铭文,易于湮失蚀灭的材料如竹、木、丝帛之类则广泛用来抄写书籍、文件及其他日用文字。前一类材料用于延续许多代的纵向信息传递,后一类型的材料则主要供同时代人之间进行横向信息交流”。之前我们过于看重这些材料的物质性,而忽略了其本身也带有时效性,毕竟书写是有一项行为过程。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因为伯懋父簋墨书的出现,使我们更有可能将金文纳入书法范畴内进行考察,从这简略的三字中,多少可以推想当时书写工具、载体以及背后的姿势与运笔笔法,毕竟“古代铭刻的形式之美属于书法艺术的范畴,它不仅有其独特的审美要求,而且表现得相当突出”。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大胆的设想过这个墓群的主人是爱好习字的一家人。当然我们这一不成熟的商周书法探研工作,也只是一个开端,也多属于蠡测的范畴,我们也尽力解决书法的起源之探,文字的起源与书法的起源并不是一回事,也需要把甲金文中非书法的因素剥离出来。这可谓是铜器石刻铭文为载体的大小篆的书写的首要问题,因为上古书法音信微茫,甚至有人直言“玉筋真文久不兴,李斯传到李阳冰”,可见要探索商周书法着实困难,需要对考古材料与书法认识的双重剖析。而中国书法的最为精妙的就在于它的笔法,“笔法是构成书法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笔法控制线条质感的作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它对于书法艺术从来不曾失去应有的意义”。笔法是对运笔动作的控制,节制着笔管行进与滞留,所以才能产生高质量的线条。在甲骨材料的线条中我们看到的是熟练,但看不到节制。因此,我们不同意将所有能够见到的商周文字书写材料都统称为“书法”,甲骨文字只能是广义上有助于书法的材料,并不是书法;而经过书法训练的人士选取甲骨文字进行书写则是另外的情形;青铜器铭文因为制作的关系,书意渐浓,但是否是纯粹意义的书法作品则另当别论,具体而判。 (已发表在《形象史学研究》2015上半年,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插图说明: 图1-1 河南郑州小双桥出土的朱书陶文(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页。) 图1-2 河南郑州小双桥出土的朱书陶文(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页。) 图2-1 河南洛阳北窑出土伯懋父铜簋(M37:2)(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二五,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图2-2 河南洛阳北窑出土伯懋父铜簋外底上的墨书痕迹(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二五,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图3-1 伯懋父铜簋上的墨书(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二五,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图3-2 伯懋父簋墨书摹本(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二五,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图4 甲骨刻辞显微照片,略见刻手用刀痕迹(采自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编着《英国所藏甲骨集》图版Ⅸ,中华书局,1982年。) 图5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带有朱书的卜龟(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一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图6 散车父壶(采自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2》,巴蜀书社,2005年,第192页。) 图7 散车父壶铭文照片与拓片(采自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2》,巴蜀书社,2005年,第194页。)    图1-1 图1-2 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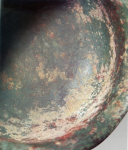    图2-2 图3-1 图3-2 图4    图5 图6 图7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