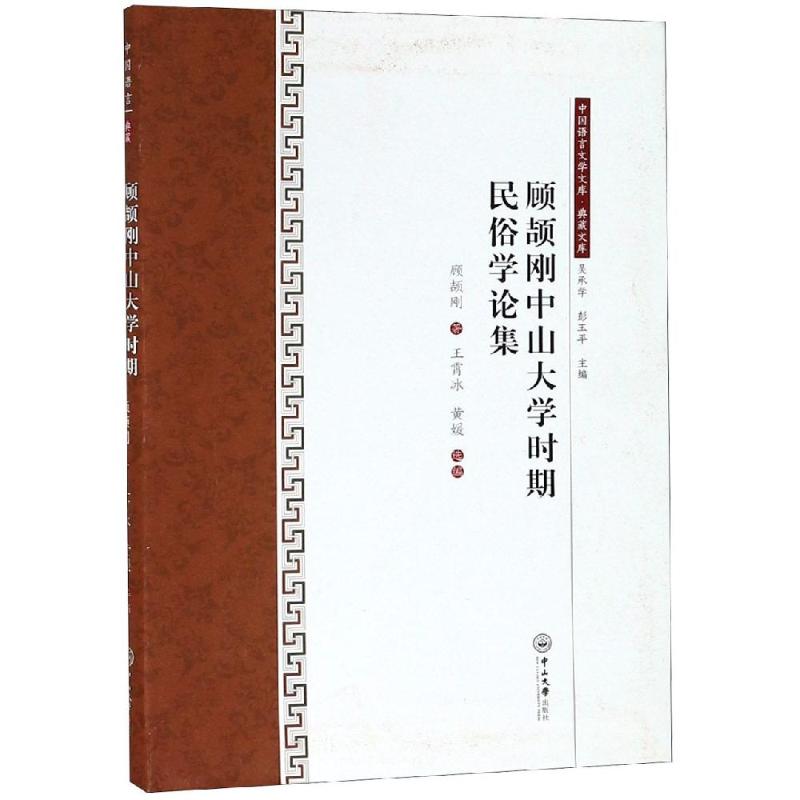 《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论集》 顾颉刚著,王霄冰、黄媛选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一 2011年初,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八集六十二册。此前,顾先生的女儿顾潮老师分别找了一批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帮助校对书稿。我接到的校样是已经四校之后的《读书笔记》,到我这是第五校。虽然发现错误的概率非常低,但我还是逐字逐字地进行指读。看了十几页还没发现一处错误,心里就有点沮丧,生怕自己成了无用之人。每发现一个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的字词,我总是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为顾先生做了点工作。 后来从顾潮老师处得知,被她选为“全集”校对员的三位民俗学者,分别是陈泳超、刘宗迪和我。这让我很惊讶,这三个家伙恰恰是民俗学界最狂狷的三个“革命党人”。我才疏学浅,干点粗活累活是情理之中的,陈泳超和刘宗迪那时虽然都还不是什么博导或齐鲁学者,却早已粪土当年万户侯,尤其刘宗迪,那可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鼻孔朝天的主,他们居然也欣然接受了这单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活,多少让我感到些意外。 某次酒桌上,大家说起这事,也忘了是谁最先感叹说:“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只有顾颉刚的书稿,能同时让你们三个人心甘情愿地俯首甘当校对了。”印象中酒桌上还有几位兄弟,语调一致地对我们仨接受了这么一项光荣而艰巨的“苦差”表现出真诚的艳羡,来自海峡对岸的钟宗宪教授喝多了,不断拍着胸脯要求我们向顾潮老师转达他的心意,如果还有没校完的稿子,他非常愿意躬与其盛。 我们都听说过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而我更愿意把顾先生摆在“真理”和“我师”的中间。我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即使是直接的师徒之间,也不必然存在所谓的学术传统。相比之下,许多并非同一单位的学者,因为相近的学术旨趣或思维方式,反而会选择相近的研究范式。一批散布于不同学术机构的,与顾颉刚扯不上任何师承关系的青年学者,反而是顾颉刚民俗学范式最忠实的拥戴者。” 我们没能赶上顾先生的时代,甚至没能一睹顾先生的天人风采,但是,我们都借助一本《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踏上了敲开顾学大门的台阶。我认真研究了王学典老师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曾暗自庆幸,没赶上顾先生的时代,对我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顾先生是个极爱才的人,但是,大凡爱才之人,必有责人之心。1928年,《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由中山大学出版部印出之后,顾先生在书中发现许多校对错误,就曾非常生气地在日记中写道:“《孟姜女研究集》,夏君所校,误字百出。彼乃真无一技之长,无法用之矣。”看了这些责备的文字,我总是杞人忧天地担心自己也像“夏君”一样,被顾先生划入“无法用之”的行列,从而被拒千里之外。 顾先生百年之后,借助其皇皇巨著,我们就成了顾先生无法拒绝的私淑弟子。陈泳超刘宗迪也许未曾有过我的担忧,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曾自诩为顾先生的私淑弟子。用一句时髦的网络语说,我们都是顾先生的“铁杆粉丝”。我们读着顾先生的书,领会着他的思想,琢磨着他的思路,穿越时空向他求教,与他对话,甚至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我的顾学论文《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02期)诚惶诚恐地写了三年,用它参加过三次学术会议,每次都有近半篇幅的大改,这才敢拿出来发表。可惜的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都不可能得到顾先生的一丁点回应。其实我的内心是多么希望顾先生能够看到我的质疑论文,从而赐下一两招乾坤手,说不定我就能“一招鲜,吃遍天”了。 二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主要创始人,“古史辨派”的代表与旗帜,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古史研究、古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的杰出贡献。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的历史观念;他的充满个性色彩的民俗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一种典范,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在本民族民俗学理论的独创性上,顾颉刚的文章是压卷的,他研究孟姜女传说,也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但在民俗学上,他是走自己的路的。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民族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同样能够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 关于顾颉刚,其实不需要太多介绍,稍微了解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读书人,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管是赞成他、质疑他,还是反对他,只要你的阅读或研究涉及到“史”的建构,无论是民俗史、学术史、还是观念史、故事史,顾颉刚就是一座绕不开的学术高峰。这里只是简单说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时期的一点工作。 因为受到傅斯年的邀请,顾颉刚于1927年4月来到中山大学。顾颉刚到广州时,只有三个月就放暑假了,加之中山大学亟需扩充图书和设备,因此,顾颉刚受朱家骅、傅斯年之托,于5月17日乘船离粤,到沪杭一带购买图书。这一去就是五个月,总共购书约十二万册,其中民间文艺约五百种、民众迷信约四百种、地方志约六百种、碑帖约三万张(这些碑帖现已成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后来装成120余板箱,放置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购书期间,顾颉刚一直与容肇祖、钟敬文等学术同道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积极筹备在中山大学恢复北京大学时期的“歌谣研究会”。 顾颉刚于10月13日回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并协助傅斯年筹备和主持着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各项学术活动,成为著名的“语史所”实际负责人。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虽未成立,而已有房子、书籍、职员、出版物,同已经成立一样,这一方面孟真(傅斯年)全不负责,以致我又有实无名地当了研究所主任。” 关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要将它办成“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二,继续北大未竟的事业,在南方形成一个文科研究中心。而对于该所旗下将要设立的各学术团体,开始并无定名。 在民俗学的建设方面,顾颉刚也有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他刚到中山大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在中山大学恢复北大时期的“歌谣会”,后来考虑到“歌谣”的范围太窄,就扩大为“民间文艺”,并于1927年11月1日正式出版《民间文艺》周刊。但即使在该刊出版之后,顾颉刚的工作计划也还处于变动之中。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民俗学会”一词最早的正式出现是在第2期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年11月8日),其中有《民俗学会刊行丛书》的消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在外国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可是这门学问,在我国尚没有很多人注意到。现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诸人,因组织民俗学会,专从事于民俗学材料之搜集与探讨。该会为求达到广大搜求与研究的功效,极望国内外的同志,加入该会合作。”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没有确定时间。第一本打着“民俗学会”旗帜正式出版的书刊是由杨成志、钟敬文编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该书1928年3月3日出版,扉页和出版页上都明确标署了“民俗学会小丛书”,书前有顾颉刚的《<民俗学会小丛书>弁言》以及钟敬文的《付印题记》。 真正让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名扬天下的,是《民俗》周刊。钟敬文先生说:“《民俗》周刊,是中大民俗学会活动中的主要定期出版物,它与30多种民俗丛书构成这个学会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整个学会具有比较显著的成绩的一部分。不管从它本身看,或从它对当时学界的影响看,都可以这样说。” 顾颉刚还是较早在中山大学开设民俗学课程的教授,1927年10月22日的中山大学国文史学两系会议中,议定顾颉刚担任5科导课任务,其中就有《整理民间传说方法》和《中国神祗史》两科。此外,他也会在历史系的常规课程中穿插民俗学的内容,并把自己的民俗学著作送给学生。 无论《民间文艺》还是“民俗学会”还是《民俗》周刊,都是在顾颉刚的倡议、领导和筹划下得以付诸实施的。虽然顾颉刚并没有全程参与具体的编辑和组织工作,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没有顾颉刚,就没有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顾颉刚,就没有中国现代民俗学。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钟敬文,也没有中国现代民俗学。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伟大创建者,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民俗学。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