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是由众多地域文化构成的。浙江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入考察来进一步推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大课题。为此,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宁波大学于日前联合举办了“浙学论坛(2018):浙学·新时代的文化思考”学术研讨会。较之本刊之前所刊浙学文章,本期所选取的三篇会议论文视角独特,可谓有“里”有“外”:《学必证明于史》深入触及浙东史学发展的内在机理或机制,从而抓住了一个学派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派的“魂”;而另外两篇则将浙学由“古今”问题置于“东西”纬度,在比较的视野里观察其气象与脉络,《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浙学》讨论了浙江传统学术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外部冲击后所发生的变化,《西方文献中的李之藻》,更是以西文文献为依据,对明末浙江学者李之藻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独到的考察。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浙江传统学术文化,而且对研究其他区域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提到清代的浙东史学,学界公认经世致用为其显著特色,也是其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但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支撑一个学派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从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学术实践和学术理念来看,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无疑是该学派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大力倡导经世实学,尤有志于史学研究,明确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他广搜博采,汇聚明人文集多达二千余家,手自披览,采择编选,先成《明文案》217卷,后增辑为《明文海》482卷,被后世学者誉为“一代文章之渊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目睹“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俟后人之掇拾,然而泯灭者多矣”(黄宗羲《南雷诗文集·都督裘君墓志铭》)之情形,黄宗羲十分痛心,故而他尽力搜集记载明末人物史事。他始终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南雷诗文集·万履安先生诗序》) 黄宗羲之学,博大精深,气象宏阔,于宋代以来各家学术,陶冶熔铸,无不会通。后世学者推崇他“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而浙东地区自宋代以来学术文化就十分发达,史学一脉亦源远流长,黄宗羲曾在一首诗中简要梳理南宋以来浙东史学的发展脉络,并表达了对前代史学大家的敬仰之情。诗曰:“昔也宋金华,文章莫与雠。后此三百年,玉峰为介邱。元明二代史,属之以阐幽。推琴起讲堂,束帛多英俦。直不让南董,于以赞《春秋》。”(《南雷诗历》卷四,《次徐立斋先生见赠》)前代学者既已为浙东史学创辟榛莽,黄宗羲生当易代之际,怀抱故国之思,更毅然以保存一代文献史事为己任。这种以传承文化、延续文脉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堪称浙东史学的显著特色,也是黄宗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并为浙东史学开启崭新局面的重要原因。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特设博学鸿儒科,又重开明史馆,网罗明末遗臣和著名学者参与《明史》的编纂工作。黄宗羲坚持孤臣孽子之心,不与清廷合作,但他最终同意弟子万斯同及其子黄百家进京参与修史,并将自己有关明史的著述和搜集的资料交付万斯同,以作修史参考。他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诗文集·补历代史表序》)可见黄宗羲把保存一代文献、修成一代信史的希望,寄托在其弟子万斯同身上。万斯同遵其师嘱托,怀抱“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接受总裁徐元文的多次聘请,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他发凡起例,拟定传目,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钱林《文献徵存录》卷一,《万斯同传》)。在史稿的修订方面,万斯同耗费心血精力尤多。当时诸纂修官分别撰写的史稿,最后都集中于总裁之处,由万斯同审核修改,排纂成编。据记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鲒埼亭集》卷二八,《万贞文先生传》)今宁波天一阁珍藏的万斯同《明史稿》,其上多有朱笔、墨笔以及白粉笔先后数次修改涂抹的字迹,足证万斯同为《明史》纂修付出的心血。今本《明史》能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编写质量较好、学界评价较高的史书,与万斯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全祖望(1705—1755),人称谢山先生,是浙东史学传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他私淑黄宗羲、万斯同,于黄宗羲尤仰慕有加,一生读书治学,成就卓著,其史学研究的文献特色尤为突出。他曾与礼部侍郎李绂一同借抄清宫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开启清代利用《永乐大典》的先例。又致力于整理校注历史文献资料,撰成《七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稽疑》《困学纪闻三笺》等书。在乡邦文献的搜求和仁人志士的表彰方面,全祖望与黄宗羲更是一脉相承,声气相通。他生活的甬上,自南宋以来,就是“忠义之邦”和学术之乡,明清之际又是江南抗清的重要基地,故而“明季遗民之盛,莫如甬上”,忠义之士,多出其间。全祖望浸润其中,深受影响,他不遗余力,多方发掘其乡先贤及江南地区志士仁人生平行迹,大量撰写墓志、传记、碑铭,阐幽发微,唯恐不及。据统计,全祖望《鲒埼亭集》中墓铭传状之文共计32卷,占其文集全部88卷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这多达32卷的篇幅中,他总共撰写了210篇传记碑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记载明清之际人物及相关史事的碑传文字。如孙嘉绩、钱肃乐、张煌言、张肯堂、沈廷扬、张名振、董志宁、王瓒爵等诸多仁人志士,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万斯同、刘献廷等著名学者,无不囊括其中。而全祖望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不仅极为重视厘清其生平行迹,阐扬其忠义大节,而且笔端常带感情,字里行间多凛然正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章学诚称赞“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与胡洛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可谓知言。 章学诚(1738—1801),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法等方面造诣独深,“其中倡言立义,多前人所未发”,“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章华绂《文史通义跋》)。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在与学者讨论方志纂修问题时,曾明确指出:“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予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对史料包罗范围、文献采择方法等问题,章学诚也多有论述。他还专撰《校雠通义》一书,阐述文献整理的宗旨和要义。其中所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宗旨,至今仍是学界公认的文献整理及目录编纂的最高标准。 而在清代浙东史学的传承发展上,章学诚堪称是予以总结扬厉的有力殿军,所撰《浙东学术》一文,首次从理论上对浙东学术做了高度概括。他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正是因为章学诚明确梳理了浙东学术从宋至明而清的渊源流变,大力倡导浙东学术“切于人事”的经世性质,并揭示出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特色,尤拈出史学一脉中自黄宗羲开启新局,经万斯同弟兄继武其后,至全祖望接续其意的传承线索,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自此而后,浙东史学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始逐渐为学者所认同。 综而观之,清代浙东史学在其开创、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文献特色和自觉的传承意识。从黄宗羲,到万斯同、全祖望,至章学诚,无不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正是这种扎实的文献基础,为浙东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赋予了浙东史学朴实厚重的品格。而浙东各位史学大家所具有的自觉的传承意识,所秉持的坚定的文化担当,不仅为浙东史学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大大发扬了中国古代学人士子自觉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思想理念,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又一典型范例。 (作者:黄爱平,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浙学 作者:龚缨晏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并于1524年前后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建立起贸易居点,直到1548年才被明朝军队捣毁。双屿港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的第一个贸易居点。在葡萄牙人活动期间,有些浙江人搭乘葡萄牙人的船只,最后漂泊到了西欧,成为最早侨居欧洲的中国人之一。因此,浙江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主要区域。 在明末清初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学者及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浙江籍的。我们知道,1583年,正是在肇庆知府王泮(绍兴人)的鼎力帮助下,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才得以首次在中国内地居住下来,从而获得了在中国发展的广阔空间。利玛窦于1601年来到北京后,获得了一大批浙江籍官员的支持。在“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中,除了徐光启是上海人之外,其他两位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杭州人。17世纪初,金尼阁、艾儒略、卫匡国等一大批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在杭州生活过。杭州因此还成为中西交汇的学术中心。《职方外纪》《西学凡》《寰有诠》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就是在杭州出版的。 通过直接与利玛窦等人交往、间接阅读他们的著述等途径,明末清初的一些浙江籍学者逐渐了解、学习、甚至接受了西方文化。当然,更多的浙江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西方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这样,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西方文化的作品。这些著作,有的全文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如李之藻的《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有的被列入《四库存目》中,如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另一位杭州人许胥臣的《盖载图宪》等。还有一大批杰出学者,如杨廷筠、虞淳熙、刘宗周、吕留良、黄宗羲、万斯同等,虽然《四库全书》只收录其部分著作,但实际上他们都讨论过西方文化,或赞赏,或疑惑,或拒斥。当然,更多的著作及作者,《四库全书》根本没有提及。相反,在巴黎、罗马、东京、圣彼得堡等地的图书馆中,却可以找到这些浙江学者的著作。明清之际浙江学者关于西方文化的著作,成了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从明朝末年开始,由于西方文化强烈地影响了浙江学者,因此,浙江传统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空间视野。1405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曾经到过非洲东海岸,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向西航行所到达的最远地方。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浙江绍兴人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中,详细列举了他们所经过的20个主要国家。这些国家,都位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最后一个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天方国”。从16世纪末开始,浙江学者的空间视野已经扩大到整个世界。1599年在南京与利玛窦见过面的鄞县人徐时进介绍了“八万里而遥”的欧罗巴(欧洲)。1602年利玛窦绘制、李之藻资助、“钱塘张文焘过纸”的《坤舆万国全图》,则完整地展示了包括美洲、南极部分在内的整个地球。 第二,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浙江的天文学历史悠久,东汉时期的王充就专门探讨过天体问题。六朝时余姚人虞耸、虞喜等人提出过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但传统的天文学一直停滞不前。明朝末年,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依据西方天文学理论,进行了历法改革。清初,黄宗羲研究过西方天文学,他的儿子黄百家则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这样,浙江的天文历算研究,就从传统迈向近代了。 第三,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近代欧洲人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开路先锋,就是先进的火炮。1548年明朝军队在捣毁双屿港的过程中,就缴获过欧洲火炮,并且进行过仿造。明末,赵士桢等浙江人对欧洲火炮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写出了《神器谱》等著作。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后,带来了许多西方制作的器物,包括令中国人颇感新奇的自鸣钟。明末徐时进、朱怀吾、沈德符等浙江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讲到过西洋自鸣钟。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将西方逻辑学首次介绍到中国。此外,随着天主教的传入,李之藻、杨廷筠、朱宗元等一批浙江人写过许多关于天主教的著作。所有前述这些内容,不仅在此前的浙江学术文化中是没有的,而且,在中国学术文化中也是没有的。这些全新的学术领域,是浙江学者面对着全球化冲击而开拓出来的。 第四,引发了新的学术论题。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当欧洲文化传入中国后,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从而引发前所未有的学术新论题。由于浙江学者较早、较多、较深地接触了西方文化,所以,明末清初,许多浙江学者讨论过这些新论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问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中心,距离中国越远,其文明程度就越低。据此,“弹丸穷岛居西极”(万斯同诗句)的欧洲,应当是非常野蛮落后的,可事实上,他们却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人据此而拒绝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刘宗周就这样说过:“四夷”的天文学,“未必尽行于中国也”。而黄宗羲等人则一方面努力学习西学,另一方面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来论证学习西学的理论依据。此外,根据利玛窦等人所带来的天主教,中国人不能祭祀祖先和孔子,只能崇拜上帝,这就与儒家学说、佛教教义、民间习俗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明末清初的浙江,天主教学者杨廷筠、朱宗元、张星曜等,以及更多的反天主教僧俗学者沈、许大受、虞淳熙、莲池法师等,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或发难辩驳,或释疑解惑。这些论著,丰富了浙江学术文化的内涵,激发了浙江学术文化的活力。 第五,催生了新的文化思想。陌生而先进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浙江学者中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明末许大受认为,必须彻底禁绝西方文化,即使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必须一并禁绝,因为西方科技虽然“巧”,但“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与此相反,李之藻等人则以宋儒“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点为依据,用杨廷筠的话来说,就是“东海西海,不相谋而符节合”。这些论述,实际上蕴含着可贵的现代意识: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共同的价值,拥有各自的优势,因此,我们应当以平等的心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抱着居高临下的心态来俯视西方先进文化。侯外庐评价说:李之藻等人学习西方文化的活动,“正反映着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要求”。 浙江的学术文化悠久而深厚,但同时又与时俱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汲取外来先进文化,从而保持蓬勃的活力。在新的时代,浙江学术文化更要发扬这种广采博取、包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从而推动浙江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作者:龚缨晏,系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西方文献中的李之藻 作者:金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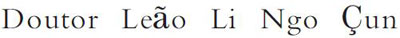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明末杭州人李之藻,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陈垣于1919年发表的《明浙西李之藻传》,开创了对李之藻的研究。方豪于1966年出版的《李之藻研究》,则是集大成之作。进入21世纪,龚缨晏、郑诚、邬国义等人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但是,由于有关李之藻的汉语史料非常匮乏,许多重要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样,西方文献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一、李之藻的名号。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凉庵逸民、凉庵子、凉叟、存园寄叟、东海波臣。在西文文献中,除了“官人李之藻”(Madarin Licizao)这个称呼外,许多来华传教士根据中国习俗,以字号相称,如利玛窦称其为“Lingozuon”,熊三拔笔下作“Lengocum”等。这些都是“李我存”一名的拼写。不过,使用最多的还是“凉庵”之号。熊三拔还将姓、字和号联用,称之为“李我存凉庵(见图一)进士”。李之藻自己在1626年用葡萄牙文书写的《上耶稣会总会长书》中,自称“东方弟子李凉庵”(Ly Leam)。因此可知,在教内李之藻的正式名字是“李凉庵”。所谓的“凉庵”,其实是葡萄牙文“(见图二)/Leam”的音译。此词在拉丁文中作“Leo”、西班牙文为“(见图三)”,意大利文的书写形式是“Lione”。在拉丁文和新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leo/(见图二)(leam)/(见图三)/lione”为一普通名词,意即“狮子”。但在中文里,如果直接将“狮子”或“狮”这样的动物名用作个人字号,显然不雅,于是李之藻非常巧妙地将其译成“凉庵”,作为自己的字号。从词汇学来分析,“(见图二)”或“Leam”由两个音节构成,与“凉庵”的读音完全吻合。因此,“凉庵”之译名,在读音上忠于西文原词,在中文里又具有深奥的韵味。这个译名,既体现了李之藻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反映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认识。 二、李之藻的生卒年月。关于李之藻去世的时间,明末清初在华的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见图四)在《远方亚洲(Ásia Extrema)》手稿中(1644)明确说:“他(凉庵进士,Doutor Leam)按皇帝的谕旨返回京廷。路上病情加重,进京时未有康复。数月后,在京去世。正巧是万圣节,即阴历九月二十七日,合阳历1630年11月1日。” 对于李之藻的出生年代,学者们则有不同的说法。方豪先生认为是1565年;法国传教士裴化行则主张是1566年;郑诚提出“约1565”;龚缨晏根据《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便览》确定是1571年10月13日。考诸史源,“1565年说”或“1566年说”其实是根据1630年逝世日期倒推出来的。鉴于中西文史料的不同记载,目前看来,还无法解决李之藻的出生年代问题。 三、李之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李之藻在天文、历算、地理学等方面的贡献,早已广为人知,现在几乎每年都可见到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但根据西方文献,李之藻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推动了西方文化知识在中国的合法化。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去世。负责利玛窦后事的有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在用葡萄牙文书写的一份日志手稿中写道:在为利玛窦守灵期间,“有个杭州Juen姓天主教徒,进劝庞迪我神父说,向皇上疏请恤,请求赐地,安葬利玛窦神父。庞迪我神父和李我存凉庵(见图一)进士共同起草了一题本,然后交熊三拔神父过目。他们认为,还应当索要一座古庙,得到了它,我们不仅拥有了坟地,且获得了设立教堂之处,因此,题本申请赐隙地一块或旧庙一座。5月18日,庞迪我神父以利玛窦神父同伴名义,向天子呈送了题本。凉庵(见图五)进士时在京廷,曾鼎力相助”。对照中文史料,可以知道,庞迪我和李之藻起草的这份题本,就是著名的《乞收葬骸骨疏文》。庞迪我是西班牙人,李之藻则是明朝的官员,因此,这份题本,虽然以庞迪我、熊三拔的名义上奏,但其执笔者无疑是李之藻。 1601年,利玛窦入居北京,但一直没有正式的身份。《乞收葬骸骨疏文》入奏后,明朝礼部官员认为,利玛窦“虽其自来中土,与外所遣陪臣不同,但久依辇毂,即属吾人”,应当赐地安葬。神宗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样,利玛窦获得了一块墓地。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通过获得钦赐墓地,不仅利玛窦个人的身份合法化了,而且,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合法化了。而这一事件的主要推动者,正是李之藻。 最后,讨论一下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位“杭州Juen姓天主教徒”。我认为,这个Juen就是“阮”的音译,此人就是阮泰元。在《帝京景物略》中,提到了“杭州阮泰元”“仁和阮泰元”,由此可知,阮泰元与李之藻是同里。在利玛窦于1603年绘制的《两仪玄览图》上,有署名为“□斯阮泰元”的题跋。对于“斯”前面那个残损难辨的汉字,德礼贤主张是“来”,黄时鉴、龚缨晏及黄一农认为是“耒”,王绵厚和杨雨蕾则认定是“采”。我们认为,应该是“耒”字。“耒斯”,亦作“类斯”。它们是葡萄牙文洗名“Luís”的音译,其古形式写作“Luiz”。龙华民于1602年在韶州刊行的《圣教日课》中有《圣类斯公撒格祝文》。“圣类斯公撒格”的葡萄牙文是“(见图六) Luís Gonzaga”。耶稣会士金尼阁撰写的1621年年信同时涉及了徐光启、李之藻和此人:“……其师耒斯(Luiz)均为教徒……”因为有了葡语名字,便可确定是“耒”字,而不是“来”或“采”。 本文所讨论的几份西文文献表明,李之藻这一文化名人,既是浙江的,也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今天,在“浙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当重视西文文献的搜集整理。此外,随着中外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陆续披露,方豪先生许多已成定论的观点,似乎需要补充,甚至修正了。编写一部更完善的《李之藻传》是“浙学”应该提上日程的任务了。 (作者:金国平,系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