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唐作藩 北京大学 编者按:2020年,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110周年之际,北大中文系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参与专访的38位学人,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 2022年1月,这份汇聚北大中文几代学人身姿与风采的访谈实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中国作家网经出版方授权,特遴选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唐作藩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音韵学家,在这则对话中他回顾了自身的学术与人生路径,并向后辈敦敦教导,“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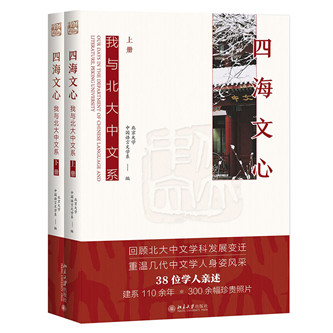 《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上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受访人:唐作藩,1927年生。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语言学论丛》《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中国语言学》学术委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汉语史学习与研究》《汉语语音史教程》等多种著作,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采访人:向筱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在读博士生。 采访时间:2020年9月18日  唐作藩先生 向筱路:唐先生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领域有深厚的造诣。从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算起,您已经在北大中文系工作和生活了六十多年。今年适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对您做一次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与北大中文系的故事,以及您对汉语音韵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您是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接受的大学教育,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那一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唐作藩:好的,我回顾一下。我觉得我是文人命啊!我的运气好吧。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邵阳地区,当时叫武冈县。现在从武冈分出一个洞口县,洞口县下面有一个小镇,叫黄桥镇—江苏不是有一个黄桥么,我们那边也有一个黄桥镇—我就出生在那个小镇上。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我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父亲在商店里当了两年学徒,刚刚出师吧,自己做一点小买卖。十一二岁的时候,母亲老是带着我到外婆家去,所以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里长大的。我外婆又善良,又能管家。外公我从来没见过,很早就去世了。另外外婆家里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大姨妈。后来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自己还有地种了。本来我父亲要我跟他一样,去当个学徒,做点小买卖。但我的一位二叔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父亲有三兄弟,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我的二叔长年跑外,先是在家乡的小镇,然后到宝庆府,即今邵阳市。我们那里近代出了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魏源,武的就是蔡锷,所以别看这么个小地方,还是出了不少名人。因此我二叔的眼光比较长远,他对我父亲说还是读书好。 这句话可以说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是我父亲就送我去读书了,即先去上黄桥中心小学。我本来念了两年私塾,那时候已经十二三岁了。去报名的时候,校长曾育贤老师说你这么大了,不能从一年级学起,念五年级吧。我一辈子都记得,念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期末考试得了37分,不过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全班的第二名了。读完小学后接着去读中学,考上了洞庭中学。抗战时期国民党有一个军校,叫作军二分校,校长叫李明灏,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因为当时有好多教官的子弟要上学,他就创办了这所中学,在湖南武冈县县城郊外,取名叫湖南私立洞庭中学。我记得我是在初10班,后来在高4班,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我老伴。我念高中的时候,她念初中。她家里比较富裕,有三姐妹,父亲是国民党的上校,所以跟着去了后方。她当时还在念初中,两个姐姐读高中。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演话剧,我记得演过《万世师表》,讲闻一多带着学生从北京到昆明的故事,我演老师,她演学生,她大姐就演我的老伴。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认识了。  唐作藩与夫人唐和华合影 本来我是想考北大的,我记得当时北大和清华同时招生,要么报清华,要么报北大,我就报了北大,结果没考上,考上了中山大学。那时候在湖南还不能参加北大、清华的招生考试,得到上海去。湖南不是出锑嘛,有很多锡矿山,实际上是出锑,出的锑常常要运到上海去。一个工程师的儿子跟我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就坐运锑的船去上海,参加考试。  1982 年春唐作藩与王力先生(左)合影 因为我们在中学演过话剧,我当时不知道,以为语言学系是演话剧的,就这样报考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本来中山大学没有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创办的。王力先生是清华的教授,系主任是朱自清,原本他是准备回清华的。在他回北京之前,先回了广西老家,然后经由广州回北京。结果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挽留他,请他在广州待几年,然后再回北京。于是王力先生给朱自清写信,说有朋友要他留在中山大学。朱自清说也好,同意他待在广州。王力先生给中山大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创办语言学系,校长答应了他。我记得那时候除了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高华年先生、严学宭先生等。高先生是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另外还有黄伯荣先生,当时是助教,后来我毕业的时候他是讲师。 向筱路: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您也随之北上,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唐作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提出一个建议(他是王力先生在清华时候的学生)他想把全国搞语言学的老师集中到北大来,从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专业中分出一个语言专业,这样就在1954年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全部老师和学生调来了。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那一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招了三十名学生,是历年最多的,以前总是只有五六个人。我们那一级也只有六七个人,现在有些还有联系,你可能听说过。如暨南大学的詹伯慧,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欧阳觉亚,现在在美国的饶秉才,还有麦梅翘,毕业以后留在了社科院语言所—麦梅翘比我们都大,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刚才说胡乔木要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师资力量。当时的燕京大学也合并过来了,像高名凯先生和林焘先生都是燕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是老北大的教师,还有周祖谟先生,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都集中到北大来了。那时候北大没有语言学系,所以王力先生建议创办一个语言专业。后来成立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汉语教研室,一个语言学理论教研室。语言学理论教研室是高名凯先生做主任,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做主任,后来汉语教研室又分为现代的、古代的两个,那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 我1954年来到北大,本来那时候中文系不光有汉语言、语言学专业,还有一个新闻专业,后来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去了。 向筱路:到了北大中文系以后,有哪些先生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呢? 唐作藩:主要是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本来在中山大学,留下我是做岑麒祥先生的助教的,跟着岑先生学语言学理论。到了北大以后,王力先生对我说语言学理论教研室已经有两个助教了,就是石安石跟殷德厚;我们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还没有助教,那你就跟着我学汉语史吧。这样我就转换了研究方向,从此就一直跟随王先生。我记得那时候住在现在咱们中文系所在的原朗润园教师住宅区。朗润园还是有四合院的房子,还没有盖咱们现在这个人文学苑,旁边住的是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住在未名湖边的,我记得还有季羡林先生。我在那里就这样度过了好些年。  1955 年秋北大汉语教研室教师在颐和园听鹂馆前合影(左起:潘兆明、梁东汉、周祖谟、唐作藩、 魏建功、杨伯峻、姚殿芳、黄伯荣、林焘、王力、吉常宏)  1974 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戴澧、王力、岑麒祥、林焘,后排 左起依次为:蒋绍愚、张万起、唐作藩、徐敏霞) 刚才提到,到北大之后,王力先生要我就跟着他学。这时候正好吕叔湘先生提出要普及语言学的知识,他就跟王力先生说,您来写一个音韵学的普及读物吧。王先生住的那个四合院,实际上只有东屋、北屋和西屋,王先生住在北屋和东屋,我就带着我老伴和一个三岁的小孩,住在西屋,虽然只有一间房,但有卫生间。王先生把我叫过去,对面就是他的书房,他说刚才开会回来,吕先生要求我写一本音韵学普及读物。他就要我写,我说我还没学,他说边学边写、边写边学。这样我就写了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没想到那本书后来在我国香港(1972)也出版了,在日本还出了两种正式翻译本(1962,1979)和一种自印翻译本。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现在,从事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 向筱路:关于“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这两门课程,您后来都出了教材,就是《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影响很大。这两本教材的编写过程,您在后记里都做了一些说明。我想请您讲讲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自己来编写教材?它们和同类的著作相比有什么突出特点?比如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在1936年就出版了,后来改名《汉语音韵学》,他在50年代出版的《汉语史稿》(上册)也是语音史的内容。  唐作藩编著的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书影  1980 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后北大校友留影(前排左起:徐复、黄绮、刘又 辛、殷焕先、严学宭、郭良夫、王均、李格非、唐作藩;后排左起:杨耐思、王宗孟、赵振铎、陈 振寰、杨春霖、许绍早、李思敬、许梦麟、但国干、鲁国尧) 唐作藩:另外还有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导论》,是吧?王力唐作藩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他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包括罗常培先生的《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原来是跟着王先生写《汉语音韵学常识》,然后就是《音韵学教程》,是这样的。后来再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也是考虑到学生们反映看王先生的那些书,不容易看懂。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写得更通俗一些,让学生除了在课堂听课,也能够自学。 向筱路:主要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早地、更方便地入门。 唐作藩:对。那时候同学住在礼堂前面,咱们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原来是大饭厅,我记得外面行人路上还有一个桥。那时候很少有汽车,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在那后面还有一个食堂,邮局也是在旁边,就在三角地,还有好些小商店。那时候同学们就住在前面的楼里,现在是多少号楼我都记不得了,在礼堂的南边,他们常邀我到学生宿舍里面去辅导,尤其是57级、58级、59级的那几个班。 向筱路:汉语音韵学可以分为今音学、古音学、北音学和等韵学,它们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您对每个门类基本上都做了研究。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越来越细,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限于时间和精力,往往只能就其中一个方面进行探索,难以做到全面贯通的研究。音韵学研究也有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唐作藩:这种做法太窄了,我觉得不太合适。你学音韵学不光是音韵学本身,还要有汉语方言的基础,因为很多古音都保存在方言里面,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广州话、客家话、福建的闽方言,都保存了比较多的古音。所以5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方言学课,我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他学了,学了以后还记录了我湖南家乡的方言,记录以后请他看,后来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所以我觉得音韵学跟方言是分不开的,学音韵学一定要学好方言学。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语音学学好,没有语音学的基础,你就不会记音了,是不是?  唐作藩给中文学子题词:“学,然后知不足!”[徐梓岚 摄] 向筱路:很多人把音韵学称为绝学,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研究人员都有比较高的门槛。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高校的中文系或者文学院没有开出“汉语音韵学”等课程,北大有非常好的研究汉语语音的传统。您觉得北大中文系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唐作藩:我觉得一方面系里面在安排课程的时候,不要忘了安排这门课,虽然有时候选课的人少,但是还是应该开。另外就是要招收音韵学方向的研究生,因为你要想进一步学好音韵学,还是要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另外,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学语言学的需要音韵学的基础,学文学的有一点音韵学基础也是好的。我的好朋友袁行霈先生,他就听了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到现在我们还经常有联系。 向筱路:您觉得就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北大中文系目前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强的? 唐作藩:据我了解,我觉得我们中文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好几个教音韵学的教师。除了孙玉文老师,还有现在已经退休的耿振生老师,还有张渭毅和赵彤,赵彤本来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人大,现在调回来了。 向筱路:您在北大指导了不少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您在指导过程中,最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具体是怎样体现的? 唐作藩:跟我学的日本的学生比较多一点,最早是花登正宏、古屋昭弘,还有平山久雄的一个学生,叫什么我一下忘了。另外我在马来西亚教了一个学期的课,除了教音韵学,另外还开一门《诗经》研读课,所以有些那时候的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来旅游了,总是要来看看我。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坚持开这些课吧,是不是?本科就开音韵学,研究生就开上古音,中古音,《切韵》,还有《中原音韵》,对不对?过去咱们的校友杨耐思先生是研究《中原音韵》最好的学者,可惜已经去世了。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好既要做到专深,也要做到广博。比如说你要是重点学中古音,近代音、上古音也得掌握,另外我也反复强调方言学对学习音韵学、汉语史的重要性。 向筱路:您在中文系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六十多年,您觉得有什么特质是北大中文人最应该坚守的? 唐作藩:我觉得一般来说,北大的师生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像袁行霈先生他就强调,学文学也得学点语言学,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对。那么我们学语言学的人也不要忘了文学,也得学点文学,这样比较全面一点。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尽量去了解一下别的学科,这样对提高自己本身的研究也会有帮助。 向筱路: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对北大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唐作藩:当然是希望能越办越好了。除了留我们自己学校毕业的,外校如果有好的青年人才也可以交流,条件成熟的话把他们引进。因为要办好一个学校,办好一个系,主要还是教师吧,教师好,开的课才好,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是不是?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就是各个方面的教师都有,除了中大的,我记得还有从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调来的。当然,他们应该都是有专长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