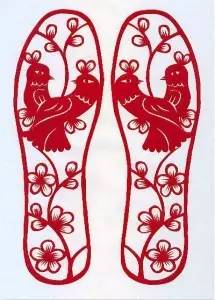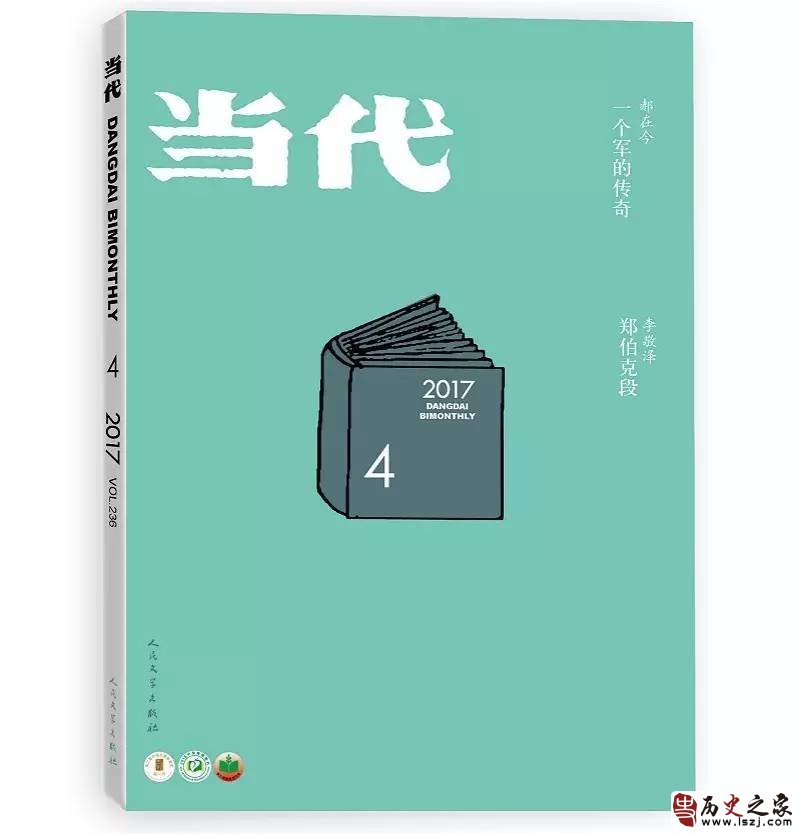|
“黄连开花儿一肚肚苦,骡儿家的苦水跟谁吐;
煤窑窑开花儿黑加黑,下辈子拴我脑袋也不来。
天轮轮开花儿吱呀呀响,谁家的孩子不想娘;
荞麦子开花儿愁连愁,哥哥你一去为啥不回个头。
以前她每天接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自从丈夫不在了,她接回来的只有她家的骡儿……
”  刘庆邦,1951年生于河南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神木》《遍地白花》《刘庆邦小说自选集》《民间》等十余种。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车倌儿
文|刘庆邦
原载|《当代》2005年02期
早上六点来钟,太阳还没出来,窑嫂宋春英就去窑口下面接她家的骡儿。这里不把骡子叫骡子,这家那家,都在骡后面加了儿音,叫成骡儿。这种叫法儿好像是对骡子的一种昵称,叫起来亲切些。煤窑既然是一座开采规模不大的小煤窑,窑下运煤就没有使用电机车,而是使用了运输成本相对低廉的骡子拉车。一天三班倒,一班大约下窑六十来头骡子。拉车时间加上交接班和上窑下窑在斜井里走道儿的时间,一头骡子一个班要在窑下待十来个钟头。比如上夜班的骡子头天晚上九点下窑,要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之间才能陆续上窑。到了这个时间,宋春英就提前到窑口下面去等。不管好天好地,还是刮风下雨,她一天都不落下。其实宋春英家的骡儿认路记家,宋春英不必到窑口接它,它出了窑,自己就会回家。可宋春英每天接骡儿已经成了习惯,不及时把骡儿迎接一下,好像对不起劳苦功高的骡儿似的。以前她每天接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自从丈夫不在了,她接回来的只有她家的骡儿。
有接骡儿习惯的不止宋春英一个,不少窑嫂都在窑口下面等着接骡儿。窑口建在一个山坡的平台上,平台高出地面两丈多。平台下面是窑上的风机房,那些窑嫂就站在风机房后面或房山东头,仰着脸,眼巴巴地朝高处的窑口望着。她们沿着阶梯攀上平台,直接到窑口接骡儿不行吗?不行,绝对不行!不知是哪个说的,煤窑是窑儿,女人也是窑儿;煤窑属阴性,女人也是阴性,窑儿碰窑儿,阴性碰阴性,是不吉利的,女人一到窑口,窑下就可能出事儿。女人们别说到窑口去了,哪怕走得离窑口稍近一点,就会遭到窑口信号工和检身工的大声呵斥,让她们离远点儿。别的大一些的煤窑,开绞车的,发灯的,做饭的,要用一些女工。女工工资低,用起来便宜些,还可以给窑上调节一下空气。这座窑为防止女人因工作关系接近窑口,连一个女工都不用。窑主因此很骄傲,说在我窑上做工的是清一色的男人。那些等着接骡儿的窑嫂对该窑的性别歧视都很有意见,她们说,都到啥社会了,还这样看不起女人,真不像话!有意见归有意见,窑上窑下的规矩她们还得遵守。
一个窑嫂说,出来了!好几个窑嫂马上附和,出来了出来了!她们的声调和表情都很欢喜。
此时太阳刚露出一点红边,从那点红边看,将出升的太阳不知有多么巨大呢,也许会把半边天都占满吧。太阳红得很厚实,恐怕挑一块最大的煤烧红,都赶不上太阳红得厚实。太阳红得也很艳丽,很有传染性,它不仅染红了天际,连那些窑嫂们脸上都有些红红的。别误会,她们说的出来了不是指太阳,而是指从窑口出来的第一头骡儿。不错,窑口朝西,骡儿是从地底冒出来,是从东边出来。太阳出来的地点、方向、时间和骡儿几乎一致。可窑嫂们用近乎欢呼的声调所说的出来了的确指的是骡儿,不是太阳。也就是说,在她们心目中,骡儿比太阳更重要,更值得她们关心。
骡儿从窑下出来,都要在窑口处稍稍站一下,往下面的窑场看一看,并不急着马上离开。它们都不会说话,从没接受过记者采访,谁都弄不清它们为何站下?看到了什么?有何感想?它们目光平静,像是有所沉思。沉思过后,它们顺着绞车道往上走几步,往里一拐,从平台一侧的斜坡上走下来。不管是黑骡儿、白骡儿,还是灰骡儿、红骡儿,它们身上的毛都湿漉漉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淋水。它们一定是累坏了,也饿坏了,一走下斜坡,就低下头,嘴唇贴向地面,开始找吃的。地上都是脏污的煤尘,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有的骡儿嘴唇触到一根劈开的葵花秆儿,衔住吃起来。还有的骡儿衔起一只废弃的纸烟盒,竟像吃树叶儿一样吃到嘴里去了。每一头骡儿后面都没有跟着赶骡儿人。赶骡儿人也叫车倌儿。车倌儿下班后,都坐着笼形的载人车,提前出来了。骡儿的体积太大,进不了笼车。再说骡儿天生是拉车的,好像也没资格坐车。
宋春英的骡儿是一头青骡儿,青骡儿刚拱出窑口半个身位,宋春英一眼就认了出来。她的嘴张了张,想对着青骡儿喊一声,告诉青骡儿她在这儿呢!因青骡儿没有姓氏,她也没给青骡儿起名字,不知喊青骡儿喊什么。她快步走到斜坡下面,一手抚着青骡儿的脖子,一手把绾在青骡儿辔头上的拴青骡儿的皮绳解开,把皮绳牵在手里。她看看青骡儿的眼睛,还没等青骡儿看她,就把目光躲开了。她听人说过,骡儿的眼睛看人时,人形是放大的,能比人的原形放大好几倍,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不然的话,骡儿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出许多,不可能受制于人类,在人类面前不会这样驯服。因骡儿的眼看人高大,才对人有些害怕,不得不受人使唤。宋春英之所以不愿让青骡儿看见她,是不想在青骡儿眼里变形放大,免得青骡儿害怕她。她想跟青骡儿保持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不看青骡儿的眼睛了,她就看青骡儿的四条腿和四只蹄子。蹄子踏在地上哒哒的,四条腿迈动得很均匀,没有什么问题。青骡儿的背部和臀部两侧呢,也没有磨破和受伤的地方。看到青骡儿一切正常,她就放心了,牵领青骡儿到一个固定的、细土多的地方去打滚儿。从窑下出来,骡儿们都要在地上打一个滚儿,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作和程序。骡儿们为什么非要打滚儿呢?是为了去痒?解乏?还是为了干净呢?也许这几项作用都有吧。好比窑哥们儿从窑下出来都要洗一个热水澡,热水澡一洗,就舒服了,来精神了。青骡儿腿一屈卧下了,先把肚子右侧在土里滚了两下。滚过右侧,它四蹄一弹,弹得仰面朝天,又迅速滚向左侧。左侧也滚了两下,青骡儿的滚儿就算打圆满了。它站起来那么一抖擞,仿佛身上又来了使不完的劲。下一步,宋春英就该伺候青骡儿吃饭了。门口有一根木桩子,旁边支一个由大铁桶锯成两半做成的铁槽,铁槽就是青骡儿的饭碗。宋春英把青骡儿拴在木桩子上,青骡儿就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谷草筛过了,上好的黑豆泡好了,也煮熟了,青骡儿一回家就可以开饭。可惜青骡儿不会喝酒,要是青骡儿会喝酒的话,她会把白酒备上一点,举起杯对青骡儿说,来,干!宋春英早上给自己熬的是小米稀饭,盖在锅里还没吃。等青骡儿开始吃了,她才陪着青骡儿一块吃早饭。她听见青骡儿吃得很香,好像自己的稀饭也香了许多。  晚上八点半,车倌儿赵焕民准时到宋春英家牵青骡儿,准备下窑。这时宋春英已把青骡儿牵到屋里去了。她家用泥巴糊顶的小屋是两间,一间住人,一间住骡儿。两间屋有门相通,门口只挂一块旧布帘子。这里的贼人偷骡子偷得很猖獗,只要天一落黑,她就得把青骡儿牵到屋里去。之所以把两间屋打通,也是为了保护青骡儿,只要青骡儿那边稍有一点动静,她都听得见。赵焕民站在门口说,嫂子,牵骡儿。
宋春英开了门,让赵焕民进来。
赵焕民说,身上脏,不进去了。他头戴胶壳矿帽,脚穿深筒胶靴,已换上了下窑的衣服。窑上不发给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就是自己平常穿的衣服。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红秋衣,下身穿的是蓝裤子。不过煤粉子把红和蓝都遮盖住了,上下的衣服几乎都变成了黑色。
宋春英说,脏怕什么,进来嘛!
赵焕民只好弯一下腰进屋去了。屋里的地比较低,他脚下一闪,像下进坑里一样。屋顶也很低,只要一伸手,就会摸到屋顶。
宋春英指着一个小凳子说,坐一会儿嘛!
赵焕民没有坐,坐下说什么呢!他说还要去领灯,没时间了,牵骡儿吧。
宋春英打开那屋的门,把青骡儿牵了出来,交到赵焕民手里。她想跟赵焕民交代几句,青骡儿在窑下要是不听话,该骂就使劲骂,只是打的时候注意点儿,别打得太厉害。若打得太厉害,骡儿会受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骡儿有可能跟人记仇。有一个车倌儿打骡儿打得太厉害了,骡儿就跟他记了仇,拉着重车把他往煤墙上挤,结果把他的胯骨挤断了,好好的人成了残废。这些情况都是丈夫生前告给她的。听丈夫说,每个车倌儿在窑下都打骂骡儿。他们骂骡儿骂得声音很大,也很恶毒,从骡儿的亲娘亲姐亲闺女,一直骂到八辈祖宗。他们一边骂一边打,打骡儿打得也很凶。他们打骡儿的器具有多种,有的用皮鞭,有的用钢丝鞭,还有的用劈柴棒子,你只看骡儿出窑时身上的道道鞭痕、块块伤疤,就知道骡儿在窑下挨了多少打了。反正骡儿不会说话,他们好像不打白不打似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看得起做窑的,他们在窑主面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他们觉得憋气、觉得委屈,只有拿骡儿们发泄一下。不想想,你们拿骡儿们出气,骡儿们也有血有肉、知冷知痛,它们找谁出气呢!话到嘴边,宋春英没说出来。以前她每次向赵焕民交代,赵焕民都不说话,不好好答应她,这让她甚是担心,赵焕民在窑下不知怎样欺负她的青骡儿呢。每次接到青骡儿时,她都马上细心检查。还好,青骡儿身上没什么鞭痕,也没有被鞍子和套绳磨破皮的地方,这表明赵焕民对青骡儿还是不错的。这天她说出来的是,小赵,谢谢你!
赵焕民问,谢我什么?
你对青骡儿挺好的。
看出来了?
早就看出来了。
怎么看出来的?
宋春英笑了一下,说这话问的,用眼睛看出来的呗。
赵焕民说,我对青骡儿再好,也比不上嫂子你对青骡儿好呀!
宋春英说,那是的,我和郎郎就指望这头青骡儿了。
年初的一天,窑下的变压器着了火。因变压器放在一个用木头支架支起来的煤棚子里,变压器一蹿火,就把木头支架引着了,接着煤壁和煤顶也着了火,整个窑腔子里顿时狼烟动地,浓烟从窑口冒了出来。那些烟像水一样,无处不到,很快把各条巷道、各个采煤工作面都灌满了。烟和水又不一样,水先往低处流,在斜巷高的地方,人还可以暂时躲避一下。而烟是轻质的,不管高处低处,它一处都不放过。越是高处,越是边角,烟充得越满。须知那些烟是有毒的,它们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氧气吃完了,只剩下毒气。当时在窑下干活的有一百多个窑工,七十多头骡儿。毒烟一起,窑工和骡儿霎时乱了套,你往这边跑,他往那边跑,撞得人仰骡儿翻,堵塞了巷道。大概连老鼠洞里也充满了毒气,白毛老鼠也乱窜一气。那次着火,一共毒死了二十三个窑工,六十一头骡儿。当时,宋春英的丈夫驾驭的骡儿拉的是装满煤的重车,他想把骡儿从车上卸下来,拉着骡儿一起跑。结果还没等他把骡儿卸下套,他和骡儿就被毒烟熏死了。丈夫的尸首是完整的,倒在车辕里的骡儿也没有少皮掉毛。据下窑救护的人说,她丈夫死时,两只胳膊还紧紧抱着骡儿的脖子。死掉的骡儿,各家都没有剥皮、没有吃肉,也没有卖到肉坊里去,而是在窑外的山坡挖个坑,把骡儿深埋了。一头骡儿的市场价是四千块到六千块,窑上只给死骡儿的主人赔了一千块钱就完了。
丈夫和骡儿死后,宋春英和儿子在窑上没有走。窑上停产整顿四五个月,宋春英成天一点事干都没有,但她仍然坚持不走。她的老家在四川,离窑上很远。老家就那么一点点山地,每年打那么一点粮食,恐怕连供孩子上学都不够。窑上恢复生产后,宋春英把丈夫因工死亡窑上给她和儿子的抚恤金劈出一些,加上因死骡儿赔给的钱,她花了五千多块,买了现在这头青骡儿。没人为她下窑赶骡儿,她就雇了赵焕民当车倌儿。她家除了骡儿,还有一辆胶皮轱轳铁壳子车,她是主家。她和赵焕民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赵焕民刚到窑上打工不久,他没有骡儿,也没有车。而没这两样东西,他就没有下窑的资格,只能被有这两样东西的人来雇佣。这种关系不能说成赵焕民租用宋春英家的骡儿和车,只能说是主家雇佣车倌儿,主次相当分明。窑上在月底跟他们结算工资时,也是只找主家说话,窑方把工资付给主家,再由主家分给车倌儿。分配的方法一般是一半对一半,比如车倌儿一个月在窑下赶车拉煤挣了三千块钱,那么主家先留下一千五百块,另一千五百块付给车倌儿。这种雇佣车倌儿的办法不是宋春英发明的,她是跟别人家学的。有的人家只养骡儿,只置办车辆,骡儿养了两三头,铁车打制了两三辆,家人一个都不下窑,每辆骡车都雇佣一个车倌儿,只等着分骡儿和车股的钱就行了。当然,在一家只有一骡儿一车的情况下,男主人下窑赶车的多些,这样人和车挣的钱都是自己的,对自己家的骡儿也会爱惜一些。话说到这里就明白了,宋春英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的确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全靠青骡儿给他们挣钱。他们吃饭靠青骡儿,穿衣靠青骡儿,儿子上学交学费更得靠青骡儿。宋春英的丈夫没有了,郎郎的爸爸没有了,母子俩不靠青骡儿靠谁呢!  秋风凉了,窑上的煤卖得好,工资也比以前发得及时。这才九月半头,八月份的工资就下来了。窑上的账房通知宋春英去领钱,宋春英找到自己的名字往后一看,心里突地一跳,这个月的工资总数竟有三千八百多,扣除了她家的房费、赵焕民的房费,还有骡儿的保护费(每头骡子窑上每月收取八十块钱的保护费),还能得三千五百多。挣钱挣得多,说明赵焕民运煤运得多。窑上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装满一车煤重量是一吨,车倌儿们把一吨煤说成一个煤。每从采煤工作面运到窑底车场一个煤,车主和车倌儿就可以得到十二块钱的装卸费和运输费。整个算下来,赵焕民一个月运了三百多个煤,平均每天超过十个煤。据说运一趟煤来回要走七八里路,这十多趟煤,青骡儿和小赵一天要走多少路啊!
宋春英把自己应得的一半钱留下,把赵焕民的一半给赵焕民送去了。赵焕民正在宿舍里吃饭,他用铁锅煮的挂面。他还用一个装糖果的大玻璃瓶子腌了多半瓶子咸菜,里面有白萝卜、红萝卜、包菜片子,还有辣椒。他一边吃汤面,一边就咸菜,吃得满头大汗。他从窑下出来,一定是饿坏了,连澡都没洗,连窑衣都没换,就那么黑着脖子黑着脸,就开始做饭吃饭。见宋春英进来,他有些不好意思。窑工都是这样,在没洗澡没换衣服之前,都不愿让女人看见。宋春英说,正吃饭呢,你的饭太简单了。
赵焕民说,吃饱就行了。
那可不行,稀面条子不顶饿。宋春英的丈夫活着时,丈夫每天下了班,她都要给丈夫炒点肉,炒俩鸡蛋,还让丈夫喝点热酒,从不会让丈夫吃得这样简单。
赵焕民说,屋里太脏了,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没关系,我站一会儿就走。这个月的工资下来了,你干得很不错。
这都是青骡儿的功劳。
青骡儿有功劳,你也有功劳,至少有一半功劳是你的。给,这是你的一半工资,你数数。
赵焕民接过钱,没有数,就装进挂在墙上的干净衣服口袋里去了。
宋春英说,你这屋子不是放钱的地方,吃了饭,洗了澡,先别睡觉,马上坐车到县里邮局,把钱寄回家去。
我知道。
宋春英要走时,赵焕民喊住了她。赵焕民说,嫂子,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宋春英以为是有关工资分配的事,说,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赵焕民说,嫂子,我劝你以后别去打麻将了。
哦,是这事儿。宋春英说,我没打,我只是去看看。
我听说你昨天输了九十多块。
谁说的?
我在窑下听别的车倌儿说的。
宋春英无话可说了。她心里还是不大服气,我打麻将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又没花你的钱,你管那么宽干什么!
马字搭个累字就是骡儿,骡儿挣点钱不容易。有那几十块钱,还不如给孩子买几本书呢。打麻将的人最后没有赢钱的,都是输钱的。
宋春英脑子里在拼字,骡儿的骡果然是马字和累字拼成的。她也是初中毕业,骡这个字成天在脑子里过,怎么没想到骡原来是马累或是累马呢!看来在对骡儿的理解上,她还不如赵焕民。
青骡儿吃饱了,在眯着眼儿晒太阳。天很蓝,太阳很好,阳光照在人身上穿透力很强。每天这个时候,宋春英该去打麻将了。窑场大门口右侧有一个饭店,去那里吃饭的人不多,去打麻将的倒不少,饭桌变成了麻将桌。每天,打麻将的至少开两桌,有时开三桌。有上手打的,也有围观的,每个麻将摊周围都站了不少人。周围的人不光是看,还压钱。见哪个人手气好,就往人家面前压钱。人家若是赢了,压钱的人就跟着沾光,压下的钱就可以翻番。如果人家输了,压的钱就被别的赢家收走了。他们把麻将在桌面上磕得很响,嘴里还胡乱骂着,饭店里甚是热闹。打麻将的有男有女,其中不少人是宋春英的老乡,从口音上,让宋春英觉得亲切。从一定意义上讲,宋春英是冲着乡音去的。可今天还去不去打麻将呢?宋春英有些犹豫。要是她去打了麻将,那些参与打麻将的车倌儿到窑下又会乱说,赵焕民又会知道。她倒不是非要听从赵焕民的劝说,一个她雇佣的车倌儿,与她非亲非故,她听不听两可。可是她得承认,赵焕民的话确实有道理。她丈夫活着时,丈夫打麻将有些上瘾。那会儿,是她劝丈夫别打了,丈夫就是不听。为此,她和丈夫骂也骂过,打也打过,为了惩罚丈夫还不让丈夫上她的身,丈夫到底还是改不掉。现在的事情是,她成了成天打麻将的人,别人劝她不要再打,这算怎么回事呢?她对自己说,算了,不去打了。她在屋里转了转,心神还是有些不安。丈夫死了,儿子去县城上学不在家,她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呢?窑上没有学校,附近农村也没有学校,宋春英听了别人的介绍,只好把儿子送到县城的私立小学去上学。私立学校收费高,一个学期一千多块。为了儿子将来的前程,宋春英认了。窑上离学校几十里,儿子一上学就得住校,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晚上睡觉时还要妈妈搂着,拉个屎还要妈妈帮他擦屁股,现在却要一个人住校,吃喝拉撒睡,都是自个儿管自个儿,真是让人心疼。还有,校方每月向每个孩子收取的伙食费是一百三十元,而孩子能吃到一百元钱的东西就算不错。粮价菜价都那么高,孩子能吃到什么呢!她问过儿子,每天能不能吃饱。儿子说能吃饱。她问儿子几天拉一次屎。儿子说不知道。连几天拉一次屎都不知道,可见儿子是吃不饱。宋春英没办法,不能因为儿子吃不饱就不让儿子去上学。有人唱山歌,喉咙沙哑着,但调子很苍凉,唱得很好听。那人唱的是:黄连开花儿一肚肚苦,骡儿家的苦水跟谁吐;煤窑窑开花儿黑加黑,下辈子拴我脑袋也不来……宋春英赶紧从屋里出来,想听那人多唱会儿。那人唱着出了窑上的大门口,就不唱了。她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神儿,不知道赵焕民会不会唱这样的山歌。赵焕民既然会拆字,会解字,大概也会唱山歌吧。这天宋春英把自己管住了,到底没有去打麻将。她从床席下面翻出那只没有绣完的鞋垫,坐在门口一针一线绣起来。鞋垫是两只,丈夫活着时,她已经绣完了一只。鞋垫上的花样子是她从老家带来的,上面除了有喜鹊梅花,左右还各有一个字,一个是恩字,一个是爱字。这样的鞋垫当然是为丈夫绣的,左脚鞋垫的恩字刚绣完,丈夫就出事了,右脚鞋垫的爱字就没有接着绣。她想还是绣完吧,就算丈夫不能再用,权当寄托对丈夫的一份思念,权当打发时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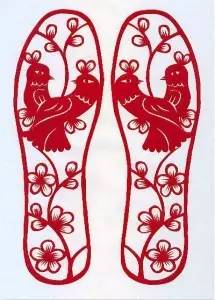 赵焕民再去宋春英家牵青骡儿,宋春英抓空子就问赵焕民,会不会唱山歌。
赵焕民问她什么山歌。
宋春英说,那个,就是那个,挺好听的,一听就让人想哭的那个。
赵焕民让她唱一句试试。
宋春英想了想,说她唱不了,只把听来的两句歌词念了一遍。
赵焕民笑了一下,样子像是有些不好意思,问,你听着这歌词好吗?
当然好了,这样的歌词把骡儿和窑哥们儿的心里话都唱出来了。
这都是我瞎编的。
宋春英大为惊奇,像不认识赵焕民一样瞪大眼睛问,真的,真是你编的?
编不好,瞎编。他随口又念了两句:天轮轮开花儿吱呀呀响,谁家的孩子不想娘;荞麦子开花儿愁连愁,哥哥你一去为啥不回个头。
宋春英眼圈红了一下,却笑着说,既然会编歌词,一定会唱了?
我不会唱,真的不会唱,我嗓子不行。我把歌词告诉别人,都是别人唱。
宋春英真正开始对赵焕民另眼相看,是她送儿子郎郎去上学的那天下午。郎郎一月回家一次,回家休息四天,接着再去一个月。郎郎去上学时,有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到窑上来接郎郎。面包车当然不是接郎郎一个,这个窑上有五个孩子在县城上学,都是搭这个车。来这个窑之前,面包车已去了两个窑,车里已塞进十一个孩子。宋春英本来说好跟郎郎一块儿去,去给郎郎交这个月的伙食费。一看车上实在挤不下了,宋春英就跟郎郎说她不去了,让郎郎跟老师说一下,她过两天再去。她把郎郎一个人十块钱的车费付给了开车的师傅。郎郎一听说妈妈不去了,眼里即时涌满了眼泪。郎郎没有哭出声,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那么在眼皮里包着。这真是一个本事,眼泪包得那么满,两眼都明汪汪的,却一滴都不掉下来。这时赵焕民从车旁路过,便把头探进车窗,往车里看了看。他看见了郎郎,也看见了郎郎眼里的两包眼泪。他每天到郎郎家牵骡儿,有时会看见郎郎,知道郎郎是一个心事很重的孩子。他想跟郎郎说句话,问一问,郎郎,郎郎你怎么了?话没问出口,他的眼睛也湿了。他的两个湿眼窝子被宋春英无意中看到了。他只顾看郎郎了,没有注意宋春英,宋春英却注意到他了。宋春英想起了赵焕民编的一句歌词,天轮轮开花儿吱呀呀响,谁家的孩子不想娘,这个孩子谁能说不包括郎郎呢!她心里一热,算是知道她的车倌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宋春英用一个搪瓷大茶缸蒸了半茶缸米饭,把炒好的鸡蛋压在米饭上头。为了保温,也是为了让饭菜保持干净,她给茶缸盖了盖儿不算,还在茶缸外面包了一个厚塑料袋,并用橡皮筋把袋口紧紧缚住。赵焕民又来牵青骡儿时,宋春英让他把饭菜也带上。
赵焕民说,嫂子,我在窑下不吃饭。
在窑下八九个钟头,饿着肚子对身体不好。你大哥活着时,我每天都给他带饭。
我已经习惯了,在窑下真的不吃饭,再说也没时间吃。
我叫你带,你就带,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啥子嘛!你放心,我不会扣你一分钱工资。
话说到这份儿上,赵焕民只好把饭菜接在手上。
下班后,赵焕民向宋春英送还空茶缸子时,顺便从窑口给宋春英扛去了一块煤,那块煤亮晶晶的,很大,没有八十斤,也有七十斤。虽说窑工和窑工家属烧煤都不花钱,赵焕民给她家扛去大煤,她就不必去捡装车时撒在地上的碎煤了。赵焕民说,嫂子做的饭真香!
宋春英说,香吧,我说让你带你还跟我客气呢,你个傻瓜!你要是吃着香,以后下了班自己就不用做饭了,我提前给你做好,你就在我这儿吃。
窑上没有澡塘,窑工们下了班,都是自己临时烧水,烧了水倒进盆子里,各自在宿舍里洗。赵焕民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才去嫂子那里吃饭。因他洗得细致,洗得慢,宋春英等的时间就长一些。终于有一天,宋春英对赵焕民说,以后我提前给你烧好水,你就来家里洗澡吧!说了这话,宋春英的脸很红。
赵焕民的脸比宋春英的脸还要红。
人心里头开花儿应该怎么唱呢?
插图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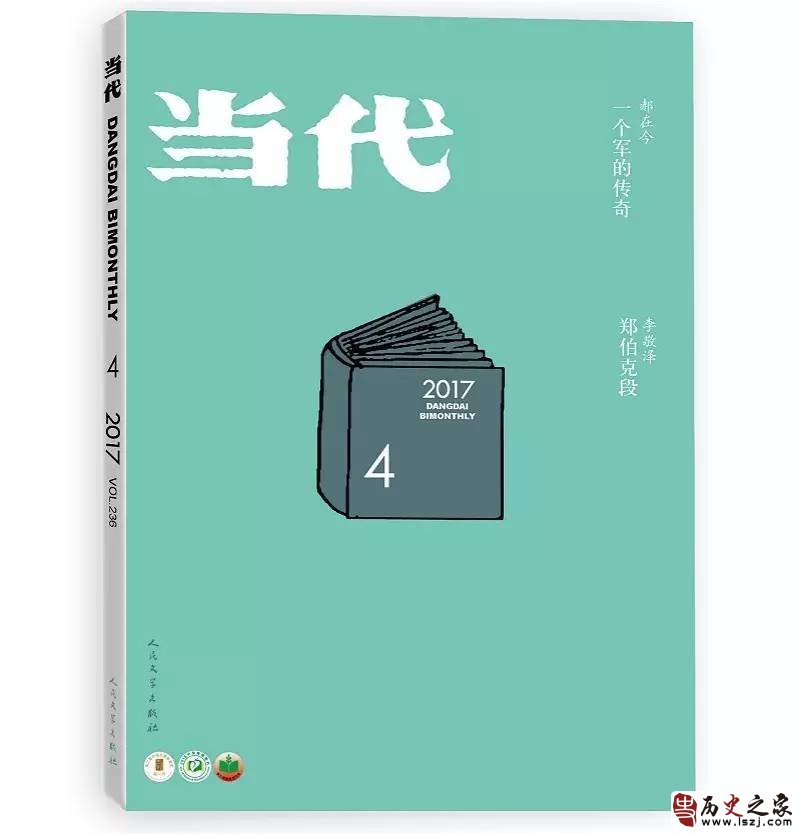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