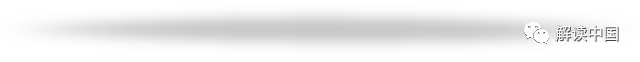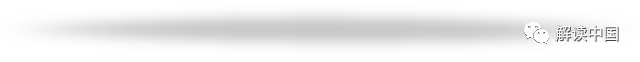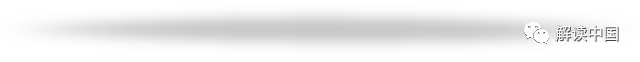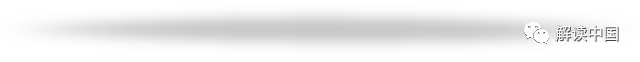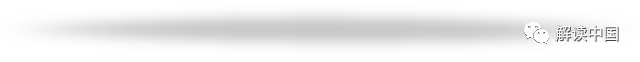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
宦读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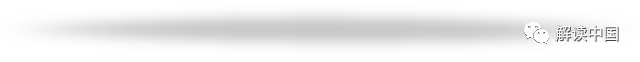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
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实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种复杂而危险的人际纠葛之中,往往是整日忧虑,满心烦恼;然而,官场却每有既能承担又能克服这种忧烦的高人,每有在这种忧烦之余清心问学的得道者。据说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氏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
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即可见出了他对于词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湛修养,令人玩味不已。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宾馆参观总统套间,可谓宝气珠光、豪华备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李书磊:没有传统的人生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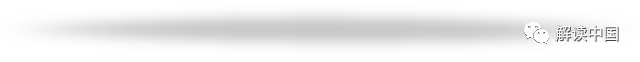 高晓春
记者:有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是从生产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的,广播里喊着你的小名,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你不相信,甩起羊鞭,冲着广播喊:别骗我,我不去。有这么回事儿吗?
李书磊:有点儿失真(笑)。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故事里说:你上小学时连跳两级?
李书磊: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记者:老师喜欢你吗?
李书磊:不喜欢,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同学们都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两拨儿小孩儿有时见了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都咳嗽。往往咳嗽末了就动起手来。我也参与,但不是主力,是出主意的。我出生的村子叫刘庵村,和我上学的破车庄一样,都在黄河滩上。
黄河出现在文章里往往很神圣,但小时候对我来说黄河就是我家门口的一条河,是我饮羊、洗澡、逮鱼和打水漂的地方。黄河有时发水,会淹死人;当然不发水的时候也淹死人。淹死人吓坏的只是爹娘,吓不坏小孩儿。各家的父母用粉笔在小孩儿的背上画上圈儿防备他下水,但这也好对付得很,等凫完水再让同伴用粉笔将圈儿画上。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让我妈省心的,我属于小孩儿里的文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过日子受穷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儿也不知道作难。最愉快的还是自己看书。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
记者:你14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读硕士、博士。在北大的这十年里,一定有不少热闹的事情发生吧?
李书磊: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在北大读本科,同班同学教会我很多东西。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到班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我的同屋有一位河南同乡叫赵建庄,他甚至还在中国北方流浪过几年。因为得罪了大队书记,书记准备把他抓起来斗争,他闻讯出走,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小工糊口,也算是开了当代民工流动的先河。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行装是一部《红楼梦》。有一次他睡在唐山火车站的广场上被警察半夜踢醒,搜他的行装,搜出一套《红楼梦》,警察就说你接着睡吧,看你读这样的书也不会是坏人。赵建庄五大三粗,是个壮汉,能如此沉迷于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异数。
他自己也写诗,是楼梯式的,有一首开头是“我/白杨/高高生长/邙山上!”我还看过他在流浪途中写的一首词,是言志的,结尾是“何时杀尽害民贼,于国于家无愧”。可以看出他没有太多文才,但是条好汉。他后来改学了法律,大概是要圆“杀害民贼”的梦。再后来他去了美国当律师。同班同学既是各路神仙,他们之间难免有明争暗斗,但他们对我都很爱护、很教导;他们之间也谈恋爱,甚至已经结婚的人也有些秘密的爱情,毕业很多年后我才吃惊地听说原来谁和谁还有一手。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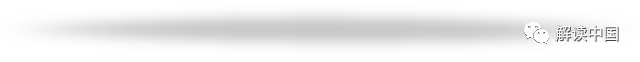 记者: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那些年,你却每日与古书为伴,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李书磊: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其实,重读古典的最初动因就是一种情感需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经历批林批孔,批孔,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批评,我们又重新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立场。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批判中国古典中度过的。但这个东西有些奇怪,你越是批判她,你和她的渊源就越深,了解也越深,感情也越深。实际上,当我们真正作情感选择的时候,她就成了我们的寄托。
记者:在别人眼里,你是位学有成就的学者,那么,你为什么总说自己时不时会陷入一种惶惑?
李书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人过了30岁,日子也随着年龄一道急速地奔驰而去,紧迫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想,人一辈子也就活到80岁吧,我已经过了几乎一半了,而且最后的一段,会衰老到不堪的程度,真正的壮年已经没有几年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希望的——能写出一两部传世之作,也还离得挺远。我心慌了,这种心慌,这种紧迫感和半生过去事业未成的惶惑,拧在一起,时时缠绕着。
记者:你已经写了九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是不是对你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
李书磊:可以这么看吧。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从放羊娃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再到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的人生经历,既简单又精彩。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有不少感受吧?
李书磊: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我算是幸运的——能赶上高考的机会,能考上北大。在此之前,到县文化馆做临时工,就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经过那么艰辛的打拼,没有被选择出来,没有被社会接纳;还有许多人,走了那么多坎坷的道路,好不容易拼出个天地来了,又被“双规”了。这样的事儿,你看多了,对人生就有理解力了,对他人也就会有同情心了。
人的觉悟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经验世界和精神能力都是无限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魅力。明朝的徐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就是说,你要想一段时期内不受苦,也没有烦恼,全是高兴事儿,那不可能,所以有高兴的事儿就赶紧高兴。下联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痛苦的人实在是痛苦不堪,而且看不到尽头,然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受苦的人,因为还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呢。
在逆境中寻找乐趣,哪怕是纯粹受苦,你也应把它当作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它能让人更达观,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
我为青年喝彩,我为青年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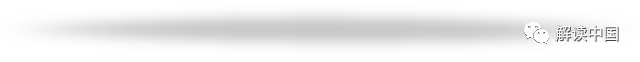 记者:你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对于文化的变迁,你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李书磊: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其实一直经历着文化变迁。梁启超、鲁迅,他们经历过这种变迁,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变迁。从经历变迁的这种命运上看,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和前人大不一样了,我们更复杂,也更惶惑。比如,对于现代的态度,鲁迅是一心求新的,在抛弃传统、追随现代这个立场上,他非常坚定,也义无反顾。
今天,我们也在追随现代,对现代性的认可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较之从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困惑、犹疑和内心矛盾。比如,现代生活方式过分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尤其是被对物欲的无限追求所左右,文化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对于此,我感到不适,感到忧虑。
我的另外一个忧虑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暴力倾向。这件事说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研究现代化史的人,他们对现代性和力的关联是认识得非常清醒的。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给毁灭性战争提供了条件,而现代文明的约束力量又不足以规范、制约、驯化人的暴力冲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胸怀利器,杀心自起”。“9.11”及其带来的冲突就是一例。无论是恐怖主义表现出的那种残忍,还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暴力征服欲,都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更引起了我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和忧虑。
记者:这一代青年人也同样经历着文化变迁,这个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书磊:当然体现为文化的代际更替。最近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巨大的能量和引导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信息化以来,几乎所有的最有前途的新兴行业,年轻的一代都成了它们的骨干。原来的那种由老年人主导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年轻人主导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这么年轻的人,掌握这么多的财富,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我看过一些父辈写的文章,他们特别崇拜自己的子女,完全在文化上投降了。在我的身边,我也看到儿子、孙子挣的钱比老子的多几倍、十几倍。年轻人掌握核心技术,这有利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他们与传统没有很深的过从,他们与人类文明伟大的传统相疏离,也不知道他们能把社会引领到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社会有主导力量,也应该有校正的力量,并且,最好能形成合力,这样,社会就比较健康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
李书磊: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崇尚、趣味与目标,与更年轻的一茬人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会受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影响他们。我们当然要理解、顺应时代潮流,但我们也很难去趋奉时尚。趋奉时尚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最好是各行其是。
记者:你刚才说到传统,你觉得传统在今天意义何在?
李书磊:伟大的传统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智慧,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佑护力量。在今天文明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我们格外念起传统的可贵。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传统,包括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重温来亲近传统,一方面也通过新的文化创造来延续传统,让传统在当代的人群中复活,成为今天生活的组成部分。
伟大的传统会使我们内心丰富起来,强大起来,使我们有所敬畏,不轻妄,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和质量。对传统的集体性遗忘是危险的,所以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年轻的一代解说经典,解说传统,用他们能够理解、喜爱的方式展示经典及其精神的魅力。
乐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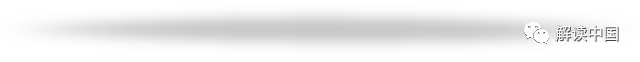 李书磊
读书改变人生,却往往很难说是哪一本。当然某一本书也会对人生作用非凡,特别是经典,“辛苦遭逢起一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古今相同,但更经常塑造人生的还是持续不断的广泛阅读,是不同年龄、不同境遇下的随缘涉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博览群书中反省经验、变换气质。所以古人特别主张“读万卷书”,主张“饱读”。
不仅是读闲书才有乐趣,读有用的书也会意趣盎然。其实只要心志开阔,有对万事万物浓厚的兴趣,读“闲书”也会很有用,读“有用的书”也可以不离性情。马克思的文字汪洋恣肆,恩格斯平实深厚,列宁神采飞扬,他们的理论都是可击节浮白的好文章。
我还记得上初二时读《列宁选集》欣喜若狂的心情,列宁那种再三下定语的句式,那种极而言之的语气,那种斩钉截铁的设论,都使我羡赞不已。当时是在油灯下朗读列宁的文章,觉得这样的大好文章不朗读不足以表达热爱的心情。后来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论课,读到“元气淋漓”这个词,我一下子就联想起了列宁的文章。
马克思的文章洋溢着一个伟大“先知”的豪迈,他的思辨与逻辑更血肉饱满。我其实特别喜欢封面是黑底红字的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版本的译笔很放得开,译得情采跳跃,我觉得是深得马克思的笔意。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房门口的书架上,有时进书房随手抽一本来到书桌前,随便翻开读上几页,都会多有新得,感到莫大的满足。这套老书翻开来纸色黯淡,也觉格外亲切。
我曾向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建议,修改马恩著作的译文可否设定“能不改就不改”的原则,特别是对大家耳熟能详、出口可诵的语句,如果不是意思真错了,最好是不要改,可此可彼的译文最好是仍旧,不要轻作无谓的字词改动。改动那些早已入脑人心的警句真是让人痛惜,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稳定性。而且最好要特别注意保留马克思的文采、文气,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不应是放在图书馆备查的文献,而应是在人间流布的火种,有文方可行远。我作此建议的心情特别强烈。
中国的古书读来则很有亲近感。古书既是母语,也是“语母”:今天用的字能在古书中找到真切的出处,有时意思略同而又有微妙出入,一下子增加了对这个字的理解,有悠然心会之喜,这个字以后再看见也有了新的色彩。写文章时会不自觉地化用一个字词的古义,让现代汉语的文章中透出些异样的气氛,感到很自得,也算是对古人.种新的发扬吧。
古书中的字词有时特别入骨,状述一个情景、一种情态特别贴切、准确,让人怦然心惊,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用词则常常涣散无力,达意而已,说不上传神。重温古人遣词让我们对母语有新的觉悟,于现代生活的匆忙中体会到古人的细察深思,也意识到我们守护语言的责任,应该经常淬火保持字词的锋利。
读古书也是件轻松的事。古代的经史也不是高头讲章,多是故事,很好读。《论语》是一部回忆录,有情节,有场面,生动得很,所以孔子的话就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人心里去。学生记孔子言行也不搞“三突出”,很家常,仿佛是无心记下的见闻,一时不是很高大的形象也都不省略。“子见南子,子路不悦”,估计是嘀咕了一些难听的话,孔子脸上就挂不住了,赌咒发誓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否则“天厌之”。
这一个细节就让我感到《论语》是可信的,对孔子那些听来调子很高的夸奖大概也是写实的。《论语》笔调,平和自然,悠哉悠哉,一读就读进去了,两千多年之后也好像是在从夫子游,变成了他的学生。我是当年批林批孔时开始读《论语》的,那时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从这样的本子入门肯定不会有对孔子的神化问题。惟其不神化才更能得其真义,才更能秉持素心体会其价值。那时都称孔子为“孔老二”;现在平心而论,“孔老二”虽然不敬但也不恶,不像称林彪为“林贼”那样狠,也使圣人有了些烟火气,不隔膜。
《论语》还有个好处是一条一条地不连贯,这样随手翻开就能读下去,没有非得正襟危坐的压力。《孟子》可以说是一部游记,写孟子到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当然主要是说了什么话、怎么说的。孟子说话很冲,滔滔不绝,是用食指点着人说话的样子,语调昂扬。他把一套道理说得很完整,算是有点理论性了,但因为语气充沛也不觉得枯燥。
孔子对学生说话也大都和颜悦色,孟子对国王说话却经常疾言厉色,显得很可爱。孟子周游可以说是谋职也可以说是跑官,拔高点说是为了“行道”,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求于人,他却仍然用这样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语气,可见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真的。《孟子》有青春气,少年时代读有同怀之感,现在读则有对少年的羡叹。本应是古人为老,我辈为少,但有时情景恰恰反转过来;从古人处汲取得少年精神,也是读古书的一种奇缘。
虽说经史难分,但读史还是有读论孟所难有的体验。中国古史记载的多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将相,他们其实与孔、孟这样总是候补的士大夫看问题角度有别,行事也不同。史书记载的事更真实、更残酷无情,更反映惨淡的人生,也更能反映惨淡人生中的英雄与圣贤,是实践着的善恶,比单纯口说心怀的善恶更结实。大学时代读《通鉴纪事本末》,常感觉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事件往往是沉痛的悲剧,事件的展开又环环相扣、密实压抑,真有“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慨伤。
后来读《资治通鉴》本文就缓和了不少,一个大事件中又夹杂着许多不甚相关的小事情,可以冲淡一些,换换心情。今天说起“案例教学”我总想起《资治通鉴》,每一页都是大大小小的案例,一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当事人是什么态度,是怎样应对的,结果如何,都很完整,作政治训练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我有时想这书取名叫“鉴”,比作镜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以史为鉴”是老生常谈,但真正细想起来还是感叹比喻得真是好。
读史难免是把自己放到里边的,读到险恶而内心悸栗,读到忠直而肃然起敬,参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非“鉴”而何。纪传体史书要更活泼一些,不是以国家而是以个人为传主,有个人的命运,有更丰富的喜怒哀乐,更鲜明的面容。
读史决不仅仅是学得经验,还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增进觉悟。说读史是修身一途,也不仅仅是指阅读中内心激浊扬清的是非判别,还指的是心智与境界的扩展。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高亨写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或许只有“掌上千秋史”,胸中才能有百万兵。
日常读史会感到心胸开阔,放眼一千年、两千年的历史,不禁豁然开朗,身边的些小恩怨还算得了什么。读史也加深我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了解,祖国每一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关系我心。自将磨洗认前朝,牧童拾得旧刀枪,茂密庄稼、新起楼群下的土地曾经历无数故事,步行走过生出无限的珍惜之情。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祖国的历史,我们就是古人预言和期待中的人物,在履践并修正着从前的因果,我们要在今天的四海风云中把祖国引向光明。
古人说“右史”“左图”,其实不仅仅历史,所有的学问都与地理相关。读地理著作别有喜悦,“游记”、“风土记”、“岁时记”,但看书名就让人心驰神往。《徐霞客游记》我有两个版本,一是上海古籍社的增订本,一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民国时期丁文江编本,都字大行疏,无事读来特别休闲,徐霞客笔下的山川古道、桃花杨柳,仿佛就在我眼前伸展。地方史志也可以看做是地理文献,出差到陌生地方,夜晚在旅馆的灯下读当地的志书,挥笔圈点,也觉得乐莫大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