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 有学者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但是,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其身价大为提升。 主张放开鸦片贸易的许乃济,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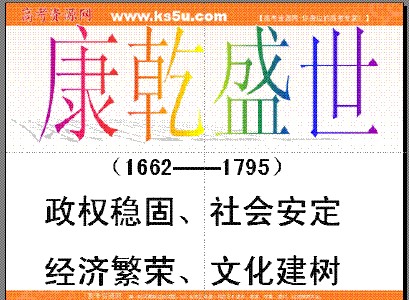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尽管皇帝会查禁这种贸易,并也会一再严旨重申禁令;尽管总督会恪遵上谕发布告示,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也会传谕行商慎遵法令;但是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提督、知县以及再往下到那些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小人物们,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对于法令的不断破坏也就熟视无睹了。他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除了从广州的“公所基金”、澳门的“行贿基金”等处间接受益外,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受益。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以缉私为名而从鸦片中分润的,上至副将、守备,下至普通士兵。拿获鸦片之后,他们要么“私卖分赃”,要么“得胜放纵”。 到1826年,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元人民币)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在猫鼠同盟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专以护私渔利,与南洋船约,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报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紊,而鸦片(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水师收入“得自粮钠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禁烟造成关税停征,但是却被贿赂代替,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用不着说,帝国官吏是贪污的;在违禁品的征课上,他们所干的,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在干着的那种勾当,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以备不时之需。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一等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把行商和“公行”推向第一线,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