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遇上的落差 乾隆朝,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虽为主持盐政的大吏,却有着很好的文艺素养,在任时以爱才好士著称,幕府宾客众多,极一时之盛。郑板桥以怪著称,不仅书画风格怪异,而且为人处世不攀附权贵、傲骨铮铮。而卢见曾却与郑板桥交往密切,甚至有至死不渝的友情,两人诗文集中互有反映。板桥从三十一岁来扬,度过了大约十年的卖画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穷愁潦倒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父亲穷困而死,儿子随后夭折,卖画无人赏识,境遇之惨,几乎把板桥逼上绝路。板桥把这段时间自喻为:“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郑板桥集·诗抄·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讳敏中(一)》)。他31岁至40岁期间主要落脚地是在扬州,卢见曾不仅给予他物质上的资助,还与他建立了一种超越主宾的挚友关系。落魄扬州的郑板桥对卢见曾抱着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卢见曾招揽郑板桥的举动也具有特别的文化道德关怀。 尚小明的《清代士人游幕表》载:“郑板桥1736年顺天学政崔纪邀入幕,又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扬州画舫录》卷十载:“郑燮……往来扬州,有二十年前旧板桥印章,与公(卢见曾)唱和甚多。”乾隆四年(1739),郑燮作《送都转运卢公》诗四首赠之,奉呈雅雨山人卢老先生老宪台,兼求教诲,板桥自称后学郑燮。其时板桥四十七岁,卢见曾也不过年方五十,板桥称雅雨为老先生、老宪台,而自称为后学,可见郑对卢敬之耳。此年十一月五日,板桥还手书了李葂所作之《题雅雨夫子借书图》中的一首诗“旋假旋归刻未闲……”,此时卢见曾已是戴罪之身,前途未卜,而板桥依然如此,非卢公之知交挚友不能也。次年,卢见曾戴罪赴边、远谪塞外,郑板桥为高凤翰等人所绘之《卢见曾出塞图》题长诗一首,其诗长达二百余字,慨慷激昂,直抒心意,颂扬卢有杜甫韩愈之才,“磊落胸中万卷书,文章政绩两殊绝”,可谓是“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待到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时,两人皆已步入晚年,时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板桥65岁,卢见曾亦已68岁。是年,卢于扬州虹桥修禊,郑亦应邀顶其雅集,并作《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四首、《再和卢雅雨四首》,雅兴无前。卢见曾对郑板桥亦备加推重,他在复官不久写的《扬州杂诗》十二首中,第一首即是颂郑板桥:“一代清华盛事饶,冶春高宴各分镳。风流间歇烟花在,又见诗人郑板桥。”《扬州画舫录》卷十五载,卢见曾衙署之“苏亭”,其额即为板桥所书。板桥还为卢见曾改建的祀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的“三贤祠”撰写碑文:“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足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彼此相重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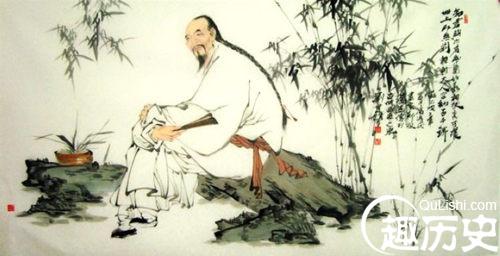 当时出入卢见曾府署中的知名学者文士甚多,除了郑板桥外,也有吴敬梓。吴敬梓在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诗的最后一句“蔽芾甘棠勿剪伐”,以“甘棠遗爱”的故事称颂有德政、泽及人民的地方官员卢见曾,不仅切合他们的关系,而且他本人也感同身受。吴敬梓早年出游淮扬,就曾得到卢见曾的资助。当乾隆“十九年卢见曾还任两淮盐运使”时,吴与卢原有旧谊,因而再度来扬拜访卢见曾。但吴敬梓是一位寒儒,地位并不十分突出,虽能经常出入于卢雅雨“大公祖”幕中,但却自行住在邻近徐凝门一带、后土祠(琼花观)附近的族人吴楷(字一山)家中。在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上,治晚生吴敬梓的题诗亦在图的绫圈右下端,已被从原图中割截另行装裱。卢见曾没有特别看重他,吴感到于世不用,叹息“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感慨“谁识王明,斋钟愧阇黎”,常有被冷落的苦恼。吴敬梓一生贫穷,写作《儒林外史》亦多凭卢见曾、程晋芳等人的支持。吴敬梓死后,卢见曾亦慷慨解囊,买棺装殓,并且安顿好吴敬梓的妻儿老小。卢见曾的爱才好士深得时人赞许和后人褒扬。 吴敬梓与郑板桥虽同为卢见曾的幕宾,吴并没有郑幸运,被奉为上宾。加之他沾染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经济头脑又不及郑板桥,在父病逝后过着挥霍的浪子生活,“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子弟戒”无疑是乡里将他看作一个败家子式的反面教材了。他应科举时,也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不得不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郑、吴两人境遇上的落差,是导致他们俩不相往来的重要原因。 对待科举及官场态度的不同 吴敬梓出生在“家声科第从来美”的仕宦名门,他的曾祖是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自他的父亲起家道衰落。吴早年对祖上得益于科举制度,也曾引以为豪,他从安徽全椒刚迁到南京时,写过一篇《移家赋》,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他的一生变化极大,由富入贫,大半时间消磨在宁、扬两地,他对于科举考试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追求、失望到冷淡、憎恶的发展过程。从与“上层人士”的交往及接触中,愤慨地看到官场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一落千丈,因而对社会百态及官场黑暗以及科举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功名富贵表达了与常人截然不同的看法。雍、乾年间,清朝统治者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以理学为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他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他的《儒林外史》,被誉为含着热泪控诉科举功名毒害读书人的救世之书,显示出他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展露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而郑板桥生于一个寒儒家庭,其父郑立庵是一位“私塾先生”。板桥出生时,兴化连年遭灾,生活困苦不堪。板桥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艰苦与辛酸中度过的。板桥30岁时,父亲立庵病故,家无长物,卖书葬父,锅中无米,灶间无柴,可门前还不断有人来逼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板桥曾逃到海陵、镇江焦山躲债。贫寒的家境,凄苦的身世,不幸的遭遇,促使板桥发愤改变命运,走“读书——科举——作官”的发达之路是他心中孜孜以求的梦想。他多次对朋友表白:“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与江宾谷、江禹九书》)板桥在《焦山读书复墨书》和《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两书中皆告诫舍弟郑墨:“愚兄既不能执御执射,又不能务农务商,则救贫之策只有读书。”“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并一再叮嘱:“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他是不屑于做一个乡下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的,“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此种心迹流露无遗。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两代,以制艺取士,其僵化腐朽、摧残人性的一面日益显现出来,造成了不少人生悲剧。板桥读书应试自有他的路数,他主张不要死读书、读死书,万不可“为古人所束缚”,所有史书“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所有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材”,他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这是板桥不同于一般腐儒的高明之处。板桥大半生专心致志于科举,竭力突入统治阶层,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和束缚。在此过程中他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封建社会传统文人并无二致,其身上具有的新旧思想杂陈、进步与落后因素并存的现象,可算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历史嬗变过程中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