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记忆”超越时空,它让我们尝试着用心灵倾听,与历史对话,捕捉已逝去的声音,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碎片中再临历史现场的鲜活,有幸发现历史更深刻的一面。“记忆”还能让人们反思心灵,重获活力。  舒衡哲(Vera Schwarcz),生于罗马尼亚,中国史研究学者、诗人。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五四运动史和犹太史研究。现任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Freeman Chair Professor)。曾获古根汉基金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1979—1980年,她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了历史研究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著有8本专著和5本诗集,包括获奖的《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张申府访谈录》(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鸣鹤园》(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诗集包括《记忆之园》(In the Garden of Memory)、《园林短憩》(Brief Rest in the Garden of Flourishing Grace)、《记忆之凿》(Chisel of Remembrance)、《灵》(Ancestral Intelligence: Improvisations and Logographs)。  在时隔60年后的1979年,中国开始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幸存者也开始陈述往事,把对“五四”的记忆留给后人。也就在这一年,当时已研究了10年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舒衡哲也终于来到中国大陆,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倾听步入暮年的“五四”一代的声音,开辟了她“五四”研究的新路径。 她是一位睿智的学者,是一位情感充沛的诗人,更是一位善于聆听的人。对沉默的倾听,对弦外之音的感悟,使她的“五四”研究独具一格。在采访中,她告诉记者,30多年来让她一直铭记在心的,是“五四”一代在讲完那段过往之后陷入的沉默,其力量甚于语言。 1 倾听“五四”一代的回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从1969年就开始研究五四运动,当时是什么吸引了你? 舒衡哲:20世纪60年代末,我开始研究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从共产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的人,我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潜力一直以来都非常着迷。1969年大学毕业后,我突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而周策纵先生关于“五四”的书带给我灵感,五四运动激进的政治寓意吸引了我。 虽然那时我还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但我已经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五四运动。在我当时年少天真的理解中,“五四”似乎“证明”了让-保罗·萨特 (Jean Paul Sartre)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所有左派理论。在斯坦福大学写的有关中国史的博士论文中,我也大量引用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时隔10年后你再一次来到中国大陆,这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舒衡哲:刚开始研究“五四”时,我太过理想化,而且总是把老师告诉我的关于胡适等人的故事信以为真。1979—1980年,当我终于到北大学习的时候,我开始走访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已是“中国史教授”,但我对中国的理解还很抽象,因为我只在1977年到过一次中国,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文革”的幸存者。从张申府、梁漱溟、叶圣陶、俞平伯、冯友兰、周扬以及其他思想家那里,我亲耳听到他们对各种思想、知识分子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战争革命年代在中国推行“启蒙运动”的叙述。我最初那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因此变得更冷静、更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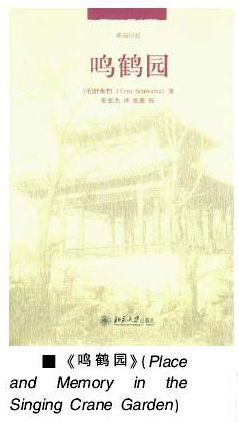 2 “记忆”超越时空 再现历史的鲜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的研究以“记忆”为主,在特殊年代,你是如何叩开紧锁的大门,设法获得这些珍贵的“记忆”的? 舒衡哲:我来到并住在中国大陆,这个决定很快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值得去做的。这一切始于为“五四”研究做一些采访。拜访“五四”一代幸存者的步伐走得很缓慢。刚开始,在一个处处受限的特殊社会环境里,“五四”话题依然敏感,因此,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礼貌地谢绝参与一些研讨会,只能徘徊在外。然而,在北大学习与生活期间,我却有机会与经历“五四”的人接触。随着与他们友谊的渐渐深厚,且我的汉语不断进步可以让聊天顺畅起来,我们彼此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我最终得以叩开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门,到他们家中聊天,他们也开始敞开心扉地与我谈话。 张申府成为我口述历史项目的首位采访对象,随后,我还有机会采访了冯友兰、朱光潜、叶圣陶、许德珩、梁漱溟,和郑振铎、顾颉刚以及朱自清的孩子们。 我深深感受到,这些直面困境的个体,曾渴望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然而这种渴望却遭受了现实的无情扫荡。他们的回忆和对现场细节的再现,让我的研究开始离开大段大段的理论,让我冷静下来去聆听,聆听个体零碎回忆背后的真相,聆听不同于书面材料的鲜活的口述历史。我也体会到,这些年迈的中国知识界幸存者在与我谈话时,怀有一种不寻常的热情和开放的态度。这不单单因为我能用流利的中文与他们交流,还因为我的成长经历,使我们能相互理解。正如张岱年教授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所说的:“因为你是犹太人。你更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你们的民族也同样遭受苦难。咱们是知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口述历史有其形式上独有的特点,记录“记忆”为你的研究带来了什么? 舒衡哲:“记忆”让我拨开书面材料和理论知识,有机会窥探到个体直面的历史真相,让我对历史的分析更加冷静。记忆的主题,包括个人的和文化的,不断在我的研究中出现。在写完《中国启蒙运动》10年后,我写了《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一书,以填补犹太文化记忆与中国文化记忆之间的个人和历史联系,同时也是为了回应张岱年教授的启示。还有我的一本个人诗集《记忆之凿》,也是对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间个人与历史的探寻。 甚至在我上一本书《鸣鹤园》中,也回到“记忆”这一主题。当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19世纪花园的门口时,记忆便不断涌现。我再次尝试聆听,聆听已经被人遗忘的堆满了记忆碎片与哀鸣的某个角落发出的声音。口述史、思想史和园林史指引我们去倾听“那些已经无法开口说话的人们发出的嘶哑的声音”,帮助我们掀开了鸣鹤园曲折的历史赋予这所花园的特殊寓意,成为反映历史和语言的载体,娓娓道出了记忆和废墟如何通过个体和文化实现其精神上的复活。 长期以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始终相信学习过去、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碎片中厘清头绪,能够丰富我们自己。我们始终无法圆满捕捉或传达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历史教导我们全新认识已发现的碎片,这是学习历史的魅力。“记忆”超越时空,它让我们尝试着用心灵倾听,与历史对话,捕捉已逝去的声音,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碎片中再临历史现场的鲜活,有幸发现历史更深刻的一面。“记忆”还能让人们反思心灵,重获活力。 3 领悟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过这么多年来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舒衡哲:当我刚开始研究“五四”时,我还太过理想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攻克传统壁垒中扮演的角色还持乐观态度。1973年我到台湾地区访问学习,那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湾,阅读关于新文化运动(1916—1921年)思想先锋(例如鲁迅和陈独秀)的著作是闯入“禁区”的冒险行为。后来,当我开始对中国大陆步入暮年的知识分子采访时,我听到了他们在探索道路上遇到的困境。他们对过往的回忆,让我开始领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命运。 1979—1985年,“五四”一代一直是我研究的中心议题。后来,我想转到其他主题上去,但我的中国朋友一直坚持说,关注“五四”未竟的遗产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一次次回到中国,参加1999年和2009年的“五四”纪念活动。当我1979年开始对五四运动开展访谈时,1919年的那场运动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它涉及小心谨慎地重新评价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现在,它已经变得不那么“敏感”,但重要性不减当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继续在热烈地讨论启蒙。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比较? 舒衡哲:今天,当我们回首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回首当时知识分子的那份自信时,看到的是他们陶醉在人类智慧中,看到的是他们因蔑视阳光背后的阴影而迷失。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挑战传统思想,出于对新世界观的渴望,出于解脱旧制度的理想,他们探索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而正是这些思想在最后最直接地导致了中国革命的爆发。不同于法国哲学家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推动者在赞扬人类理性的进步时,仍深刻铭记着阳光背后的影子和黑暗。 欧洲的启蒙与中国的启蒙有天壤之别。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对历史的强力浓缩。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革命年代,走过了200多年。而在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很快的速度吸收着新思想、梦想和愿景,然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进行社会革命。时至今日,那些思想和理想依然重要,而在欧洲,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要少得多。不像中国,西方学者的所思所为与民众整体并无太大关系。 4 追寻中国大学者的脚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有着多重身份,同时担当五四运动研究者、作家和诗人三重角色,在你看来,这些角色彼此间是如何相得益彰的? 舒衡哲:对我而言,诗歌和历史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我写诗、写历史,也教诗、教历史。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文史也不分家。所以我感觉是在笨拙地追寻中国大学者的脚步。我也发现(尤其是“9·11”事件爆发时,我正任维思里安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我周遭所听到的媒体和学界喋喋不休的评论相比,诗歌对历史创伤的反应更有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有什么新动向? 舒衡哲:我刚完成两部新著,它们还需进一步修改:一本是诗集,名为《灵》。该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是根据陈寅恪的人生和著作而写,陈寅恪是影响了我很多年的一位历史学家和诗人;后半部收集的是为专门赞颂单个汉字而作的诗(如以一个汉字开头,后面的句子围绕汉字本身进行抒情创作),它代表了我对历史创伤期微妙语言的重要性的个人冥想。它是我10年研究的反思的汇集,是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黑暗时代群像》(On G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的反思。 一开始,我只是在知识海洋岸边浅探浪花,这一知识海洋围绕着在中国被熟知的杰出知识分子。逐渐地,我发现自己与在“文革”中经历苦难的知识分子融合。然而,直到开始写这些诗之前,我却始终无法传达“语言本身的遭遇与荣耀”的动情力(pathos)。正是在我收集由单个汉字组成的诗时,陈寅恪著作中蕴含的深厚的历史引导我探寻中国文字更古老形式的词源学,并试着向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传递一些新的东西。 “语言作为一种救生筏”也是我另一本新书《真诚本色》(Colors of Veracity: A Quest for Truth in China, and Beyond,2014年将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核心思想。虽然这本书关注的是在历史创伤期真理的重要性,但我自觉地想用一种不同于其他历史哲学书的方式来写。我想写的是一本简短、生动、个性和巧妙的书。它也将我的中国研究与许多有关犹太对真理的定义的新理解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维思里安大学的东亚研究在同行中备受赞誉,你多年担任东亚系主任且培养了很多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在这样的经历中,你如何评价中国研究在美国年轻一代中的发展? 舒衡哲:我已在维思里安大学教了近40年书。刚开始的时候,我仅为维思里安大学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开一门课。而如今,我许多最好的学生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他们都很优秀,都在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年轻时在自己国内学过的那些问题和事件。他们对真理追求的如饥似渴激励和指导着我自己的工作。 链接:诗人历史学者舒衡哲:用诗化的言语抒写历史 舒衡哲是一名历史学家,也是一名诗人。在她的作品中,文字的平叙和诗歌的抒情相得益彰。例如,在《鸣鹤园》一书中,舒衡哲在描写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历史时,多次借用诗化的言语。她写道:“面对曾经的创伤,诗歌的帮助比较大。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o poetry after Auschwitz)。在饱受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创伤后,他认为任何语言形式的倾诉都已苍白无力了。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诗歌是一种最为合适的语言形式。较于学术语言,诗歌这种浓缩的语言形式有时能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更好地叙述真实。” 评论者对舒衡哲这本诗集中激动人心地将情感、智慧和历史视角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大加赞赏。美国诗人山姆·汉米尔(Sam Hamill)如此写道,“这些表面看似简单、直接的诗在深层内涵上却是‘有机’的,它深深扎根于犹太、中国以及其他古代传统中,并且就像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时深呼吸一般自然地伸展。读之,令人无比愉悦。” 另一位诗人查尔斯·费雪汶(Charles Adés Fishman)补充道,“舒衡哲的词语真真是如椽大笔,揭示和表明其所爱、所祝、所哀、所望。在《记忆之凿》这本诗集中,过去没有隐退至被遗忘的历史领域,而是奔突至今。在这本充满入世感和优美感的诗集中,舒衡哲挥舞‘记忆之凿’,巧妙地循着神圣、必要和永恒的道路前行”。 二战期间的英国军官、后成为一名作家和旅行家的斯坦利·莫斯上尉(Captain Stanley Moss)也称赞舒衡哲的作品是“词语经极妙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诗,同时又受英文、中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德文和希伯来文,以及犹太宗教传统的综合影响。她的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诗歌,以及诗歌所传递的深恶痛绝的磨难与痛苦,也教导着我们对自然的深深的爱,以及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追求的简单的快乐”。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