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庶昌故居内雕像  黎庶昌故居 李贵云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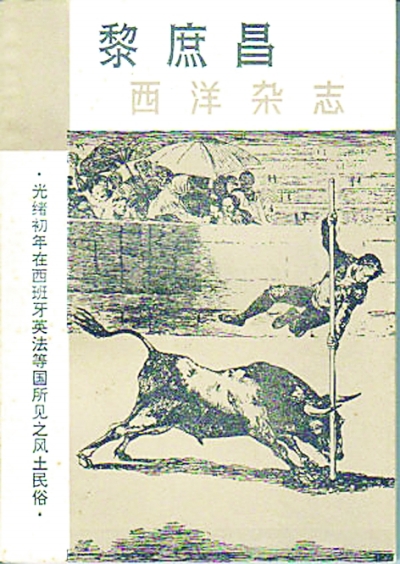 1878年,黎庶昌作为清政府驻法公使参赞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他将此行的所见所闻记载于其《西洋杂志》中。该书于1900年刊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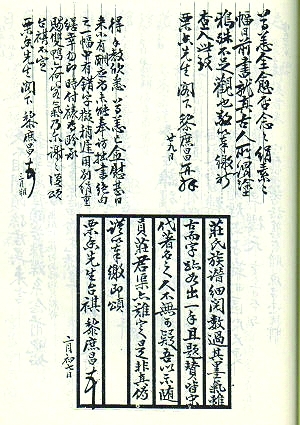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黎庶昌手札。1881年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两度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 作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作为一名从西方盗火的知识分子,黎庶昌在走向世界的行旅中,获了别样的文化眼光:他固然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但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他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他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 我们去凭吊位先贤。车在遵义近郊的沙滩村停下,路边有庭院两进,前带清流,后枕山峦。正房屋檐下一黑漆竖匾,“钦使第”三个字灵动飘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火凤凰,为古旧的宅邸衔来几片沧桑。这里,就是一代先贤黎庶昌的人生起点,也是这位贵州好汉的人生归宿。 一 秋风已至。京城一间民宅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后生推开窗户,凝望片刻,头一甩,脑后的长辫划出一道弧线,“啪”的一声缠在脖子上。他踌躇多日,终于下决心回到案前,写下开头: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诏书…… 他就是黎庶昌,时年26岁。两次乡试不中,一贫如洗,滞留京师已走投无路。 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太平天国正与清廷激战,英法联军不久前攻陷了北京。后又天呈异象:太阳三晕,流星南奔;七月间更有陨石雨和彗星划破苍茫天际。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控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担心这是“危亡倾覆”的征兆,为消灾弥变,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言”。黎庶昌毅然上书,洋洋七千余言,雄视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谓。如此闭塞之地,为何走出了腹隐珠玑、蔑视天颜的黎庶昌? 此时,我就伫立在黎庶昌沙滩故居的老屋中。 青砖铺地,横木成梁;一张圆桌,两把座椅;靠墙有六尺卧榻,四周挂着白纱帷幔。黎庶昌别妻辞子,就是跨出这间房子,一路翻山越岭赴京城应考。生他养他的沙滩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圆不过数里,渔樵耕读,延绵不绝。其间,出了几十位贤士,著书百种,内容涉及经史、诗文诸多领域。其代表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他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过这位才学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读古人之书,十七八岁时便立下志向:“以瑰丽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时政,探寻强国富民之道,两次乡试落第,更使他对八股文取士的陈规不屑一顾,批评皇帝“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认为吏治腐败、人心敝坏,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种。 消息传到沙滩,郑珍吓了一跳,言其惹下杀身大祸。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赏了他一个“候补知县”,差遣到曾国藩江南大营听用。其实,他只委了“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个偶然机遇,以小吏之身终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国藩早起查看诸营,夜色未退,只远处一点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见一年轻人正习文练字,一番攀谈有感其才,遂调进了秘书班子。这之后,未见黎庶昌在军事上有过什么建树,但曾国藩乃桐城派晚期领袖,其诗文风骚独领,他身边又聚集着一群饱学之士,黎庶昌与他们诗文唱和,文学上倒是日有精进。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黎庶昌一度仕途彷徨。为此他写信向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求教,希望他推荐自己到李鸿章的淮军中去建立军功。曾国藩回信认为不妥,理由是,中原初定,建立军功已殊为不易。况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屡立战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杖策相从”,充其量混个助理、秘书罢了,何必呢。 曾国藩这一瓢冷水浇得正逢其时。如果黎庶昌随李鸿章去陕西“剿匪”,手上就会沾上血污,笔下则少了华章。这当然并非曾国藩初衷,历史在这里愣了一下神儿,清廷失去了一条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中国近代史则多了一位引火种于华夏的先贤。 二 1876年10月17日,黎庶昌第一次漂洋过海,他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从上海吴淞口起锚出海时,可曾想到,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中国的近代史,他的荣辱进退也将构成祖国母亲脸上的细微表情? 记述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伦敦记》,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历时50余天,航程31000里,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观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见黎庶昌当年的情景: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极目远眺,但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低头,海浪击打船舷,有如碎玉乱溅;抬首,一行海鸥正掠过天际,引发了他一腔豪情。说来令人惊诧,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以“天朝上国”自居,凡出使外邦者皆为人不屑。郭嵩焘首任英国公使,竟被乡党耻笑,他原拟檄调的参赞也有人囿于偏见托词不就。黎庶昌则不然,他受林则徐、魏源影响,企盼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学来富民强国之道。尽管行前家人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奉调,成了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诸国,开明的黎庶昌还是有些“蒙圈儿”。 他这样描述递交国书的过程:宫门外陈兵一队,奏乐迎宾。至门前下车后,他以参赞身份手捧国书,紧随公使曾纪泽身后,“以次鱼贯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国总统则“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双方互致诵答后,再鞠个躬就齐活了。不妨对比他回国时被召见的情景:半夜两点半来到军机房候着,早上八点半才应召进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黄纱幔,制如屏风,皇帝则坐于幔前”。黎庶昌进门即跪,高呼“跪请圣安”;复摘冠于地,再呼:“叩谢天恩”,随即一个头要在地上磕出响儿来。其后,所有的回话都要跪地而答。慈禧先和他扯了几句闲篇儿,突然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是站立么?”“是。”“他们也还恭顺。”听慈禧话音儿,仿佛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后,割地赔款的不是清廷,倒是以两万余众便长驱直入北京,令慈禧仓皇出逃的西方列强。 黎庶昌前后出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参赞,参观了不少政务活动,且看他笔下法国议院开会的场面:在一个可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厅里,议长居中而坐,手边放一铃铛,与会者可自由发言,议长“不欲其议”,摇铃制止也没人理会。有一绅士,“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10人,余皆民党”,或嘲讽讥笑,或拍手起哄。法国总统马克蒙因为在议院中得不到多数支持,只好下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 黎庶昌没有嘲笑“蛮夷之地”的不臣之举,反省清廷决策过程,认为这才是民政之效也。他参观各类工厂,深感机器生产确是强国富民之要术,见证了顶层政治设计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看到西洋民众欣赏戏剧、参观画展、举办舞会,被封建卫道士斥为桑间濮道的所谓“淫靡”之风,不过是社会风气开化的表现罢了。由于法制相对完善,为官者较之清廷也廉洁得多。耶稣蒙难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举办纪念活动,国王和王后竟亲自给平民洗脚。在大清王朝,有这想法就触犯天条,说出来就是作死! 黎庶昌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了下来。按说,他游览西方诸国,事事皆动于心,文章应声情并茂,可是在他的笔下却没有文接千载的议论,都是纯客观记述,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零度叙事。这是因为他当年应召上书,出语无忌受到弹劾,如果不是特定背景,被“递解还乡”甚至杀头也未可知。郭嵩焘作为首任中国驻外使节,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欣赏羡慕之情常溢于言表,结果被抓住小辫儿,斥为“汉奸”,堂堂二品大员被一摞到底,死后还险些被开棺鞭尸。不过,倘据此认为黎庶昌是因为官场颓风熏染而变得圆滑了,则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学问立身,如求自保,可以尸位素餐。作为一个盗火者,黎庶昌其实是想尽量不被守旧势力纠缠,多运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沾溉。 三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绿色还在路上。一匹快马疾奔而来,扬起一路黄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佩带腰刀的折差一挽缰绳,烈马前蹄腾空,发出一声长鸣。 日本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第16个年头,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书清廷求变。 使欧归国后,黎庶昌升任驻日公使,时年45岁。官帽上的顶珠已由青金石换成了珊瑚,穿上了绣有锦鸡的清廷二品高干制服。那时的他对未来一定踌躇满志,“斯游应比封侯壮,莫道书生骨相穷”,便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不然,展室墙上的黎庶昌怎么会怡然而笑? 黎庶昌当然有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犹存,朝野中许多人对中华文化颇有造诣,可以汉文成诗。黎庶昌家学渊源,上任甫始,便常与他们吟诗唱和。一时间,在日本的文人骚客当中,如果与黎庶昌没有过从竟成了一件很没面子的事。那时西学渐兴,旧版秘籍已不为日本书肆所重视,其中竟有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还是孤本。黎庶昌通过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访。“耗三年薪俸积余,举银一万八千两”,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丛书》200卷。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伟。 不过,黎庶昌脸上的笑容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他的文化外交应该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对本国及所在国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他很欣赏前任大使的参赞黄遵宪,想留其共事,却被黄一口拒绝了,理由是,“非不为公佐,实弱国无外交可言”。上任后不久,黎庶昌即感到黄遵宪言之不虚。在许多外交场合,他所受到的礼遇颇为疏阔。中国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强行设县,黎庶昌赴任后曾试图通过交涉有所转圜,终因国力衰微,眼巴巴看着日本将其彻底吞并,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天朝上国”怎样被“东海区区一岛国”所轻慢。他出使欧洲6年,足迹遍及西方诸国,再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反省清廷的因循守旧、国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变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3年,黎庶昌写成《敬陈管见折》递交总理衙门,请求转奏朝廷。他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海军实力,认为当时的水师“战舰未备,魄力未雄”,“实难责与西人匹敌”,要练足一百号兵船,分成南北两个水师,专做攻敌之用,而且每个水师应有铁甲巨舰四五艘。只是,这道奏折皇上看都没有看到。总理事务衙门认为“情事不合,且有忌讳处”,将原折退回。曾纪泽知晓奏折的内容后,认为“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掌管总理衙门的亲贵大臣觉得这道奏折有涉忌讳处,也不是纯属推诿之词。天朝威武。慈禧觉得有水军撑一下门面就足矣,花更多的银子去添船置炮纯属多余,如果当时看了黎庶昌的折子,难保不甩脸子。至于朝廷那些守旧的大臣,十分仇视“火车轮船”,对黎庶昌的相关奏请更会横加指责。 清廷又错失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折当时能被采纳,后来的甲午之战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中国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四 我端详着黎庶昌的半身雕像不愿移步。真是感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贤塑造得栩栩如生:瓜皮帽、长布衫,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两道利剑,脱鞘而出,正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向远方眺望。 我们的目光在瞬间对接。 哦,他的目光中为什么会有难以排遣的忧怨? 他的忧怨是因为他对大清国的失望。甲午开战之前,时任四川川东道员的黎庶昌曾请命去日本斡旋,他明白战端一开断难取胜,不是因为兵单力薄,那时,北洋水师已有各种战舰70余艘。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九。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军力对比。政治腐败、贪腐盛行,李鸿章已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在官场谋身立命的私产,上下不能一心,将士难以用命,水师成军后装备从未更新,指挥、训练、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备,早在日本海军之下,一旦交手,胜算能有几何?清廷没有“恩准”他的这一请求。翁同龢主战,光绪皇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他们已被表面上的强大所迷惑。深知水师实力的李鸿章则有口难言,因为他以操练水师有功揽权邀宠,已获得了清廷太多的褒奖。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虽然他出使日本时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盛誉,但以他的游说想使日本休兵罢战,则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满岛国之境久矣,对外扩张是既定国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国之是非皆以实力强弱而论,他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但是一旦开战,作为爱国者的黎庶昌则从主和派变成了坚定的主战派。双方已然交手,再提后撤无异投降。甲午之战期间,黎庶昌每每忧愤至极,终日不食。 焉能不怨?开仗以来,噩耗频传。十年前就上书清廷需厉兵秣马的黎庶昌,在战事中要捐白银万两以襄军费,并奏请朝廷令各级官员出钱助战,被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闻败耗便失声痛哭时,慈禧却正在筹措巨资,一门心思要办60大寿庆典,准备接受百官朝贺。黎庶昌的眼泪仅仅是流给阵亡的将士吗?作为一介儒生,他的内心是矛盾的。清廷的专制与腐败他洞若观火,而忠君的历史局限又让他不愿看到大厦将倾。这和其恩师何其相似乃尔,曾国藩深知清兵腐朽无能,弹压内乱尚可,抵御外敌堪忧,曾提出裁撤绿营编练新军。清廷拒绝了他的军改方案,曾国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异族统治者,原来清廷惧内乱较外患更甚,由此绝望至极。但听幕僚预言清廷将在50年内灭亡,却唯愿速死。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识分子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幸?“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况且,凤非凤台亦非台;情系华夏,当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苍生,何必因沉舟病树哀伤? 作为晚清一名从西方盗火的知识分子,黎庶昌固然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但是,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国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种施政理念,这或许比坚船利炮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强盛。 黎庶昌多次记述了递交国书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也是“相视一笑,礼仪甚简”。反观清廷,仅一个“拜折”仪式就令人惊诧:地方大员向朝廷呈报奏折前,要设置香案供奉用黄缎包裹的小木箱,要鸣放礼炮,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朝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场规则,但是他却在文章中曲隐地表达了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的不以为然。 不过,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者不同,黎庶昌主张“酌用西法”。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吗?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们的经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倡导吗?黎庶昌与李鸿章均为曾国藩幕属,后来李鸿章权倾朝野,但黎庶昌对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赞同,曾婉言提示,或许李鸿章不以为然。黎庶昌无奈叹曰:“两大之间难为小,然子产相郑,郑已立。国朝的子产安在乎?”郭嵩焘在引欧风美雨启迪民智上功不可没,但他认为英国拥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为“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在汲取与接纳西方文明时,黎庶昌没有忘记托承传统文化之精义,难能可贵。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还表现在能与时俱进。他也曾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也曾盲目憎恨洋人。可贵的是,经过实地考察,很快纠正了偏见,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滩老屋郁郁而终,时年61岁。他死后第2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其实,谭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张大都在黎庶昌的历次上书中涉及。一腔热血谁珍重?洒去尤能化碧涛!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社会彻底变革之先声,谁能否认,菜市口刑场上空那血染的风采中,没有黎庶昌的一腔热血呢? (作者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选刊》杂志原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