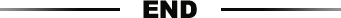|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罗素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代表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简介:约翰·勒恩兹(John R. Lenz)著 吴万伟 译。作者系罗素协会前会长,在德鲁大学讲授古典学。
本文讲述罗素为什么认为哲学是有价值的。
伯特兰·罗素对哲学这个词的定义给哲学造成了伤害。早年,他曾将哲学定义为逻辑分析方法。这个定义如此严苛以至于虽然他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撰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谈论战争、和平、幸福、科学、社会和人类未来等,但他被迫将很多书描述为“大众的”或“非哲学的”东西。事实上,他逐渐形成了对哲学及其人生价值的另类观点。
他的很多流行著作被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和对罗素作为哲学家感兴趣的人忽略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当然,他有很多社会活动、流行著作和争取和平的运动都很著名而且深受民众的爱戴。但是,这些通常都留给传记作家当作素材而非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哲学著作。随手捡起一本书比如《剑桥罗素读本》或者最近的百年纪念文集《哲学问题》,你可能根本无法从这些书中了解到罗素的人性理论;他一再(至少从1916年到1960年代末期)鼓吹的未来乌托邦建议;他充满激情地支持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人生价值,即哲学是通向幸福和智慧的道路。学术界对罗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分析哲学,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的著作。但这个视野过于狭隘。罗素的视野要宽广得多。
罗素吹嘘他对哲学的贡献是革命性的。他帮助开创的逻辑分析方法是解开传统哲学问题死结的工具。他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1914)等著作中提出了这种科学方法。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里,知识理论占据中心舞台。哲学已经变成区分真假知识、信仰和命题的科学。
超越分析的哲学
当今哲学家对分析哲学源头的辩论部分就基于自己对该领域的观点。汤姆·阿克赫斯特(Tom Akehurst)提出了新鲜见解。在2010年的书《分析哲学的文化政治》中,他说英美分析哲学旨在忽略政治,但其实是把英国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分析哲学的繁荣基于一种文化共识,因为英国和美国并没有遭遇困扰欧洲大陆的意识形态冲突。那是安全的、非意识形态的,关心形式命题而不是生活,不是革命,不是黑格尔激发的激进主义。分析哲学对革命没有兴趣,因为黑格尔的逻辑是错误的。
罗斯本人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从来没有限制兴趣范围。他与黑格尔哲学决裂与他在第一本书《德国社会民主》(1896)中对社会进步问题的英国社会党途径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仍然对探索逻辑分析和社会科学感兴趣,同时认识到后者还不是科学。作为无神论者,他或许体现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开端。在他看来,哲学指出了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
甚至在举起逻辑分析的大旗之前,罗素就表达了有关“哲学价值”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信条。在《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尤其是最后六段至今仍然令更严格遵循学院派哲学的罗素崇拜者感到尴尬,因为他热情称赞哲学的精神价值。“除了它的功利性之外,哲学还有价值---或许是它的主要价值---通过它思考对象的宏大和从这种思辨中产生的摆脱狭隘和个人目标的自由。”他接着补充说,通过“哲学思辨”庞大和非人的宇宙,“致力于哲学探索的人”会享受“宁静和自由”。这种情感是彻底的苏格拉底派,接近于斯多葛派。思想的宁静源于逃脱欲望、自我和激情的牢笼。当然,罗素采取了柏拉图式语言,虽然他拒绝了柏拉图哲学。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他谈论精神问题是徒劳地找到与情人奥托琳·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一致的共同立场。但是,将这些话当作罗素这个人而不是哲学家罗素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的这种哲学观一直持续到他漫长一生的尽头。就在宣称其“科学方法”两年后,在战争期间,罗素写到“世界需要推崇生命的哲学。”(社会重构原则,1916)。这是他一辈子的工作。他后来说,“如果没有活着的人了解的话,逻辑真理还不如两个大头针重要。”(interview, 1964, in R.W. Clark, 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 p.504)
超越实用性的哲学
分析之后智慧到来。罗素的典型做法是在流行著作的末尾提出警告,把他一直在分析的技术问题放在更大视角之中。比如在《科学世界观》(1931)年的最后一章第17章“科学与价值”中,他区分了两种知识:“我们或许寻找某个对象的知识,因为我们爱这个对象或者因为我们希望拥有控制它的权力。第一种冲动导致一种思辨性知识,后面一种导致一种实用性知识。在科学的发展中,权力冲动越来越多地凌驾于爱的冲动之上。”科学取得实际成功,但它不过是工具性的,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什么是更高的目的?爱情激励下的思辨性知识让我们知道和逐渐栖身于“给予快乐或愉快或狂喜”的更高目的。哲学家(等人)寻求“思辨的狂喜”。“恋人、诗人和神秘主义者能找到追求权力者永远不知道的更充分满足。”这里的恋人包括热爱真理者,即哲学家,虽然可能存在很多个别道路。
对理性生活的这种高度赞扬与他的逻辑分析哲学并不冲突,这种哲学旨在获得非个人的真理;但是,他当然远远不止宣扬智慧:“正是对永久性内容的这种愉快思辨让斯宾诺莎称之为“”对神理智的爱”。对那些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来说,它是智慧的关键。”这里的“永久性”在这位著名的无神论者看来是指某种“人类生活之外的东西,非个人的和人类之外的目的,如上帝或真理或者美。”(社会重构原则,1916)。罗素从来没有偏离这个观点,虽然他后来弱化了形而上学形象。在论述科学未来的著作的结论部分,他感到遗憾的是,实用科学的胜利显然意味着好奇心的丧失、对宇宙之爱的丧失,以及形而上学之前提供的人类价值观的丧失。所以,罗素希望他提供的哲学能弥补这种丧失。
最初,伯特兰·罗素觉得“伟大的世俗主义者”这个说法是个悖论。但是,与大众的假设相反,倾向于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哲学家并不总是支持唯物主义价值观---想想伊壁鸠鲁学派;相反,我们习惯于看到倾向于唯心主义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是唯物主义做派。罗素嘲笑没有想象力的唯物主义:他说,最具人性的人类活动是由“在地球表面或接近表面的物质的位置改变”所构成(称赞无所事事,1932)。“实用主义对心智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在星球表面发现了其充满想象力的物质整体。”(实用主义,1909)
这是他反对功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是纯粹的实用性(这不公平)。他认为只是鼓吹现实成功或者功利哲学或科学哲学或教育理论都源于“权力冲动”,不过提供“政府眼中的真理”罢了。教育应该培养的不是国家的优秀公民而是“世界公民”。“在永恒的外表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在我看来,个人教育是比公民教育更细腻的事。”这样的个人为社会改善带来世界性视角(想象从柏拉图的洞穴中逃出的哲学家返回洞穴教导里面居民更高的智慧),不仅个人而且整个社会都能从思辨中受益,在更宏大范围内成为“世界公民”。当然,我们永远需要提醒大学意识到自由教育的原则。
世俗主义者罗素并没有在寂静主义(quietism)止步。这是行动哲学:他写到“行动若产生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就是最好的。”(无用的知识,1932)或者“人生目标不仅仅是思辨或者不仅仅是行动,而是建立在思辨基础上的行动,试图将世界的无限具身化的行动。”(《文集》“约翰·福斯特的难题”,1912年,第12卷)。可以说,聪明人一只眼盯着城市,一只眼看到城市之外的东西。
超越时空的哲学
后来,罗素减弱了他带有柏拉图风格的思考永久普遍真理的语言。但是,他继续做出有关哲学效果的雄心勃勃主张,因而也是有关哲学是什么的主张。在《西方哲学史》(1946)充满必胜主义的最后一章,他甚至断言非个人色彩的“科学”哲学方法的好处延伸到“人类活动的整个空间,拥有同情和相互理解的更大潜力而减缓狂热激情。”他得出结论说,“哲学暗示和激励生活方式的功能不会停止”,因而重新承认哲学的传统目标是其逻辑分析方法的后果。(事实上,结合与社会的关系写哲学史,其本身并不是逻辑分析活动)
“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的义务”(1964)是罗素就此话题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文中,他描述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哲学家的定义性特征。这是以罗素本人采取的同样路线为基础的个人发展模式。首先,“我认为,在他的教育结束之前,他的注意力应该太多沉浸在现代哲学的技术方面,因而很少关注自己时代的政治问题。”后来,对他和哲学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或许存在一个义务,那就是说服人类相信人生是值得维持的。”接着,“在现代世界,哲学家应该如何生活?哲学的某些教训是古老和无时间性的。他应该竭力追求看清这个世界,尽可能摆脱时间和空间的偏见,不刻意强调此时此地而非其他时间和其他空间。当他考虑所生活的世界时,他必须像来自外星球的陌生人那样走近它。这种不偏不倚是所有时代哲学家的义务。”这种哲学心态给予哲学家符合逻辑的可信度,使其在世界问题上采取仁慈的立场。
超越学界的哲学
的确,罗素常常采取一种先知的口吻或乌托邦的口吻。他后期有关核时代的著作《人有未来吗?》(1961)的末尾是临时性预测“创造过程中的新世界转型期。”但是,在这似乎幻想的背后包括对世界政府详细架构的阐述,是罗素毫不妥协地鼓吹理性、他的人性理论和有关教育和适当科学追求的理论。
罗素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写进他的“畅销”书。幸运的是,他本人挣脱了自己套上的数学逻辑紧身衣的束缚。人类生活有一种闯入方式,不仅闯入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而且闯入他的哲学。在老年回顾过去时,他说,在1901年一位朋友的痛苦让他充满了“一种像佛祖一样的深刻欲望,要找到让人类生活能够忍受的哲学”(自传,1967)。他知道,这个同样重要的“生活哲学”不能完全是科学的,虽然他总是渴望从理性中找到这种生活。很多年后,他阐述自己的幸福生活观和人性和世界未来。这样做时,他持续使用广义的哲学,坚持认为普遍的、不偏不倚的视角产生更聪明、更幸福的个人,也是走向更美好世界的唯一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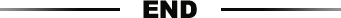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