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经过赵正之、宿白、徐苹芳等先生的倡导和实践,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地方城市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也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总的说来影响不大,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就是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虽然有徐苹芳等先生极力呼吁,却远远制止不了建筑界和当地政府在没有搞清楚城市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做出错误的城市改造规划,开发中带来建设性的破坏。以下是笔者针对上述现象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当增加主动参与到当代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工作中来,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城市规划做好基础研究,使得城市的发展建立在有序更新的基础上。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数目已经达到117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公布之后,各地也陆续公布了一些地方历史文化名城,并由此影响到了古镇、古村落的保护,从2003年起,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开始陆续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录。上述工作对于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风貌,对于影响和干预市政规划的总体方向,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传承意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建筑、旅游部门的工作相比,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明显处于劣势。我们承认建筑、旅游部门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强调没有考古工作的基础,建设和旅游部门的工作就有可能偏离保护与传承的良好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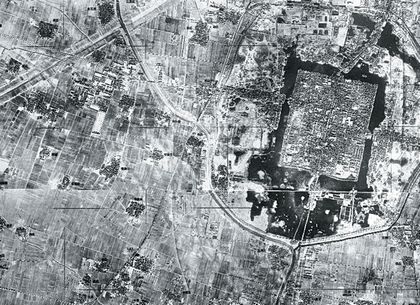 举例来说,江南古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古镇研究的重要内容,古镇都有哪些类型,它们是怎么发展演变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基础工作。目前江南古镇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带动当地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论是研究还是保护,都难得见到文物部门的身影。研究应当成为保护利用的基础,而建筑和旅游系统的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这些偏差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如阮仪山先生在《江南古镇》中试图用“带形城镇”“十字形或丁字形城镇”“星形城镇”“圆形城镇”“双体城镇”来概括江南古镇的平面形态。在“星形城镇”中,他分析了吴县甪直镇的历史演变,并绘制了“吴县甪直镇平面图及历史形成图”。 江南水系屡经变化,现在的水系不能用以代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水系。为了表示这幅图的科学性,春秋和汉唐聚落部分还都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如果真是这样的形状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至少要对这个范围内外进行过考古钻探,或者考古发掘,才能在图上标出这样的形状。我们在这里谈这幅图的问题,并不是想仅仅就这幅图来论图,我们想讨论的是,这样的图不止一幅两幅,可是有的研究以此为基础,如段进先生等出版的《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在这些图的基础上,“运用结构主义关于结构的三种数学原型对传统小城镇的空间结构进行解析”,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研究,不管运用什么“主义”来解析,结论都是可疑的。 不对古代城镇做认真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做出的规划非但起不到保护的功效,反而会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这样的事例我们屡见不鲜。 西周初年,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宋﹙今商丘﹚,建立宋国。现已探明宋国都城的城墙周长12985米,面积是现在商丘古城的十倍。商丘地处睢水北岸,故历史上又被称为睢阳。睢水在古代曾经是大运河的一段,近年来在睢水旧河岸边发现了码头遗迹,出土了一些重要遗迹和遗物。 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考古发现了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被黄河水冲坏的商丘古城,可以确认该城南墙利用了一部分宋城南墙的基础,反映了商丘古城的历史延续性。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黄河泛滥,冲塌商丘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开始,以原城的北墙为南墙重新修建商丘城。 1511年,新的城池建造工程完工。明嘉靖年间,又在新城外距城一里许,修筑了周十六里,平面近圆形,“高视城之半,厚倍之,上树之柳”的护城堤,这圈护城堤在后来的洪水泛滥中确实起到过保护城内居民的作用,并一度增加高度。所以现在许多人将商丘古城说成是外圆内方的古钱形状。 实际上为了防御洪水的侵袭,明代在黄泛区内普遍采用内城外围以防洪堤的防御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夏邑古城、淮阳、菏泽、聊城等多座古城都采取了类似的城防措施,如聊城《宣统志》卷二《建置志》“城池”记载聊城“宋淳化三年河决,城圮于水,乃移治于孝武渡西,即今治也。熙宁三年建城市,旧筑以土,明洪武五年守御指挥陈镛始甃以砖石,周七里一百九步,高三丈五尺,……附城为郭,郭外各为水门,钓桥横跨水上,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阔倍之三。护城堤延亘二十里,以御水涨,金城倚之。”这个案例说明了地方城址的研究,同样需要注重区域调查。 去年11月29日,商丘古城迎来了重建五百周年的纪念日。《京九晚报》出版了纪念特刊,刊登了同济大学所做的古城规划图,把内城之外和原来护城堤之间的区域规划成大面积的湖面,将商丘古城错误地归结为“归德之城”和“厚德之水”两个区域,并根据延伸的道路将“厚德之水”又分为“上善若水”休闲度假区、“财富智水”时尚体验区、“应天秀水”历史文化赏游区、“逍遥乐水”滨湖游憩区四个小区,把原来为防洪而围护的区域变成泽国,不但违背了史实,而且也会对宋国故城的文化遗迹造成破坏。 面对这些让人心痛的案例,考古工作者实在有必要加大自己的工作力度,在古城研究和保护发展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比如沈阳在明代是十字街,现在的井字街是为了故宫建设的需要而加以改变的,但是十字街的遗痕还在,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这个十字街的遗痕应该加以保留。再如河南光山是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县城,但是它原来的街道都是丁字街,很有特点,这些街道可以通过疏散城内居民的方式,改建成步行街。地方政府不一定接受我们的建议,但至少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呼吁,把这些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他们了,尽到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实际上现在司马光大道的扩建,将光山古代城市的机理破坏了,也并没有缓解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类似的如北京东四十条拆除之后扩建的平安大道,也并没有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反而把车流吸引到平安大道上来。从事城市考古工作的同行,应当增强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未来城市发展相联系的意识,在城市建设当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就需要重视研究古今重叠型地址城市的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 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总结与推广还不够,不但是别的学界,即使是考古学界,对此方法了解得也不够,已如笔者在《地方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所述(刊《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11日,与本文实为同一篇文章)。这种方法难免有推测的地方,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勘探和发掘,以印证我们的推测,同时有助于我们修正或补充有关的方法论。 2011年5月5日,一段《南宋皇城遗址建千万元豪宅》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开发商正在大举动工,开挖地基,而文物爱好者则在工地上淘宝,发掘出了廊柱、地砖等南宋时期的文物。为此,皇城的范围问题再次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 南宋皇城袭自北宋杭州州治,前身即吴越子城。《咸淳临安志》卷五二《府治》记: 府治,旧在凤凰山之右,自唐为治所。子城南曰通越门,北曰双门,吴越王钱氏造。……中兴驻跸,因以为行宫。 子城依山而建,下瞰罗城,是南方地区城市常见的情况。建炎三年(1129),高宗抵达杭州,以州治为行宫。 皇城的勘探是南宋临安城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东墙确定位于馒头山东麓。临安外城袭自北宋,前身是吴越所筑罗城。南宋初年,皇城东南并无外城。每遇朝会,臣僚只能先由候潮门出城,绕至利涉门入城,方可抵达皇城南门,极为不便。所以在绍兴十三年八月,大理寺臣吴镛上言请求在皇城外东南添筑外城,“若城外朝路难以移改,只于朝路之外东量添城壁,免致未旦启钥。”吴镛的建议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方下诏付诸实施: “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可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具合用钱数申尚书省于御前支降。今来所展地步不多,除官屋外,如有民间屋宇,令张偁措置优恤。” 这个方案经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看过之后,认为“展城离隔墙五丈,街路止阔三丈,只是通得朝马路。今乞更展八丈,通一十三丈,以五丈作街(御)路,六丈令民居。将来圣驾亲郊区,由候潮门经从所展街(御)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而较原来方案所更多拓展出来的八丈,“十之九是本司营寨教场,其余是居民零碎小屋。若筑城毕工,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委实利便”。后来在皇城东南添筑的五百四十一丈外城,就是按照杨存中的修改方案执行的,这样,外城墙与皇城隔墙之间的距离,就是十三丈,约合41米。 宋亡以后,皇城废置。至元二十三年,杨琏真伽于其地建寺修塔。入元以后,由于担心南方割据,这一地区的城防设施普遍没有加以维护甚至有意破坏,杭州城同样没有得到维护。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士信大发浙西诸郡民修筑杭州城。此事详记于贡师泰所撰《杭州新城碑》。这次改筑城对南宋以来的杭州城改动较大,东侧从菜市河拓展到外沙河一线,万松岭北修筑南城墙,将南宋皇城弃置于城外,南宋皇城遂日趋湮废。 文物部门以前找到一段皇城的东墙,据此明确了东墙的大致走向。所确认的皇城东墙,距离外城墙有100多米的距离。后来在粮食仓库工地又发现了一段夯土墙,据认为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但都没有详细的考古报告。这段城墙距离外城约41米。2001年在绿城西子房地产有限公司御园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迹遗物就在粮食仓库一带,有学者根据文献和这些遗迹遗物,认为这个地段在皇城之内,他们的主要文献依据是郎瑛《七修类稿》卷二《杭州宋宫考》: 计其地,南自胜果入路,北则入城,环至德侔牌,东沿河,西至山岗,自地至山,随其上下以为宫殿也。 其中“东沿河,西至山岗”中的河就是指中河,这样皇城的范围就在中河东岸,绿城公司开发的地段自然就在他们认为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依据社科院等的工作,这个地段就在皇城之外。 刘未在其博士论文《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中,指出这段文字实出自明代中晚期人的一段补注,并对以前皇城东墙的具体方位标示了保留意见,刘未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宋会要辑稿》“方域”条所载杨存中的上言明确说皇城有隔墙,这段文献是宋代人记宋代事,可信程度应该很高。补修外城的和隔墙的距离是13丈,约合41米,恰好是现在粮食仓库附近的那段夯土城墙的位置,而如果按照过去确认的皇城走向推测,则皇城与外城最近处相距也要100多米,无法解释《宋会要辑稿》中的13丈。皇城的东隔墙应该在粮食仓库一线,这个地域附近还是相当敏感的。 类似这样的勘探和发掘面积不大,出土遗物也许只是一些残砖碎瓦,但其作用却不可小觑。比如,湖北黄冈的黄州城因为苏东坡曾经贬谪此地而为著名,黄州宋城和明清城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 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宋元时期的黄州府城在“今城南二里许,西临大江,东傍湖泊,水涨湮没”,在修弘治《黄州府志》时,“其西临江岸,为水摧倾;其南今平为民居;其北、东城迹犹存。旧城门曰朝宗、向日、龙凤,余无可考。洪武元年,指挥黄荣移住今城,近北高阜固地,以易旧城”。 按照府志的记载,则宋城、明清城是分别建在不同地点的两座城址。2011年,为了解决城址的修建、使用与废弃年代,湖北的考古工作者在定惠院民房附近开了一条2×6米的探沟,探沟内的地层堆积层次清晰,城垣夯土内最早的包含物为六朝,最晚的包含物是宋代。这样,明清黄州城南有宋城遗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自古以来赤壁矶的位置没有发生过变化,如果以西北方的赤壁矶为坐标,则显然宋城在明清城南的观点又出现了问题。这条探沟恰好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即宋城的范围可能比明清黄州城大,明清黄州城的西、北相当部分在宋城的范围内。宋代的黄州城很可能延续了六朝修建的城垣,只是这座城垣在宋代已经残破不堪。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三贬黄州,对黄州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他的诗文中也数度提及黄州,在他的笔下,“黄州为名,而无城郭。西北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与北宋政府统一南方之后,对南方地区城防设施怀有戒心,不事修理有关。到了明代洪武年间,宋代凋敝的城垣基本上成为历史的记忆了,所以才有宋城与明城之间关系的争论。 城市考古所要经历的时间长,要随时注意发现的与城址有关的遗迹遗物,比如城市基建开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遗迹现象,由于没有珍贵文物,或者文物部门没有及时得到报告等原因而往往被人忽略,但是这些零散的考古材料却是地方城市发展中难得的印证。随着近些年来社会上收藏热的变态升温,这些零散的出土物却受到社会上收藏者的重视,近期在山东聊城的古城改造中,一些居民捡拾地基开挖过程中出土的瓷片和钱币等遗物;北京的一些不法商贩,甚至利用北京地方史研究的成果,雇人跟踪一些工地的进展,从中牟利。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检讨。“见缝插针,积少成多”,在大比例的城市地图上,及时将考古发现的各类遗迹标示于其上,长期积累,才有可能深化对当地城市演变的认识。因此,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研究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当地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过去许多工作有一个误区,认为城就是城墙、城门、重要建筑物、街区等,把它们割裂开来对待,而这些实际上是城市作为综合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名单里,就有几种表述方式。有只公布城墙的,如西安城墙、平遥城墙、崇武城墙;有公布为遗址、或城墙遗址的,如平粮台古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邺城遗址、辽中京遗址、应昌路故城遗址、元大都城墙遗址;有只公布城址中一部分重要建筑群遗址的,如大明宫遗址、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近年来公布时开始考虑到与城址相关的墓群、重要建筑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如所公布的许三湾城及墓群、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等,反映了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方面的进步,我们需要将古今重叠型城市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注意与城市发展有关联的所有遗迹现象。 第三,加大对中国古代地方城镇的研究力度,加强学科建设,注重人才培养。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与我们大学的课程设置有关。我们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专业划分过细,不同专业间的合作又很不够,比如,规划是作为一个专业来对待的,可是仅仅是现在大学的规划专业的课程,无法满足对古代城镇规划的需要,没有文物考古的相关基础工作,规划专业的学生无法完全认识到所规划对象的学术价值,从而也就无法规划做到位;而目前大学的考古教学,一般都是讲到宋元时期为止,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的重视程度无法满足现在文博考古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即使是到宋元,轻重也不平衡。考古学有四大研究对象,即城址(包括聚落)、墓葬、手工业和宗教遗存。但现在城址(包括聚落)和墓葬的研究明显不如手工业的研究受到重视,这势必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常发展,也势必影响到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