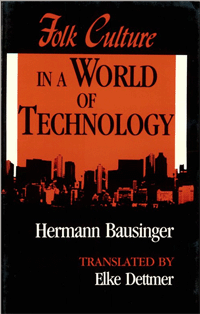|
《科技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英译本可谓姗姗来迟。当原书于1961年出版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民俗学主要刊物都未有评介。七年后,当美国的学者开始讨论城市民俗经验时,也没有任何人提及鲍辛格的这部开山之作(参见1971年阿莫里克·帕利德斯等编、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经验与民间传统》)。尽管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城市民俗和城市民族志的研究日趋增长,在英语民俗学刊物上对该书提及引用仍旧寥寥无几。然而在德国,该书初版25年后,坎波斯·沃勒格用流行版式重印此书,显示了它的生命力以及对学界研究取向的参考价值。英美的民俗学者对鲍辛格的理论研究孤陋寡闻,未曾从中获益。语言的障碍又一次阻隔了民俗研究的交流。 过去三十年城市民俗研究日渐红火的态势,居住/工业化/公司背景、当代传说、大众文化、民俗复兴、奇风异俗展示及商业化等话题的讨论,证实了鲍辛格的理论探索对当代研究的价值。当上述各个方面分别成为无数分析和描述研究的探讨对象时,只有鲍辛格试图将它们纳入到一个统一而系统的理论框架内,将之作为科技世界的反应物。面对突飞猛进的科技世界,许多人哀叹传统社会的消逝,鲍辛格则指出:当人类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会有形态的变迁,但却不会消失。与传统瓦解论相反,他提出了一种科技世界中传统文化的扩展理论。 基于此,这是一部富于革命性的著作。鲍辛格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他剥去了对民俗的浪漫情思和对传统生活的美化,在他的理论中,有着拥挤的街道、污浊的空气、种族杂居的城市,与开阔的田野、晴朗的天空、传统的村民一样,构成了民俗的“自然环境”。表现为思乡怀旧并成为民俗研究动力的城乡间的紧张关系,在鲍氏理论中变成了科技世界的一种功能;同样,作为民俗学关键概念的“传统”,并非作为民俗的起因而是作为结果获得意义。传统不是作为悠久的知识和价值观念通过语言、艺术、音乐代代相传,它常常状态混乱,在变化的压力下趋于分解;人们努力通过新的仪礼、展示、各种形式的娱乐,或通过复古以重建维持之。鲍辛格远在埃里克· 霍布斯鲍恩和特伦斯·兰杰(1983年出版的《传统的发明》一书的编者)之前,就将传统视为一种文化建造而非文化承继。 鲍辛格著作中涌现的见解,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新鲜感。其中三个突出的观念是:民俗的非民族化、扩展化和商品化。民俗在时空和社会维度上的扩展化是鲍辛格致力分析的主要观念,而非民族化、商品化的概念,其意义亦不在扩展化之下。 非民族化并不是指传统文化中一种民俗的进程,而是指一个现代社会对待民俗的应有态度,它反映了社会对民俗的一种评估(在此是低估)。民俗曾被当作是一个民族立国之本,鲍辛格则认为,作为正确论析的前提,必须低估民俗的民族意义。与浪漫主义的理解相左,他倡导将民俗研究作为一种分析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而非发掘国家民族地位的工具。源于人文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民俗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已经渗入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浪漫主义将民俗视为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现,现代某些执政党则歪曲浪漫主义的原意,用以荼毒其他民族。鲍辛格认识到,为了将民俗学从狭隘民族主义的魔掌中解救出来,特别是考虑到它曾被纳粹德国所利用,必须将之非民族化,脱离民族观念的干系,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鲍辛格倾向于将民俗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由于这一选择,鲍辛格将民俗学引入了以往较少涉足的跨学科交叉地带。社会学家们对民俗学的价值不屑一顾,而民俗学家们也大都没有意识到社会学之于民俗研究具有的理论分析潜能(见肯尼思·汤普逊:“民俗学与社会学”,载《社会学评论》1980年28卷,249-275页),甚至鲍辛格本人在他的文化分析中,也并未运用任何社会学的理论或方法。鲍辛格设想两个学科可以在同一个主题上结盟:城市。对民俗学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社会学却已涉足多年。这一共同研究领域的提出,使得社会学而非人类学可以从中受惠。现在这两门社会科学的领域正在转移,农村社会学和城市人类学已是根基稳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城市化、现代性、高科技等话题所左右,使得社会学变成了鲍辛格更适合将民俗学非民族化的学科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