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早报: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很多,有围绕人物而写,有断代等等,你们怎么尽量减少体例繁多带来的阅读障碍或困扰? 孙康宜:如果把《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剑桥意大利文学史》相比,我并不觉得我们的体例特别多。其实剑桥文学史的每一本“欧洲卷”也同样具有各种不同的体例——有围绕人物而写,有按不同的分期,不同的文体分类来写等等。我想《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特别的地方乃是它所包含的“文学史”的时间长度。因为剑桥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 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 宇文所安:按照传统的分类法(重要作家作品、文体)来写很容易,但把那些不同的片段相互串联交织、形成一个单一和完整的叙事则很难。而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文化史,它的确是一个单一完整的叙事。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国文化世界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文学史影响阅读实践 东方早报:这一二十年,各类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非常多。在你看来,文学史对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孙康宜:在我看来,文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某个时代(或地域)的特有文化阐释方式。同样在“中国文学”这样一个语境下,在西方用英文写的“中国文学史”自然会与在中国用中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同。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害怕国内的中文读者会对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中译本产生某种误解,甚至失望。当初如果我们是为了中国读者而写,我们的章节会用另一种角度和方式来写。现在我们既然没为中文读者重写这部文学史,我们也没必要为中文版的读者加添一个新的中文参考书目。的确,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会产生不同方式的“文学史”。 宇文所安:文学史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阅读实践之中(在欧洲也是如此,但在南亚可能没到这个程度)。比如说,我给你一首律诗,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美;但如果我接着告诉你它是来自明代,你再去读,很可能会得出与我告诉你“这是一首唐诗”后不同的评价。因此,一部好的文学史会使我们已有的阅读方式更加丰富。 东方早报:宇文所安教授在上卷导言中说道:“所有这些现场都为文学史带来了难题:这些现场清楚表明,作为一项现代工程的文学史,在何种程度上与民族国家及其利益绑缚在一起,为民族国家提供一部连绵不断的文化史。……”这里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语言政治”问题。你认为,你和其他几位学者在编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总体上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孙教授又是怎么看的? 宇文所安:一般来说,古代文学曾经是一个特定阶级或性别的占有物。在现代民族国家,它通过被纳入由国家建立的学校系统而得到转化,作为国民共同的占有物被教授,为创立 “国家文化传统”作出贡献,而这种国有文化传统是国民对其国家产生认同的主要方式。现代国家政府大笔投资于这一事业,是有目的而为之的。这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加影响深远。在这一(创立国家文化的)过程中,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学材料被重新设定以符合这些新的目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历史事实。 孙康宜:文学史当然会涉及“语言政治”。我想有关这一点,宇文所安教授是同意的。但下册有关现当代文学的篇章, 以及“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诸问题,不会出现在这个北京三联的简体版中。《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英文版早已于2010年出版,读者可以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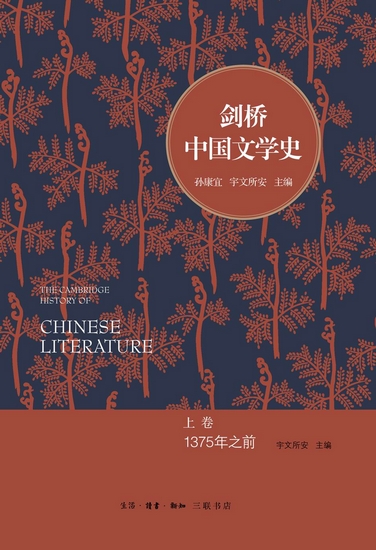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由宇文所安主编,下卷(1375-1949年)由孙康宜主编,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