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达尔文年”已经过去,但达尔文在人类科学史、思想史上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一再回味。去年,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国内出版了大量与达尔文及进化论相关的图书,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达尔文》。该书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权威、最好的达尔文传记,但在国内却未受到读书界应有的重视。为使这本重量级译著不致埋没,我们特发表陈蓉霞女士的长文,以向读者推介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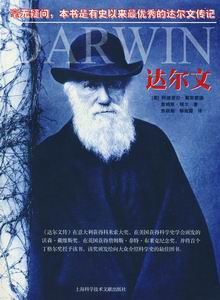 《达尔文》,[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英]詹姆斯·穆尔著,焦晓菊、郭海霞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65.00元 不同于牛顿,达尔文对人类心灵的冲击或许更有震撼力。如果说,牛顿在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依然为上帝保留“第一推动”这一角色的话,那么,达尔文却通过自然选择理论废黜了上帝的这一角色;不同于引力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无须复杂的数学公式作为表达方式,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理解似乎不成问题,但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却需要跨越更大的障碍。不同于牛顿在一个奇迹年完成了他主要的科学工作,达尔文可说是穷其一生思考和完善他的理论。这就使得有关达尔文生平的读物更具可读性,《达尔文》厚重如砖头,却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许多细节可圈可点,即是明证。 航海所见带来了诸多疑问,但最大的疑问却与人类有关。想到那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无法遏制这一念头: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曾如此?同一个造物主怎么会同时造出如此原始和如此复杂的人?一个线索逐渐浮现:各个物种之间存在一个亲缘谱系。联想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神创论的支柱也不再可靠:神所造的世界果真为人而存在? 自然选择理论的对立面是神创论或者说设计论。神创论中隐含了相互关联的若干命题:上帝造物;物种不变;物种背后体现设计者的意图;人类是创世计划中的最高一环;人类的荣耀或尊严直接来自神意。难怪当时的博物学家大多同时也是神职人员,因为博物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神创论提供证据。达尔文刚出道时,弃医学而入神学,原本就是打算做一个悠闲的乡村牧师,同时又能兼顾自己的博物学爱好。初入博物学的达尔文,曾经被当时英国神学家帕利的《自然神学》所打动。在帕利的书中,呈现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不同的物种各就各位,在这背后定然有一个设计者,而博物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寻找这种设计的证据,以便证明上帝的存在。 正是环球航行令达尔文偏离了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1831-1836年间,达尔文成为小猎犬号的乘客,起因是该舰舰长菲茨罗伊在航行期间需要一名绅士做伴,经达尔文在剑桥时的导师亨斯罗的推荐,家庭富裕、刚从剑桥毕业的达尔文有幸成为舰长的客人而获得这次机会。当然航行期间所有费用自理,包括考察费用,好在达尔文有个不差钱的富爸爸。 出航不久,达尔文做的第一个考察工作就是用网捕捉到无数微小的生命,它们形状各异、色彩斑斓,一个念头自然涌现:为什么广阔的海洋里有“如许美妙之物”却无人欣赏?将它们创造出来似乎没什么“目的”。(P89)这是对设计论投下的第一个疑惑。在南美这块新大陆,达尔文发现一种寄生黄蜂,它将刺死后的毛虫作为食物来哺养自己的幼虫。达尔文一直对这种低等生物无法忘怀,因为它的“恶行”似乎背离了造物主的“善”。 航行途中,达尔文收到了刚刚出版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1832)。在第一卷中,赖尔讨论的是地球表面的逐渐变化。在第二卷中,赖尔讨论的则是,在变化的环境中,生物是否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作者给出的结论是,环境的压力或改变只会让生物灭绝而非变化。联想到刚刚挖掘到的化石动物大地獭,达尔文对物种的绝灭印象深刻,但随着旧物种的灭绝,新物种如何产生却成了一个神秘的问题。这是达尔文首次模糊地接触这一课题。 1832年12月,军舰来到南美的最南端——火地岛,达尔文初遇传说中的野蛮人并且震惊无比,“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啊,甚至比野兽和家养动物的区别还大”。(P101)顺便提及,当时的小猎犬号上就有三位已经文明化的火地岛人,他们是舰长菲茨罗伊上次航行期间在火地岛带回的土著人,菲茨罗伊之所以承担这次航行使命,起因就在于想把这些火地岛人送回他们的家乡以便在当地传教。同样是火地岛土著人,但两者的差异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这当然证明了人类本性的可塑性。这一事实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4年5月,军舰驰入南美的科克本海峡,对着那些“起伏不平、积雪覆盖的峭壁”,还有巨大悬崖下的一个小棚屋,表明曾有人迹在这儿出现,达尔文陷入了沉思。这是一片多么荒凉的自然,而人在这种环境中又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在这里,人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主人”。(P119)这是对人类中心说的首次质疑。接下来的一年,1835年2月20日,达尔文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大地突然颤动,许多人的生命瞬间被夺走。地震持续时间虽然只有两分钟,但它对心灵带来的冲击却持久而又深远。达尔文立刻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如果这场灾难发生在人口密集的英国,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地震和火山爆发之类的灾害恰在提醒我们,人类犹如居住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上方,或者在薄薄的冰面上滑行,其脆弱和不堪一击令人心悸,但这却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它成为达尔文思考物种问题的重要依据。终其一生,达尔文都在深刻思考痛苦问题。如果说,传统宗教正是因人生的痛苦问题而兴起的话,那么达尔文思考的结果却是抛弃了宗教信仰。因为神创论与生命的痛苦难以协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