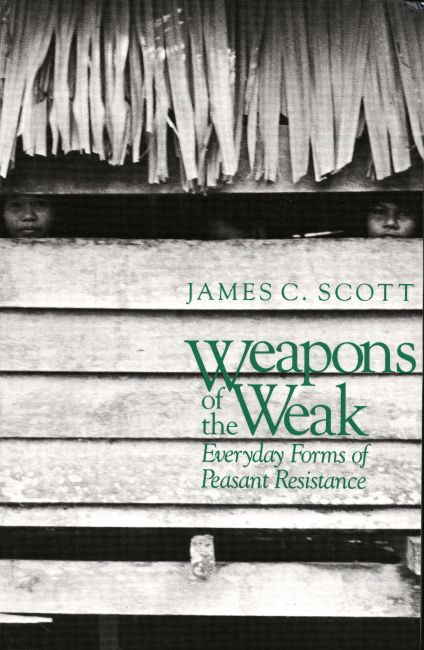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以对前资本主义乡村社会的研究而著称。继其闻名遐迩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他又以《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两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抗争与农民政治的灼见。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但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他们也不是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募、税收、劳动、土地产出的贡献者,至多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存在”。农民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注,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长久以来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亦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农民在统治者或统治精英如此的关注目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至多是作为怜悯对象而存在的。作为农民行为选择的顺从抑或反抗也是由此而进入研究视野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而这类所谓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与向他们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的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作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斯科特并不同意将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的。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正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却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理解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的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被忽视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做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以及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高度认同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去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它们之间持久存在的张力及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从《道义经济》到《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细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对垒的对手,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甚或“弱者欺凌更弱者”,但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弱势者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而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未损,反而因此增加了镇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从副标题的消失所想到的 这样一部蜚声国际学术界的著作在中国首次出版即遭遇“腰斩”——作为点题之笔的副标题不见了。不仅在封面上消失(通常被解释为出于美观的考虑),而且在所有地方——扉页、版权页、译后记中——通通消失了。更匪夷所思的是,连版权页上必须出现的原著英文书名也遭拦腰一刀,只剩下“Weapons of the Weak”这一象征性标题,从而中文读者连该书原貌也无从得知了。 作为译校者我们不禁疑惑:一本译著,一本学术著作,一本以马来西亚农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名著,用得着这么草木皆兵吗?我们也自然会恼火,因为这是对原著作者的阉割和不尊重,是对中文读者的欺瞒和不负责任。如此“一刀切”的方式全无严谨、负责的学术精神,但我并不想而且也不能简单地指责出版单位或编辑人员,他们有着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和未必能完全理解的苦衷。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考追寻其背后的逻辑,而这也和斯科特所研究的支配与抗争话题有关。 勿庸讳言,删除或修改有关字句是出于现实和安全的考虑,出版者必须顾及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经济效益。我们看到并可以理解的是来自权力和来自市场的压力在此强强联合,而且实现了双赢,而这正是阿伦特所分析的“消费社会”的逻辑窃取了公民社会和行动的地位,使“一个共同的公众世界黯然失色”。作为经营者的出版单位,面对既安全又有钱赚的事,何乐而不为呢?而有关的主管部门的确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就不由得被管理者先就心颤腿软了。预先删除有可能带来麻烦的内容,防患于未燃;主动自觉地自我约束、自我规训和自我整饬。这种人们看来似乎“过敏”的做法无疑来自于内在的恐惧,那么忌惮和恐惧又从何而来? 哈维尔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蔬果贩子在其店铺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当然并不表明他真的在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真的相信有这么回事。勿宁说这标语如同葱头和胡萝卜一样是从上面批发下来的,菜贩只有照贴不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或者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不做反倒有异端之嫌。和生活中许多其它事一样,贴标语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通过此例哈维尔想说明因为恐惧而生活在谎言中的方式,每个人都被编织进政治和意识形态之网,是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哈维尔的分析传达出极权社会中这种恐惧是深入人心的,也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是恐惧成为了行动的原则。人们在这种境遇下生存会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它的意识形态,遵循它所强加的规则,忍受并习惯其奴役,特别是将被迫转变为自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恐惧不独为被统治者所具有,它是双向度的存在:支配者害怕被支配者,被支配者害怕支配者;或者说是权力本身的恐惧和权力统治下的恐惧的共存。前者表现为没来由的、无规律可循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敏感”;后者则是“过敏”性的预先防范、主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整饬。 斯科特的著作讨论的是支配与反抗关系中的“弱者的武器”及其内在逻辑,在深藏于人心的普遍恐惧中,人人都可能成为“弱者”,比这更令人悲哀的是如果连“弱者的武器”也不拥有,就甚至不如只能使用“日常反抗形式”的农民。这不应该是一个日益走向民主、开放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现象,这也和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2007-4-9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