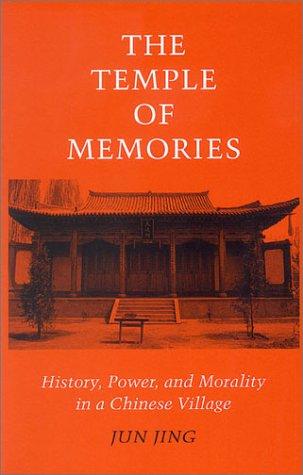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一提到“历史记忆”脑子里就会映现出书库中叠床架屋般的典籍文本。我们长期习惯性地陶醉于用浩如烟海来自诩史籍储藏的无涯浩瀚,岂不知典籍的官史脸谱与政治剪刀的杀伤力早已为近代学人如梁启超辈以“断烂朝报”形容之。因为典籍储藏有意或无意的精英化选择策略,极易把历史记录演绎为某种虚构矫情,粉饰雕琢的神话,历史经过刻意剪裁被放到了同一号码的筛选模具中批量生产出来。与此同时,官史修纂的庞大机器在历朝历代的运作,又在不断绞杀排斥着平民生活史的日常性格,甚至连文人的私人日记都变成了拼贴官方记忆的脚注与文本,滔滔如海的历史古籍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伪造记忆的流水线。在伪记忆全面阉割了历史解释的能力之后,乾嘉钩沉学的出现相继耗去了几代学人的光阴和生命,对历史的证伪居然辉煌为一门专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颇为无奈的抗拒姿态,因是之故,对经典文本垄断历史资源的超越,几乎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家们破茧而出,独辟蹊径的一条必由之路。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一提到“历史记忆”脑子里就会映现出书库中叠床架屋般的典籍文本。我们长期习惯性地陶醉于用浩如烟海来自诩史籍储藏的无涯浩瀚,岂不知典籍的官史脸谱与政治剪刀的杀伤力早已为近代学人如梁启超辈以“断烂朝报”形容之。因为典籍储藏有意或无意的精英化选择策略,极易把历史记录演绎为某种虚构矫情,粉饰雕琢的神话,历史经过刻意剪裁被放到了同一号码的筛选模具中批量生产出来。与此同时,官史修纂的庞大机器在历朝历代的运作,又在不断绞杀排斥着平民生活史的日常性格,甚至连文人的私人日记都变成了拼贴官方记忆的脚注与文本,滔滔如海的历史古籍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伪造记忆的流水线。在伪记忆全面阉割了历史解释的能力之后,乾嘉钩沉学的出现相继耗去了几代学人的光阴和生命,对历史的证伪居然辉煌为一门专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颇为无奈的抗拒姿态,因是之故,对经典文本垄断历史资源的超越,几乎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家们破茧而出,独辟蹊径的一条必由之路。清末的考古发现使得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初步揭示了官史文字记忆之伪,但是中国近世学术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去勘破人类行为之谜则起步甚晚,至多可追溯到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们。因为中国的史家大多有官修文字癖,正统史学的训导使学子们往往热衷于用经典去构筑历史的记忆空间。 无人否认,中国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依赖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知识转换系统,人们身处其中不仅记忆一些与过去相关的信息,而且把过去作为道德理性判断的基础。但是历史记忆的过程并非全然是通过文字来达致的,这在民间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龙船竞渡,新年庙会和搭台社戏年复一年仪式化了的表演同样可能是社会通过动态的方式记忆历史、相互认同的感性表现。仪式认同的力量决不小于文字认同的能力。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项研究,冠以名曰“神堂记忆”,副标题是: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权力和道德,书名即已清晰界定出了作者的立场,它会坚拒对官学文本记忆的传统迷信。“神堂记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记录所能覆盖,它尚涵括着仪式行为,家谱书写,痛苦的口碑叙事,复仇的政治与对仪式意义的冲突性领悟等等,这也就注定了它必须从草根社会的百姓们口中眼中泪中笑中去感受些什么,必须把活生生的富有血肉灵性的日常生活史还给人类。同时也就意味着必须放下都市人的架子,去和村里人一起去感受歌哭,感受让人动情的痛苦与欢乐,对村史记忆的参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枯坐宅中的依稀想象。不只一次,作者悠悠然地给我讲述过蹲点山村时孤旅行踪般的寻访轶事,他曾笑着说,那年参与拜神,为了按规矩抖落头上的红布条,磕了十几个响头,直到头上出血才完成仪式。那真是个苦地方,大葱蘸酱是常饭,回京后身上不但长满虱子还落了腰疼病,也许皮肉之苦总会这样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人类学者。从他略带调侃的叙述中,我却读不出些许轻松,而是每每为之肃然,进而感悟到了什么是学术真正贴紧了生活脉搏后的那份灵动与自信。 “神堂”的具体形象是一座孔庙,这座孔庙位于甘肃永靖地区的一个名叫大川的小村落中。传说村里的孔氏家族是从山东曲阜分流出的一支,另一支则流向了广东。孔庙自然变成僻居偏地的孔氏后人超越时空,追慕先祖的记忆象征。可是作为孔氏后裔血脉遗踪的一点证明,私人对先祖的仰慕在甘肃一隅仍不能变成远离尘世喧嚣的纯粹精神行为,田野追踪不能仅仅简化为一次封闭的心理实验,在单调重复的生活中,大川人头脑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就是孔庙在批林批孔时的毁灭与改革开放后的重建。象征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信仰的湮没,重构象征的奋斗史照样可使精神之火亮耀如初。然而一毁一建的历史间歇性时差却重塑了孔家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怪不得当年杜克海姆的同事哈尔布瓦奇斯(Maurice Halbwachs)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吼道:忘记个人吧,任何对个人记忆之源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形式,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 记忆的社会结构论被作者巧妙挪用到了审视“神堂”重建的过程之中。他发现,孔庙的毁灭无疑是对孔氏家族权威的沉重打击,但权力张扬的沉寂恰如动物的冬眠,并未伤筋动骨,神堂重构尤如记忆精灵的复活,孔氏仍会重新支配社区生活,只是其权威的控制指向确已今非昔比,记忆的内容也受到了制度大环境的强烈模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孔庙祖先环伺孔子牌位的“祖庙现象”在新庙格局中悄然改变了,孔氏祖先的牌位被挪至角落,孔子各姓弟子纷纷簇拥在了师父的周围,占尽了大川先祖原先享有的风光。按照管理人的说法,这种空间安排的目的乃是向游人展示中国文化共通鼻祖的形象,孔庙变成了文化教育中心而非祖庙,祖宗脉系的荣耀就这样为普世化的神圣光环所遮挡。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