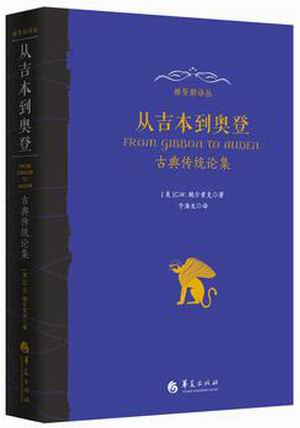 美国历史学家G.W.鲍尔索克的《从吉本到奥登: 古典传统论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8月)收入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至2007年间发表的17篇论文,内容主要是讨论以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为中心的从18世纪到20世纪文史名家(包括爱德华·吉本、雅各布·布克哈特、作曲家柏辽兹、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和英国大诗人奥登等)与古典传统的关系,“它们不仅反映出我的个人兴趣和研究领域,也例证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古典时代在现代思想与文学中一直很重要,而且在今天仍然重要”。(作者撰写的“序言”)关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学与古典时代的关系,从诗意化的肯定与赞美的角度来看,恐怕没有比爱伦·坡写于1831年的《致海伦》中的诗句写得更为动情和更为优美,虽然作者的初衷并不是关于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海伦,你的美在我的眼中/ 就像昔年尼西亚的帆船,/ 在馥郁的海上轻柔地 / 载着困倦思乡的游子,/ 带他回到故国的海岸。/ / 我在绝望的海上漂泊了太久, / 你风信子色的青丝,你古典的脸庞, / 你水中仙子的绰约召唤我回家, / 回到从前希腊的荣光, / 和往昔罗马的盛况。”写这首诗的时候,作者只有22岁,自称此诗是为中学一位同学年轻早逝的母亲简·斯坦纳德夫人而作,写的是“我的灵魂的第一次纯洁、理想的爱”。末两句“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也有译作“光荣属于希腊;/ 伟大属于罗马”,并广为流传。难怪美国古典学家、文学史家吉尔伯特·海厄特的名著《古典传统: 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0月)把爱伦·坡的这两段诗作为卷首语印在扉页,这部博学多识的著作强调指出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人对现代西方的影响是最强烈和最广泛的。但是,鲍尔索克心目中的重要性恐怕不同于海厄特说的“就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他更为关注的是古代史研究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意义,同时也更关心的是希腊、罗马在欧洲和北美历史上的影响力,他更敏感的是现代世界对古典时代的各种解释以及这些解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在所谓的“家园感”方面,他没有海厄特那么普遍化和理想化。  其实,哈罗德·布鲁姆在给《古典传统》写的“序言”中已经说了,海厄特关于我们的世界是“希腊和罗马的直接精神后裔”的说法在六十年前就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在2013年更是很不准确,但是他几乎不觉得这是该书的缺陷,他认为与这些论断相比,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绘的欧洲文学中的种种影响和联系。或许可以说,在古典时代与现代世界之间,我们除了对人类昔日不朽的精神心怀敬意之外,更应不断加深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关于古典传统的影响,鲍尔索克显然更看重专业性的实证研究,正如他在本书“序言”开篇所言,“构成本书的17篇论文,源自对古代世界及其历史更专业化的研究”。 三十年多来,作为古希腊史、罗马史和近东史专家的鲍尔索克一直对吉本研究情有独钟,原因固然是因为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离不开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认为该书提供了相关的历史性解释和说明的非凡标准(“序言”),他还曾经主编论文集《爱德华·吉本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同时,他非常关注的是对于18世纪的古罗马研究而言,曾经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和因素。这种关注也延续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吉本也仍然发挥着作用。以吉本为出发点和某种意义上的中心形象,鲍尔索克从一个相对独特的角度开辟了古典时代与现代思想的对话语境,他一直强调吉本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9年,我在悉尼国王街一家旧书店买到一套1891年伦敦GeoreBell&Sons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七卷精装小开本,是Bohn’s Standard Library文库中的一种。据该版前言,它汇集了Guizot、Wenck、Schreiterhe 和Hugo等多家注释,以帮助学生阅读和理解这部名著。颇有意思的是,我买的这套《衰亡史》每一卷的扉页都贴着一张标签,原来是英国一间学校于1891年颁发给在历史学科目中获奖学生的奖品,上面写有该生和校长的名字。这也可以看作是这部史学名著自问世之后声望巨大、影响深远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作为颁发给学习历史的优秀学生的奖品,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所能期盼的最大安慰与荣誉。正如鲍尔索克所说,吉本在今天的声誉比他生前更为稳固,《罗马帝国衰亡史》继续被重印和阅读。 在第一章“吉本的历史想象”中,作者在开头就指出,《罗马帝国衰亡史》提供的史料信息并不总是准确的,吉本的学术分析结论也没有超越他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发现的东西,因此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并不把它当作一个学术性资源”。那么,鲍尔索克在这篇论文中实际上是试图回答吉本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什么是吉本的弱点与伟大之处?为什么《罗马帝国衰亡史》能成为历久不衰的史学巨著?似乎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很快就引入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古罗马史专家特奥多尔·蒙森的研究作为对比,从蒙森对吉本的评价和敬畏中提炼和理解吉本的历史整体观——鲍尔索克更愿意称之为“历史想象”。(5页)令19世纪的理查德·瓦格纳夫妇印象深刻的是,吉本对于历史人物的个性的洞察力,以及对于他们的斗争的戏剧化展现,这要归功于吉本的历史想象;20世纪杰出的喜剧作家乔·奥顿也同样对这部著作展示人物与事件的戏剧性特征有深刻印象。对于20世纪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来说,他在自己收藏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写满带有批判性目光的详细旁注,但是在总体上他非常欣赏作者的历史视野,并从这部史著中发现了诗歌。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最杰出的罗马史研究专家罗纳德·赛姆也和他的前辈蒙森一样,深受吉本的影响——鲍尔索克说他的视角、历史观和历史想象都是彻头彻尾的吉本风格。(参见6—9页) “那么,现在让我们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什么让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历史想象如此特别……?”(9页)在分析了吉本的性格、对自我的认识之后,作者认为在吉本心目中,真正重要的是以一种既使人愉悦又能给人教益的形式呼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吉本对传统学术研究的细节考证缺乏兴趣,他从现代作家而不是古代作家的文本中引用古代材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位批评家以“抄袭”为由对他提出指控。吉本对此作了有力的回应,鲍尔索克一方面承认吉本的治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理应受到指责,另一方面则通过文本分析更详实地指出吉本不囿于史料考证而在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所产生的历史叙事的伟大价值——我的理解是,吉本为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和人物的复活提供了合适的舞台与演出的脚本。最后,鲍尔索克回到特奥多尔·蒙森,以这位杰出的罗马史研究学者的一封信件表达对吉本的认识和敬意。(26—27页)蒙森当然非常了解吉本在处理史料方面的缺陷,但是他越到晚年就越认识到那种来自既要尽情发挥历史想象力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内在冲突的紧张感。他在那封信中承认吉本是无与伦比的历史学家,达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但是并不回避他研读史料的欠缺。鲍尔索克说,蒙森清楚地知道,如果吉本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学者通常会做的那种研究,那些伟大的观点很可能永远都不会产生,这正是蒙森在晚年感到困扰的一种悖论。“通过认识吉本的弱点,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为什么如此伟大。正是这些弱点使得那种强大的想象力得以自由发挥,并创造出构成《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那些无与伦比的人物形象、高妙的戏剧艺术和生动的场景。”比较吉本与蒙森,鲍尔索克的结论是“虽然堪称是现代最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但在罗马帝国的历史创作方面,特奥多尔·蒙森完全无望与爱德华·吉本匹敌。”(28页)读到这里,不无感慨的是在学术体制化远甚于蒙森时代的今天,伟大的历史创作更是完全无望。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鲍尔索克自己走的是实证研究一路的,同时也会想起前述哈罗德·布鲁姆给海厄特《古典传统》写的“序言”,这都是使人动容的学术之魂。 蒙森在那封信中认为吉本在历史创作中注入了人性的基本原则,并以“庄严的冷笑”的记述风格为那段走向腐败、堕落和政府与教会越来越专制的数百年历史打上了坚固的烙印。(27页)这也是在古典时代、吉本与我们之间有所关联的重要方面。早有论者指出,虽然常见的看法是认为吉本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之于基督教与野蛮人(鲍尔索克也持这种看法,见291页),但其实吉本自己对此并没有一贯的和系统的说法,而在论述罗马帝国在公元2世纪达到鼎盛但同时也是衰亡的开始的时候,他认为关键还是在于罗马的政治体制,即“奥古斯都体制”(Augustan Settlement)。奥古斯都尽揽大权,建立禁卫军作为威慑、镇压的力量,以独断专行的意志支配国家、奴役臣民,使罗马原有的法治和自由精神荡然无存,基督教与蛮族的兴起只是加速衰亡的外部因素。我们知道,罗马奥古斯都时期出现了官方极力钳制历史写作自由、在历史研究中设置重重禁区的思想专制现象,在那种高压氛围之下,“历史变为缄默,甚至对重大的事情也不吭声,只知以阿谀奉承保护自身。……为了逃避检查甚至死亡,最安全的办法是根本不写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内战和帝国早期的历史”。(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115~116页,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众所周知,吉本深受古罗马史家塔西佗的影响,无论塔西陀如何热爱罗马,还是无法忍受到处蔓延的专制对自由的剥夺,更无法忍受看到遍地的人民愿意放弃自由而对专制统治者阿谀奉承。陷落在专制与独裁中的罗马,何来的“伟大”与“光荣”?因此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就是以自由对抗奴役、以法律对抗暴君意志。英国思想史家约翰·布罗在他的《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黄煜文译,商周,城邦文化出版,2010年)一书中,从希罗多德史学中揭示出这个主题(见35页),该书第二十三章“历史是自由的故事”更集中论述了自古代以来欧洲的自由观念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线索。  第十六章“一个现代的伊索”的主角是2007年去世的堪称伟大的波兰记者和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鲍尔索克的这篇论文也是发表于2007年;应该说,是卡普钦斯基与希罗多德的关系深深地吸引了他。2004年,卡普钦斯基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作品《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乌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讲述的是作为新闻记者的他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采访旅程和他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足迹的追寻与思考。在鲍尔索克看来,卡普钦斯基把希罗多德看作是全球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他以独特的方式使自己与希罗多德合为一体,他的这部书似乎就是20世纪的希罗多德的自传。所谓“现代的伊索”,指的是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令人窒息的波兰共产党统治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卡普钦斯基”“在波兰审查制度下形成的擅长春秋笔法的风格”,他希望“敏锐的读者都能发现其作品中显然存在的潜台词”。这种笔法来源于那个连希罗多德的《历史》都被禁止出版的文化高压环境,卡普钦斯基说那时“我们所有的思维,我们的视角和阅读,都受到了一种类似于对影射的迷恋的影响”。(280页)鲍尔索克说卡普钦斯基从未放弃过希罗多德寓言写作手法,“对于一个在充满镇压和迫害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282页)因此,在讲述居鲁士和大流士有意派出战斗力很弱的部队投入战斗的时候,卡普钦斯基想讲的是对士兵生命的无情利用,甚至引发了对于东德和波兰当局利用人们向往有意义的生活和获得某种自由度的心理而培养间谍的思考——事实上,他本人在这段旅行期间也正在担任波共的情报员。(283页)因此也可以说,存在于卡普钦斯基与希罗多德之间的那种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所塑造的。 最后出场的是奥登,带着他写于1966年却到了1995年才得以公开发表的《论罗马帝国的衰亡》,鲍尔索克似乎要以此向吉本表达最后的敬意。事实上,奥登在那篇文章中也像他所熟悉和引用的吉本那样,思考罗马帝国衰落的各种原因,并且力图弄清楚“帝国最初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是否存在从长远来看,必然导致其灾难的某种基本缺陷?”(309页)其实,奥登早在1944年为加拿大历史学家科克伦的《基督教与古典文化》写的书评中就指出,“我们的时代和奥古斯丁时代并非全无相似之处:计划经济社会、暴徒或官僚机构的专制独裁、通识教育、知识、宗教迫害,所有这些都存在于我们的时代”。(奥登《序跋集》,45 页,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鲍尔索克在文章中谈到这篇书评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句话,可惜的是没有完整地直接引用它。但是奥登显然更关心的是他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危机,他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被一个感觉所困扰,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无论被贴上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标签,“都将走向崩溃,而且这很可能是一个必需的过程”。(325页)最后他说“我不知道在我死去之前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我不会喜欢那种情形”。(同上)还有比这更悲观的的现实关怀吗? 有人说奥登在30年代因思想激进而颇有政治激情,到了晚年而迷途知返,祛除了政治信仰与激情,是读蒲柏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知道,奥登最后完成于1972年的《序跋集》是“献给汉娜·阿伦特”的,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与阿伦特维系着政治性批判思维方面的联系。1968年奥登为英国社会改革家亨利·梅休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的再版写了一篇书评,也充分表现出他在晚年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之情。 从吉本到奥登,不可舍弃的是对古典传统中的自由与奴役主题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