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右)与宿白先生合影(摄于2008年5月23日下午,宿白先生府上)。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自1999年投入宿白先生门下,至今恰是二十年。二十年来,有幸随侍先生身侧,亲承先生教诲,虽未曾学得先生之一鳞半爪,但初觉略识治学之门径。先生遽然离去,痛失学术上的指路人,从此就需自己摸索前行了,想到这里顿觉惶恐茫然。二十年来先生的教导又一幕幕回现在眼前。 工作七年之后,我于1999年考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蒙先生不弃,有幸得入先生门墙。先生问我博士阶段的打算,由于之前一直在徐州参加西汉楚王陵墓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已将全国的西汉诸侯王崖洞墓踏查一遍,所以想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先生说:整理六朝墓葬吧。虽有疑惑,还是谨遵先生之命。从那时开始,六朝考古一直与我形影相随。跟随先生时间久了,才明白先生让我以六朝墓葬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其一,先生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学术研究必须有一定的基础,考古则必须对研究的地域范围较为熟悉。我在南京学习工作十余年,研究六朝墓葬自然较易上手。而且,六朝墓葬几十年没有人做过系统工作,需要一次全面整理。其二,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有一定布局的。先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要求学生有周密的研究计划。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想有所为,就得有所不为。考古学讲究在平面上展开,需要从一个地域、一种文化现象入手推及其他,然后才能对一个时代有全盘的掌握。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跨时代的研究。跨代研究是高级阶段,没有宏大精心的布局和强大的执行力,不能至此。其三,先生后来指出,考古研究要从最基本的城址、墓葬入手。都城、帝王陵墓虽然都很重要且引人瞩目,但博士论文是基础训练,不适宜作为研究的对象。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学习研究范围从六朝扩展到魏晋南北朝,研究对象也从墓葬扩及到城址、文物制度、美术考古,遵循的就是对一个时代通盘了解才能有所深入的理路。每念至此,更能体悟先生当年让我从六朝墓葬入手的良苦用心,今后将继续秉承先生的教诲,把自己有限的力量集中到魏晋南北朝考古研究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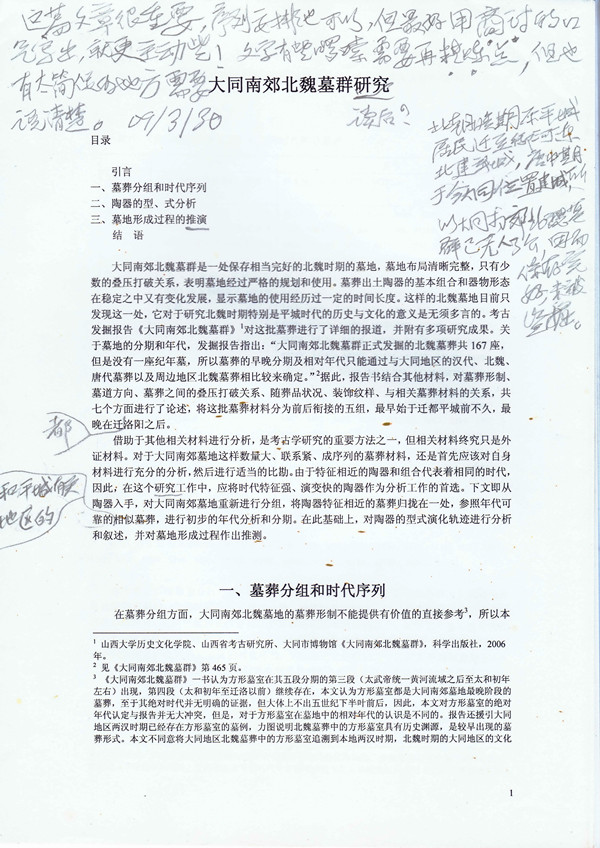 宿白先生校改作者论文的底稿(之一) 学者通常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点,但不能完全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这是我宿门问学的特别认识。读博期间,有一次,我一口气问了先生好几个问题,先生的兴致也很高,一一解答我的问题后,反问我为什么对这些考古问题感兴趣,我脱口而出:“好玩。”说完就有点后悔了,学术是严肃的事情,怎么能说好玩呢?何况是在先生面前。没想到先生说:“好玩就好办了。”后来的学习和研究在收获之外,也有艰辛,还有彷徨和不解,让我懂得单凭“好玩”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兴奋劲儿,“好办”不等于能“办好”。 现在经常听到的话就是:有兴趣就行。这句话,初听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要是完全跟着兴趣来,就不一定合适,甚至还很不合适。兴趣为人之天性,多属浅表层次,是一种自发式的喜欢,实际工作时,则需要坚强的自持力,需要不停的重复和仔细的琢磨,科研工作更是一种寂寞与繁重的劳动,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永葆活力的思辨,需要数年如一日的连续劳作和思考。不是兴趣,而是对学术真谛的不懈追求才是永恒的动力。兴趣若不能化为恒心,必不能持久。而且,既然是兴趣,可能就有片面性,对某事某物特别投入,就意味着对他事他物的忽视,也就失去了平等心,这对做科研工作是不利的,尤其是对考古学的学习不利。 考古学特别讲求真实性。考古学是可以验证的学科,新的出土资料可以证明以往认识的当否,因此,考古学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学科。这个学科忌空谈,不鼓励肆意解释和想象。考古学首先讨论的是年代问题,所有的讨论必须基于正确的年代,否则,再高妙的理论,再美丽的想象,都很可能沦为一厢情愿。即使研讨对象的年代可信,还会面临出土状况不明,或历史文化背景不明等限制,特别是欲对流入中国的外来文物进行讨论时,将相当困难乃至危险。这个时候,如何将自己的兴趣乃至欲望控制住,尤显对学术理解之深浅。先生年轻时曾对三代考古感兴趣,跟孙作云先生学习过神话,也写过《颛顼考》等深具学术分量的论文,但先生后来转向了历史时期考古。我曾请教过先生其间的原因,先生淡淡地说:三代考古的许多年代问题还难以解决,历史时期则不然,后来系里和教研室又给安排的是历史时期的考古教学工作,所以就转到历史时期来了。先生还说过,他很喜欢中外交通,并跟随冯承钧先生系统学习,但先生未曾写过一篇有关中外交通的正式论文。先生说有兴趣是一回事,真正从事研究是另一回事。先生的讲义未刊稿《考古发现与中外文化交流》虽只有百余页,却系迄今中外交通方面与历史背景结合最贴切的考古论著,而当初先生连这个讲义稿都不准备出版,这是一种何等的学术考量。兴趣在先生那里一直得到呵护,但被控制在适当的限度内。先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在学术格局中更重要的方面,并着力推进学科的全面发展。先生不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古代建筑、中外文化交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方法论的总结,而且奠定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基本框架,称先生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山之祖是一点不过分的。如果先生放任自己的兴趣,可能不会有如此全面、巨大的成就吧,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也势必受阻。虽然没有先生的天纵之才,也没有先生的高瞻远瞩,但我有幸亲炙于先生门下,就要学会管控自己的心性,不放任自己随着兴趣而奔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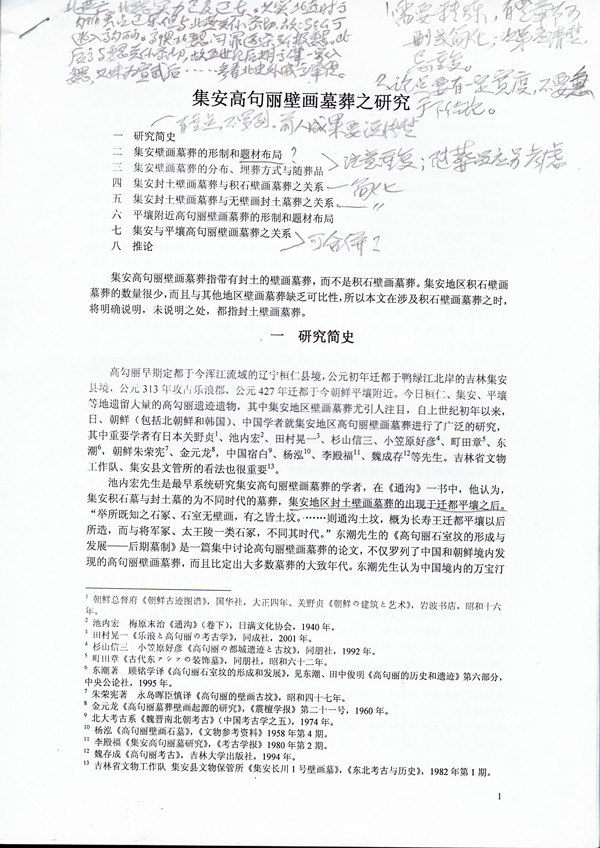 宿白先生校改作者论文的底稿(之二) 治学需有宽广的格局与心胸,是我追随先生二十年最重要的认识。到北大读博前,我参加过几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如郑州西山遗址、武进寺墩遗址、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也有过编写简报和撰写论文的经历,并且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这既让我对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产生了不少困惑。举例来说,发掘了资料异常丰富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后,我结合文献讨论了墓主身份、玉器传承、玺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始终觉得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之后似乎还隐藏着更大问题,但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听说论文代表的是一个学科的前沿,我发表的论文未必如此,但我找不到自我革新的方法,我需要高人指点,否则我的研究只能在低层次上简单重复,倒不如弃了学术。 这些想法我虽没有直接跟先生提过,但先生用自己的研究实践祛除了我的疑惑,那就是考古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必须将考古研究放回到历史大背景中去,舍此别无良途。考古发掘和考证当然重要,但能与历史大背景妥帖结合的考古研究才是好研究,不然则否。表面上看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这个要求的重点,并不只是在考古,更是在历史。掌握历史大背景,谈何容易!天生大心胸者罕见,后天更难培养。没有断然的、连续的自我突破,大心胸不可得。何况人文学科的发展日趋支离破碎,这与大心胸颇背道而驰。因此,这个要求是极高的。没有大心胸,大历史背景难现。没有大历史背景,触目所及都是问题,那就有写不完的文章,出不完的书。何况考古发现多零星琐碎,极易将人引向琐细问题,使人欲罢不能。李白有诗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来”,先生的手录极尽磅礴奔放之势,诗与书相得益彰,这正是先生治学风格的写照。先生的研究生涯长达七十余年,论文数量并不算多,但篇篇所论都非止具体问题,而皆是见微知著、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能入先生法眼的,必然是重大问题。能让先生动笔的,必然是紧迫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先生关心宗教研究,但对道教极少涉及,也没有写过关于西南地区佛教石窟寺的论文,我曾就此请教过先生。先生说:佛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自己的宗教,解决起来难度要小点;与中原北方地区相比,西南地区佛教石窟寺属于次要、而非主要问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先解决中原北方地区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格局问题,还是一种担当,更是融通考古与历史的自觉。佛教石窟寺研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牵涉到佛教史、思想史、雕刻艺术、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等诸多学科,先生以一己之力创设了佛教石窟寺考古学,为中国佛教石窟寺建立起完整、清晰的时空框架,使基于佛教石窟寺的相关研究获得了坚实基础。古人有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想就是先生之所谓也。没有博大的心胸,没有深远的规划,没有雄厚的实力,没有超人的智慧,没有将勇猛精进化为平常之心,纵有过人天赋,也难以取得如先生这般的巨大创获。先生的几本专著都是由数篇至十数篇举足轻重、力透纸背的论文构成。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的论文都代表先生就某一研究方向所作高屋建瓴布局的一部分,假以时日,先生会对各个方向展开研究,只是人生有时而尽,遂留给后人无尽感叹。 先生是不世出的大学者。先生学术考量的起点非常之高,先生的识见非同凡俗,先生知识宏丰而无畛域,治学风格雄浑厚重,治学方法无迹可寻。先生的学问是大海、是深山,先生的智慧如日月无所不照,先生一生虚怀若谷而从不喧嚣,先生的话语和研究为后来者贻则垂范。先生之气度与胸怀,非言语所能描摹。先生是我终身景仰的丰碑,永远追随先生的脚步,方能让我不迷失学术方向,让我尊重而不迷信任何学界权威,让我不至汩没于时下各种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想和潮流之中。  作者(右)与宿白先生合影(摄于2016年1月17日傍晚,宿白先生府上) 宿门问学二十载,是亲身感受先生浩瀚无涯学识、宏阔深远格局、雄浑邃密学风和从容调伏一己之趣的二十年。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从心所欲而允执厥中,成就了继往开来的大学问,是学者中的圣哲。先生翩然往矣,我将无从问学,何其之不幸也!我以平庸之质,随侍先生二十年,又何其幸哉!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