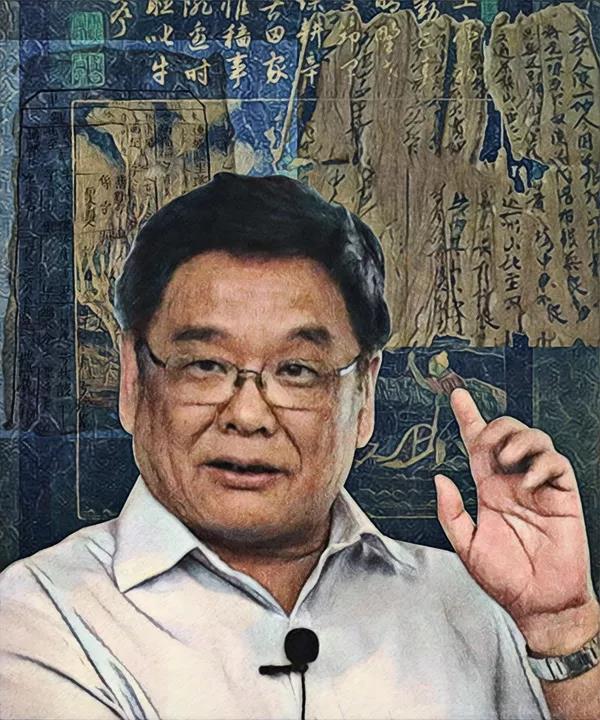
刘志伟(蒋立冬绘)
采访︱赵思渊 我们有兴趣您是怎样走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路的。您曾经和我们讲过您初次认识您的导师汤明檖先生时的情景,您说进大学不久,在开门办学时,和汤先生住在上下铺,每天劳动之余,见汤先生坐在床铺上点读《宋史》,我们当时听了很动容。您也曾片段地提到过曾经有财税实务工作的经验。我很感兴趣,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您对市场、赋税这方面问题的思考? 刘志伟:我父母是在一个小县城从事财政金融工作的,我从小在银行的宿舍长大,中学毕业后,自己从事过财政、商业、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这些经历也许是我对经济史、尤其是财税与市场方面问题怀有兴趣的原因吧。我入经济史门之后,很早就听过李埏先生讲“商品经济史”的课程,认识到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非常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先生们有过一场我认为很重要,但后来好像没有引起太多重视的讨论,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地主经济和商品经济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引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地主经济和我们后来看到的市场二者是什么关系的思考。经济所的老师们的讨论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地主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商品经济就是在地主经济体制中发展的,他们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在过去的理论里,通常是把地主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而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是对立的,由此商品经济和地主经济也是对立的。是这些讨论激励着我们思考。 我读经济史研究生时,开始是和陈春声、戴和一起,当时老师期待我们师兄弟的研究有所侧重,分工是这样的:陈春声做市场、货币、物价,戴和做海关,我做赋税。我们同时在这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互相不断地去讨论,当时我们想的问题就特别多,这些基本构成了我们的核心问题,这段经历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影响。 而且,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深受经济学传统的影响。陈春声是到上海跟着伍丹戈先生学数理统计,而我在北京的时候就以经济所的落脚点,后来到上海的时候,是在陈绍闻先生指导下,也常跟伍丹戈先生学习,我隔一两天就去伍先生家里请教。那时候,上海财经大学的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也是我的入门书,还有他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书,是我们那个时候能够读到,可以由浅入深地去学习经济学的书。有了这些经济学基础,历史学界当时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明末清初三大家等等,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形成可能跟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有很大不同。 
经济学家胡寄窗 您刚才讲到地主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国内学术界好像都将地主视作市场的对立面?英文语境中landlord和farmer应该都可以对应地主,可以分别视作土地的领主与农场主,而在中文的社会经济史里,“地主”这个概念是不是被复杂化了? 刘志伟:这牵涉到“阶级概念”的“地主”。早期革命理论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地主,后来是讲剥削关系和政治立场。而土改实行的时候,划分地主是按租佃还是雇佣来区分。如果是雇用关系,你雇人来种地的话,有一百亩地也是富农,而若是租佃,就算是有三十亩地,那也是地主。其背后的逻辑是,雇用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的,是进步的,而出租土地是封建的生产关系,是落后的、反动的。所以,涉及的相关问题,要把它放在原本的逻辑、语境中去思考,不能脱离它。 所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史,很看重是实物地租还是货币地租,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也是在这个逻辑里面? 刘志伟:对,是在同一套逻辑里的。因为在当时学术界的话语系统里,地主经济的落后性表现在,一来它是自然经济,二来它的剥削方法是腐朽的,而与这一套对应的就是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则是跟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的。至于你问的分成租和定额租,这要从生产关系的理论上来谈,生产关系讲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讲,分成租,因为地主要分成,所以他干预生产,直接奴役农民;定额租的话,地主可以不干预农民生产。极端的例子是关于江南的“不在地主”,认为地主不再参与生产过程、不干预农民生产,农民就有可能发展出农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 我们这代人学问没有做好,但对这些逻辑是非常熟悉的。现在你们年轻的一代也许已经不理解这一套逻辑了,因为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你做研究,还是要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儿。 所以,回过头来看前辈学者的研究,有些在年轻一代看来可能是很陈旧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当时的那套认知结构中去看的话,他们其实是想要极力走出来的。比如像傅衣凌先生讲“死的抓住活的”;还有李文治先生的很多认识,现在他被视作非常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者,其实你在理解了这套逻辑之后,就明白他们是想要走出教条主义的逻辑的。 
傅衣凌先生 那么在您看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从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到后来您这一代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的转折的关键点是什么? 刘志伟:在八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学界在广东开过两次我觉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第一次是1983年,中山大学开的,主题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我当时第一次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和陈春声、戴和负责操办具体的会务。这次会议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认识了当时社会经济史很重要的一些学者,他们现在若还在世,都有九十多、一百岁了。 当时会议发表的论文,很多是比较熟悉的论述,但我的老师(汤明檖教授)提交的是关于户籍制度与小农的关系的论文。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他要表达的是,如果不了解户籍制度,谈生产资料、地租,又或是小农经济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经济史研究,大家都漠视户籍制度的重要性,而他是强调这个重要性的。这其实也是梁方仲先生的立场。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梁先生非常明确地说过,如果你不了解户籍制度、官营制度、专卖制度等等,直接讲资本主义萌芽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我老师说,你不明白户籍制度就讲小农经济,这是不通的。这种意见在当时的学者中是很少见的。我印象很深。 第二次会议是1987年在深圳开的关于区域经济史的会议。这个会的灵魂人物、实际主导者是傅衣凌先生。这个会值得一说的有几点,首先在这个会议召集到的中国、日本和欧美学者规模很大,因为傅先生的号召力很大,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学者规模的会议。当时国内做社会经济史的各方学者大多都来了,欧美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也都来了,特别是后来成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那几个人全来了,濮德培、李中清、王国斌等等。他们的发言对我们这样的年轻学者很有冲击力。其次,如果我不是孤陋寡闻的话,这次会议(是国内学术会议中)第一次是以规定发言多少分钟、评论多少分钟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开会形式现在已经成为常规,但当时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当时有些国内学者还不能接受这种开会形式。记得当时我在上田信做主持人那个组,他长得年轻,日本人开会也很严谨,同组的有我们的一些老学者,发言时间一到,上田信就喊停,他们很生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次会上基本确立了以傅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中区域研究的地位,区域研究在这时候被大家所了解,而且不那么边缘了。 
李中清 
王国斌 我的印象中,当时不论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中,还是经济史研究中,专门研究某个区域好像还是比较新的想法。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区域史或区域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史和古代史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吗,还是始终被视作证明宏观过程的案例研究? 刘志伟:当时还没有案例研究这样的认识,更常讲的反倒是“有没有代表性”。当时我们做区域研究最被人质疑的就是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你做这个地方可以代表中国么?到现在还是经常有人提出这样质疑。我的反诘很简单——哪个地方能代表中国? 傅衣凌先生写江南市民经济的时候,有人这样批评吗? 刘志伟:在社会经济史,特别江南社会经济史里,一般不会被质疑,因为大家心目中讲中国明清社会经济,说的就是江南经济,所以不存在代表性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区域经济史”的概念,我记得1987年的会议上有好几篇文章还在讨论应该怎么划区域。当时讲区域,想的是,中国太大了,区域之间差异也很大,需要分别进行研究,如果把一个一个地区研究清楚了,再用归纳的方法,就可以得出全国的情况。 谈到区域社会经济史,有两个会很关键,一个是前面提到的1987年的会议,一个是1995年在西安办的社会史的会,是周天游主办的。在西安的会上大家似乎有了一致的共识,就是区域研究是做社会史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就我个人来讲,以区域为单位来研究,在方法上,并不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物理学、生物学,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学的实验,都是在很小的对象上进行的,自然科学不会问有没有代表性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来做历史,我也从来不觉得我研究的局部是否会有代表性的问题,我比较喜欢“用区域作为我们的实验场”这个说法。 前几年讲谈社编辑的中国史丛书,翻译引入中国,影响很大。我印象很深的是上田信写明清史,其中里甲制度的内容只有一页。与此相对照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丛书中写十六至十八世纪东亚的一册(第十二卷《东亚世界的展开》),由岩见宏主编,其中至少有三章是谈赋役制度相关的(《明代的乡村统治》《税役制度变革》《乡绅支配的形成与结构》)。这一二十年里,赋役制度可能已经不是明清史研究的焦点了,那么,今天怎么看赋役制度和明清史的关系? 刘志伟:我感觉,日本学者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里甲赋役制度,主要还是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中的,而上田信,还有斯波义信这一类学者,更多恐怕要连接到欧美的传统上。上一代日本学者讲里甲赋役基本是在地主经济、乡村支配、水利这几个领域中谈。而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有很多新的东西。上田信写的这本《海的帝国》,更多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对明清历史的视野和观念的发展,但是也不能说里甲赋役制度不再是日本学者明清史研究关怀的焦点,片山刚的图甲制研究,就一直备受重视。上田信这本书讲十四世纪明帝国的构造、十六世纪社会秩序的变化,都还是从里甲体制及其改变着眼的。 但是,如你所说,明清史研究的焦点在最近几十年,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明清史研究同日本不一样,中国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过去其实对户籍赋役制度是不重视的,近年来倒是有转移到越来越多关注户籍赋役的倾向。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说明,尽管现在明清史研究的视野已经越来越拓展,但王朝里甲赋役制度研究还是不能丢。老一代日本学者研究里甲赋役制度奠定了很深厚的基础,新一代把视野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中国学者过去不甚重视里甲赋役制度的专深研究,现在把很多课题的研究再连接到这个视角,我觉得这也许是学术发展同一进程中两个分流阶段之后的汇合。 我们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解释不能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比如,像现在的医疗史、性别史等等大家认为热门新潮的研究,当然都是很好的研究领域,但就像梁先生当年批评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论述一样,如果所有这些研究不放回到当时的制度环境、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脉络中,可以非常自由地解释看到的种种现象,就难以引出最整体社会历史的思考。如果真正要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尤其要理解那个社会内在生成的结构的内在联系性、历史延续性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回到特定的时空和语境中。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我会给自己设定研究目标去弄清这个结构性的东西是什么。这需要好好想想。这也是我这两年强调贡赋体制的原因,虽然我知道这种强调甚至可能有些矫枉过正。 
上田信:《海的帝国:明清时代》 如果我们观察明清史研究的这种转变,如果要做解释,是不是有这样两个可能:一个是更多学者放弃结构化的历史解释,回到纯粹人文的历史描述的传统里;第二种是,是不是过去三十年,我们已经讲清楚了赋役制度的问题,所以不再去讲了? 刘志伟:第一个情况完全可能。这要看你做的研究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如果是人文的话,只要在情感上、思想上回到人文本身,这靠理解力、想象力,通过写作和汲取的素材就可以实现。现在这种取向确实也很明显。当然,我觉得这种努力是绝对需要的,甚至可能这个才是历史学的正途,因为历史学不需要解决那么多的伟大问题。但是我们做经济史研究,这是社会科学的领域,所以必须是分析性的。所谓分析性的,就是要通过概念框架去解释现象,要建立一套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除了事实以外,除了可以超越时空、人类始终一以贯之的人性以外,还需要落实到特定时空,落实到特定的结构中,需要用概念去表达,并且分析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的研究,我觉得不可能避开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这个结构的原理和原理背后的观念层次。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就不可能离开赋役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至于赋役制度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年的研究里有没有讲清楚,我认为没有讲清楚的地方还很多。这个看法,也许无法说服人。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负。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讲摊丁入地的文章,其中观点跟以前的讲法不一样,但到现在好像没有在意我当时表达的观点。在我看来,摊丁入地的“丁”,是一条鞭法的产物,而所谓摊丁入地,在税制上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赋税征课对象的改变,按丁额摊征地银;二是税种的合并,尤其是编派项目的合并。这两种的改变,可以是同时发生,也可以在时间上分离,先后完成。而康熙末到雍正乾隆时期的摊丁入地,主要是后一意义的改革。这种看法,对认识摊丁入地的过程及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赋役制度的研究,您关心的焦点的问题是不是跟梁先生也不同? 刘志伟:具体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同,但从大的解释来说,还是在一个框架上的。 就一条鞭法来说,梁先生强调的跟我强调的内容的确有点不同,但最基本的,比如说,一条鞭法如何改变了国家跟老百姓的关系,我是从梁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去想这个问题。过去讲一条鞭法一般说是以银为税,简单地将其看作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甚至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分析的解释。那么,一条鞭法如何改变国家和老百姓的关系,把这个问题落实到更具体的研究,我后来做乡村社会的很多研究就是从这个思考出发的,这肯定是受了梁先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说我直接重复了他的结论,影响我的,是他提出问题的逻辑、思考问题的逻辑,这对我是一以贯之的、方向性的引导,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限制,因为我没跳出这套逻辑。梁先生做研究总是讲一方面如何如何,看到其发展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拉回来,看到其局限的一面,我做研究也有这个习惯。比如说研究制度,除了要看《文献通考》《明会典》里的说法,也要把它放回到实际操作的层面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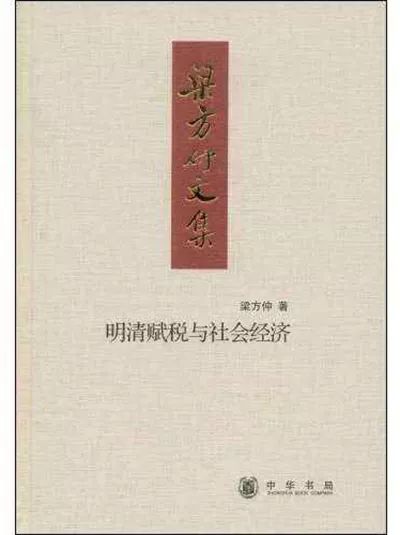
梁方仲文集之《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我觉得我基本还是在梁先生的学术脉络之下,但谈到具体看法,当然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一条鞭法的问题上,我们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对“赋”“役”的理解,尤其是对所谓“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梁先生走得更远,比如,我讲定额化和比例赋税化,我印象中,梁先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他没有把这个作为很核心的内容,而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去看的。另外,梁先生说等级丁税,我是说等级户役,这里有根本性的差异,我更强调户役,因为户是基本单位,我比较强调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一条鞭法以前,主体跟客体是同一的,之后是分离的。 梁先生的行文中,多数情况是用“税”,似乎没有一定要去区分贡赋和税? 刘志伟:对,确实是的。不过,我也不觉得要去区分,“税”“赋”这类概念,在明清文献中也没有真正清楚的区分。我喜欢用“贡赋”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只是因为“税”这个概念在近代越来越赋予了清晰的定义,并且人们也习惯从近代意义的概念上去理解和使用“税”,为免混淆,我才更宁愿用近代以后已经少用的“贡赋“这个概念。梁先生一方面指出了“赋中有役,役中有赋”这个被我理解是“贡赋”概念的特质,这已经比很多人进了一大步;但另一方面,他这种表达仍然是在“税和役”“田和丁”这样的两分法里。古人有所谓“有丁必有役,有田必有租”的说法,这样的表述,是把它看作赋役的基本分类,还是理解为征派赋役原则的表达,我倾向于后者,强调这是一个衡量均平的价值标准。表面看,梁先生可能不像我这样强调均平的价值。但其实他也是强调的。我的很多理解确实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是他引导我往这方面去想。从孔子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明代所有的赋役改革,到清代的均田均役法,都是用“均”作为一个标准,实际上均田均役法本身并没有直接解决“均”派的问题,但所有的改革的目标都是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才能达至均平的目标,用货币作为核算和支付手段也是因为均平的需要。 我觉得您很强调“均平”的概念和明清时期的等级身分秩序的关系。我想到另外一位对明清赋役制度中的“均平”概念论述非常精彩的学者——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伍丹戈先生。1980年代伍丹戈先生有一本小册子《明清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刘志伟:对,伍丹戈先生对我影响很多,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我当年在伍先生家真的是无话不聊,他们这一辈的学者跟我们谈了很多东西,具体的话其实我忘了,当年我们与现在的学生不同,我们同老师聊天只是倾听和思想,不敢做笔记,更没有录音。伍丹戈先生当时谈过很多关于江南均田均役的问题,他很强调均田均役对理解明清社会经济的重要。他谈的时候,我也是半懂不懂,只是努力去想,后来自己读史料,再做思考的时候,肯定有受到他的影响,一再思考他的问题。 
伍丹戈著《明清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 我是把梁先生的东西往前推了,推到一个离规范的经济学体系更远的地方。我们做经济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必须用规范的经济学概念,但同时,要把这些概念要往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去推。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写东西很难写,就是因为我们用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回到了这些概念原本的语境中。而梁先生用的也是这些概念,而且他是在英语的语境中思考,他说“赋中有役”,这里面就包涵了tax,但是“有役”又改变了tax的性质。而我用中文讲,就是贡赋。 另外我跟梁先生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后来关于里甲制度、保甲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从梁先生点出的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一点来的。国家跟人民的关系在里甲变质之后是怎样的?过去我们熟悉的说法是,里甲制崩溃,保甲法取代里甲法——这个说法延续了一百年左右。但是,去读文献,特别是读地方文献,就知道这个说法不对,不符合事实。我现在很高兴的是,年轻一代学者看了很多地方文献,这个事实就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了。当年只有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现在年轻一代学者都知道。这个看法不能说它有多伟大,但是,我觉得是解决了怎么样从一条鞭法解释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的改变这一关键问题, 这要感谢片山刚。我做的时候没看到他的研究,其实他的文章发表很早,但那个时代我看不到日文研究,而且我也不懂日文。后来其实对我打击很大。我原以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结果片山刚在我之前就已经讲了。但我后来认真看他的研究,发现几个关键问题上,他错了。我为什么感谢他,是因为他像是一面镜子,让我把问题想得更清楚了,他认为这是由于宗族的发展、家庭扩大化,出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我认为恰好相反。片山刚不知道户的性质的改变是因为赋税制度,看过他的研究,我就非常清楚我该怎么论述,就很容易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均平和身份制的关系,到现在除了您之外,我觉得没有人继续好好谈这个问题。其实明代文献里讲“均平”,背后是有一种对身份的预设的。 刘志伟:这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解放有关。七十年代后期,关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我们有非常多的思考,思考了半天,其实得到的结论现在看来也很平常,就是说,西方社会是人生来自由平等,而中国社会还是有一个身份制度,荀子有句话讲“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说人与动物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人不是平等的。有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入行做学问,但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都在引用这句话,所谓平等,不是我们有同样的权力,而是你在你的位置上,我在我的位置上,中国社会认为人有不同的名分、位置,我们要安分。中国社会中对“均平”这套价值,其意义不是说人人一样,而是跟你的地位、社会角色相称。我们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不同的地方。这些思考,在我们后来的研究中一直还有。 当下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对明清社会中隐含的身份秩序好像有点忽略…… 刘志伟:这就是经济史研究的尴尬之处,因为我们用的概念也好,分析体系手段也好,还有各种模型、基本假设,都是在经济学的框架下的。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主体是平等的,虽然后来制度经济学又把其他因素引进来去调整这个假设,但还是用同样的办法,把更多的因素引进来去修正假设而已。问题是,我们基础性的那套价值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简单的用加权的办法来计算,更多的还是相对的概念。 
我们在今天还有可能对一条鞭法提出新的解释么? 刘志伟:我不知道!如果问我,我认为我的研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不过,我很喜欢光纤之父高锟(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我想没有什么系统能够代替光纤,光纤是最好的,在一千年之内,我找不到一个新的系统来代替它。我这样说,你们不应该相信我,因为我本来也不相信专家的说法。”我可以说,在一条鞭法研究领域,我已经走到头了,但你们年轻人要相信,你们可以继续向前,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