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 ——杨绛 钱锺书在上海居住多年。1933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就任外文系讲师。1939年夏,在西南联大度过一段不愉快的短暂时光后,他受父亲钱基博之命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两年后离开,暂居上海,住拉斐德路609号(现复兴中路573号),杨绛的娘家则在霞飞路来德坊(现淮海中路899弄)。二人本打算休整几月就回内地,没想到碰上珍珠港事件,上海沦陷,他们就困着出不去了。此后八年,钱锺书留在上海,中途搬到蒲石路蒲园(现长乐路570弄1-9号的12幢西班牙式花园洋房),一直到建国前夕。 想起沦陷时期,杨绛心有余悸: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之前。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 钱锺书也曾作诗排解自己的苦闷情绪,诗云《古意》,内有一联:“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又有另一首《古意》,“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 钱锺书在上海暂无工作,经杨绛介绍,他做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靠给学生补课挣点家用。《家庭教师钱锺书》一文对此有过详细记载。钱锺书博闻强识,学生又没有太多考试任务,补课对他来说,不过大材小用,占不了多少时间,好不容易闲下来,钱锺书燃起写长篇小说的兴趣。1944年,在杨绛的鼓励下,钱锺书开始写长篇小说《围城》,他每天写五百字,晚上给杨绛看,修修改改,直到1946年小说写完。《围城》最开始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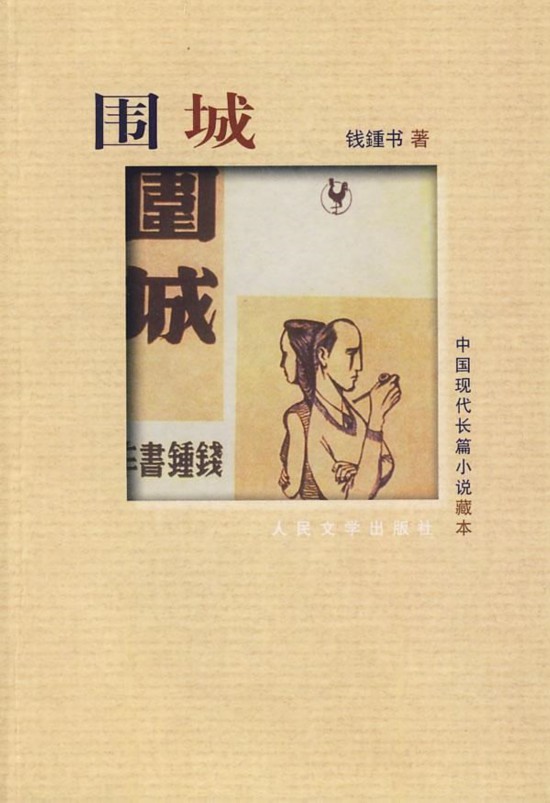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 《围城》是一部“锱铢必较”的小说,取材自钱锺书的生活,譬如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就有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影子,方鸿渐和他的朋友们,也多剪切、拼接自钱锺书的友人,但绝不等于原型。小说对知识分子有鞭辟入里的描写,对婚姻、家庭、求学等人生问题,也有清醒的看法,刚一发表,就在上海引起一些影响,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此后30年不得重印,到1980年才重见天日,引起震动。 创作《围城》期间,钱锺书还写一些短篇,被收录进小说集《人·兽·鬼》,于1945年出版。其中,《猫》影响力最大,1944年,李健吾和郑振铎策划出版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二人找钱锺书约稿,原想连载《围城》。到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没有把《围城》交付,而是把短篇《猫》交给二人。由于疑似影射林徽因、沈从文、林语堂等作家,《猫》受到了文坛的一些非议。 《人·兽·鬼》的另外三篇小说《上帝的梦》《灵感》和《纪念》被谈论得较少。《灵感》写一个“有名望的作家”荒唐的一生,是和《围城》异曲同工的作品。《纪念》一改同题小说的俗套,写小布尔乔亚的生活和婚外恋,却不聚焦于批判,而是略带苍凉的把三个主角的交集娓娓道来,留下一丝灰烬的余味。读后倒让人想起同在上海的张爱玲。《上帝的梦》则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小说中的上帝实际上是钱锺书对人类进化到极致的遐想,上帝是看似完美的人,却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他继承了人性的善恶,又因失去约束而将恶的一面发挥出来,他的自私、骄纵、虚荣,并没有因为力量的强大而改变。钱锺书在此戏仿了上帝造人的神话,用戏谑的姿态解构了神的神圣性,小说同时是对进化论的质疑,在钱锺书看来,线性上升的历史叙事并不可靠,现代人存在自以为是的性格。然而,《上帝的梦》表意过直,模仿痕迹也较重,有钱锺书自己的风格,但远未成熟。诚如夏志清所说,是“有着法郎士风格的轻浮”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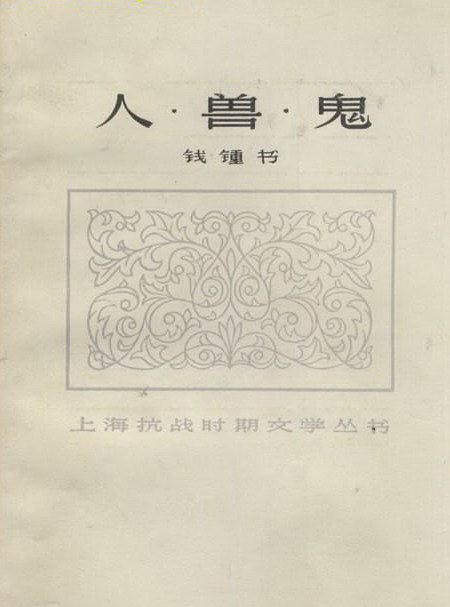 《人·兽·鬼》 钱锺书的小说常常不拘于型,夹叙夹议,反讽连连,似随笔,却又有故事的要素,他的小说和散文出于同路,都是作者观察某个群体,有什么道理想说出来,于是寄托文字,以虚入实。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是某个群体的化身,譬如方鸿渐之于孤岛时期的小知识分子、建候之于归国读书人、上帝之于想主宰一切的独裁者。小说成为钱锺书的传声筒、讽刺剧。 钱锺书深受新古典主义影响,他的小说里有英国通俗文学的影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文学盛产以毫无畏惧的年轻人为主角的小说,语言幽默、讽刺,折射世相百态,钱锺书在牛津期间读了大量这样的小说。另外,留洋经历让他能够掌握世界文学的新潮流,当一批民国作家还在为白话与文言之争绞尽脑汁,钱锺书已经在探索现代主义的技法。他在小说中影射了当时欧美文坛当红的作家,比如T.S.艾略特。《围城》里,苏文纨后来的丈夫曹先生就是研究艾略特的学者,小说还讽刺了一把艾略特,从译名就可看出。钱锺书把艾略特译成“爱利恶德”,就是爱好利益,厌恶道德。这其实代表了当时新古典主义对现代派诗人的偏见。 不过,《围城》延续的还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讽刺和比喻性的语言是它的精髓。有人统计《围城》有600多个比喻,这些比喻或是尖酸,或是幽默,个个不重样,让读者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世相的多样面貌。钱锺书利用比喻写出一部讽刺大戏,伪造学历的方鸿渐、饱读诗书的苏文执、轻声抱怨的孙柔嘉、婀娜多姿的鲍小姐,还有在她身后嘴馋的海归读书人等,都被纳入到这部讽刺大戏中,映射出抗战时期孤岛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 也是在沦陷时期,耳听刺刀划过墙壁的呲呲声,每日活在警报响起的纷扰中,钱锺书耐心完成了《谈艺录》的创作。这是一本谈论中国诗文的论艺专著,也是钱锺书第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还从事散文创作。他并不是一个专职散文写作者,写散文是“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得益于多年学术生活,钱锺书的散文引经据典,富于辩证,充满书袋气。学者范培松统计过,《写在人生边上》不到3万字的篇幅,钱锺书引经据典多达60余个。这些文章写在抗战时期,涉及战争的篇幅却少之又少,文坛上时兴的阶级、主义、革命、小资等,都不是钱锺书的主题。他既不依附潮流,也不刻意反对潮流,而是专注于他学者似的消遣,谈谈知识分子的家常。后人喜欢把《写在人生边上》称为小品文,钱锺书“名之曰家常体(familiar style)”,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迥乎不同”。 钱锺书曾把上海和这里的人写进文字里,早在1934年,他有一篇散文就叫“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文中写道: “正如‘北京人’(化石)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准还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白璧德式的人物,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 彼时的钱锺书推崇上海人,30年代上海人“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的气质给他好感,到40年代,在上海待久了,钱锺书对上海人的认识更加具体,《围城》里很多人物都有上海人的影子,比如女主角之一的孙柔嘉、点金银行的行长,唐晓芙的父母等,上海人的精明与克制、市民与物质的一面,都在里面了。 此外,钱锺书还借上海与北京的对比讽刺了一把京派文人的自我优越感。在小说《猫》中,他写道: “那时候你只要在北京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像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耀,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 抗战胜利后,上海光复,钱锺书受聘担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不必再为收入发愁。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他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教授),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跑。杨绛后来在《我们仨》中回忆道:“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 到此,四十年代走入尾声。可以说,四十年代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其中大半时光都在上海,上海是摩登与传统结合的巨型城市,乱世中的一叶孤岛,给予了钱锺书纷飞无穷的灵感。《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等作品的完成,标志着他的小说、散文创作走向成熟。 钱锺书在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后四十年。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是留在内地迎接新政权的工作,还是随一批学者远赴香港或海外,钱锺书和杨绛都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已经名扬学界,要出去并非难事。钱之俊回忆道: “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邀请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 但钱锺书都拒绝了。他爱好中国古典文化,不愿离开父母之邦,遭受漂泊之苦,为此,他甘愿枯坐板凳,收敛锋芒。 余论 钱锺书在建国后就不写小说,《围城》重印时,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 “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版《围城》,钱锺书对此不是很积极,他觉得好作品自然会被时间保留,不需要作者费力呦呵,出版社编辑好说歹说,他才答应重版。钱锺书的身上有一种二重性,他重视名节,但不追求虚名,《围城》再版之前,他的姿态都很低调,不急着出书,不卷入潮流,依然像古老士人一样手抄笔记,密密麻麻几百页纸,写完就放进柜中,很少人看。 随着小说《围城》重版、剧版《围城》热播,海内外掀起一股“钱锺书热”,打破了钱杨夫妇宁静的家庭生活,成麻袋的信寄往他们住处,各种活动邀请钱锺书,令他无法专心学问,以至于他说“浮名害我”。不过,钱杨夫妇还是客气地给读者回信,学者周绚隆说: “钱先生和杨先生属于老辈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讲老理,所有的信都力所能及要给别人回,有些读者冒失地直接找到他们家去敲门,想跟他们交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他们也很开心。” “钱锺书热”成为世纪末的奇观,也让研究钱锺书成为一时显学,钱锺书在他生命中作品寥寥的最后二十年,反而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这是历史的玩笑,也是值得观察的现象。 放在传统士人的逻辑里理解,钱锺书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尤其是在那个新旧之交的剧变时代,仍然有一些老先生和钱锺书一样,在学术上考据严谨、笔记繁复,在生活里不媚权威、待人平和,坚持自己的风骨。然而,为什么是“钱锺书”热,而不是其他与他性格相似的学者?为什么钱锺书能够成为大众眼中的文化偶像,其热度能跳出文学或学术圈子的束缚?究其原因,除了《围城》的长销不衰,围绕钱锺书构建的“记忆神话”“美好爱情”等也是关键所在。经由多方友人的回忆、著书,摆在大众面前的是一个看书过目不忘、读遍全校图书馆书籍、拥有“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钱锺书,它满足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兼济天下、经世救民,而是在智慧和人格上的高贵,书籍、媒体等共同构建的钱锺书“人设”,是这么一个高贵的化身。尽管他和真实的钱锺书有所出入。  钱锺书和杨绛夫妇 钱锺书的存在必须放在特殊的时代语境去理解,新千年后的时代产生不了钱锺书,或者说,即便出现语言功力和记忆力堪比钱锺书的学者,他也断断不可能复制“钱锺书神话”,如文化偶像一般被万千读者景仰,煜煜生辉又如在雾中。钱锺书和鲁迅一样成为转型中国的稀有动物,只有在新旧变革的时代才能酝酿那样的现象,在古士人之风遗存、欧美先进知识传来的交汇之中,在知识分子占据言论中心、互联网尚未诞生的历史缝隙中,钱锺书凭借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满足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但这种想象正随着大数据而被动摇,恰恰是在新千年后,对钱锺书的推崇已经分化为拥趸与质疑者的对立,依然会有许多人敬仰钱锺书,但这种知识神话已经愈发失去效力。与此同时,钱锺书在建国后的缄默也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批评者身处风口浪尖未必比他更勇敢。 放在如今,若有一人孜孜不倦地抄录古文,放在朋友圈,他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甚至会背负“卖弄才学”“装X”的名号。钱锺书再能背书,背不过人工智能,有再多的笔记,在互联网面前也如沧海一粟。大数据让记忆神话不再耀眼,草根群体的崛起、市民口味的变化和互联网对权威的消解,也让学者、知识分子不复往日地位,从社会发言的顶层位置滑落至边缘,钱锺书式学者失落的同时,掌握算法规律、精通草根心理的作者成为时代宠儿,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技术神话和市民趣味的结合,反权威、反精英,崇尚技术和消费的力量,用取悦消费文化和技术垄断者的姿态走入市场。于是,在此刻的潮流中回望钱锺书,仿佛民国时读书人对晚清遗老的纪念,多少有点欣赏珍奇古物的玩味。 参考资料: 钱锺书:《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杨绛:《我们仨》《记钱锺书与<围城>》 范培松:《论四十年代梁实秋、钱锺书和王了一的学者散文》 周绚隆、陆建德:《钱锺书写作<围城>之前,被称作“杨绛的丈夫”》 钱之俊:《家庭教师钱锺书》《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编辑钱锺书》 端木异:《钱锺书是怎样炼成的: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管理术》 宋丙秀:《<围城>的版本变迁及修改》 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