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取径,其在学科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它的兴起虽源于近现代史研究,但它对古代史研究的影响也日益增长,从下文所荐的三本中外学者的著作可窥见一斑。 一、【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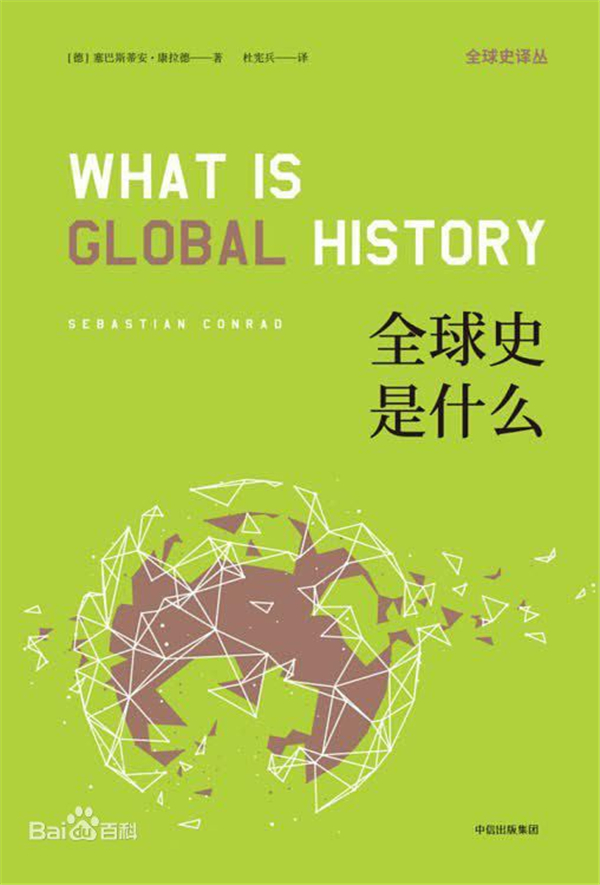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现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兴趣涉及全球史、殖民史、帝国史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本书源于作者在2013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全球史导论》,其汉译由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陈浩博士主笔,201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后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邀,将上述著作中的两章用英文进行改写,同时大幅增加其他内容,遂成本书的英文原版,在2016年初付梓。 本书共分十章,除导论外,其余各章探讨了全球史的学术脉络、与其他研究取径的关联以及自身的独到之处、全球史中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和“全球”概念的建构和全球史的政治内涵。第二章“全球性思考简史”和第三章“百家争鸣”源自作者更早出版的《全球史导论》。 在笔者读来,《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最富洞见的当属最后三章。作者敏锐地捕捉到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对全球史研究的影响和冲击。在第八章“位置性与中心论取径”中,作者剖析了“欧洲中心论”的两种主要表征模式——认为欧洲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欧洲原动力说和概念使用上的欧洲中心论。后者指历史学家即使在研究与欧洲无关的历史时,使用的诸多术语、概念和范式也带有以欧洲为中心的取向。 为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藩篱,全球史研究者势必要确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或地域空间作为考察历史的视角,诸多新型中心论也应运而生。这类新型中心论往往使用关乎文明的话语来表述其新视角,代表学说有“非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前者力图展示非洲文明在道义与文化上都领先于欧洲,后者受中国大国崛起的国情推动,试图通过追溯历史以说明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同时,“欧洲中心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9·11事件”之后,由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冲突的刺激,卷土重来,成为诸多中心论中的一种。 在第九章“世界的建构与全球史的概念”中,作者强调“世界”和“全球”这两个基本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的天然范畴,而是研究者构建的结果。有的构建认为世界是扁平的,且把全球化等同于聚合;有的则把全球碎化成若干文明;还有的主张以“帝国”或“共同体”等概念来替代全球。 作者指出,通过描述世界的概念来建构世界是历史学家建构世界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这些概念包括贸易、移民、帝国、民族国家、宗教等等。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作为对该理论困境的回应,1997年世界银行通过决议资助本土知识体系研究,从此与本土范畴相关的研究蓬勃发展。“国学”在21世纪中国的强势回归就是力证。然而,回归原生传统的做法有把文化多样性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嫌疑。不仅如此,这类披着本土认识论外衣的替代性视角也与全球史的普世性取向和对话特征背道而驰。作者主张,历史研究者应该致力于发展诸如“早期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工具,使之既保有全球史的普世性,又能够展现不同历史间的差异和多样性。 在最后一章“为谁而做?全球史的政治意涵”中,作者确认了全球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当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批判性评估。作者还提醒全球史研究者,不要过度推崇“互动”与“转移”,切忌盲目迷恋“流动性”,不应忽视现代社会的权力体系和等级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本著作的翻译质量实属上乘。译者文笔流畅,术语表达准确到位,体现了译者的全球史研究专长和扎实的中英文功底。 二、吴晓群(著):Mourning Rituals in Archaic & Classical Greece and Pre-Qin China, Palgrave Pivot, 2018。 本书作者吴晓群教授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长期从事古希腊思想文化史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本书是出自中国学者笔下的、用英文写就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作品。全书共分为六章,除去导言和结论外,主体部分的四章论及古希腊和先秦中国对死亡的认知和态度,两种文化中各自的哀悼仪式,以及哀悼者的行为举止和服饰装扮。古希腊的材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先秦中国的论述则主要取材于《礼记》。 在上文所介绍的《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作者康拉德在第三章中对比较研究的取径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比较史近年来也发生了全球转向。他认为,用比较方法来书写世界历史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即挥之不去的“目的论”幽灵和“虚构的自主性”前提。二者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独特性或例外性叙事”。 吴晓群在其著作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三大原则:首先,比较研究不应带有价值判断,研究者在从事与本人所处文化相关的研究时,不能从捍卫本文化的立场出发。其次,比较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地辨识两种文明间的异同,而应当致力于探求两个古老民族间不同行为方式的源头以及它们为何在人类历史中踏上了不同道路。最后,比较研究应当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但个案分析必须结合它所处社会的广阔社会文化背景。上述第一条原则就对比较研究中的“目的论”打了一剂预防针。 作为结论,本书作者认为在古希腊和先秦中国,哀悼表达的虽然是个人情感,但哀悼仪式绝不是个人私事,而应当由合适的人群根据恰当的程序举行。在这两个古代社会中,哀悼仪式关注的都是“此岸”而非“彼岸”的世界。在古希腊,成为哀悼的对象是死者的特权,举行哀悼仪式则是家庭成员的责任,目的在于惠及死者,以免触犯神灵。在先秦中国,哀悼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孝道,从而稳固并加强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三、【美】埃里克·H·克莱因(著),贾磊(译):《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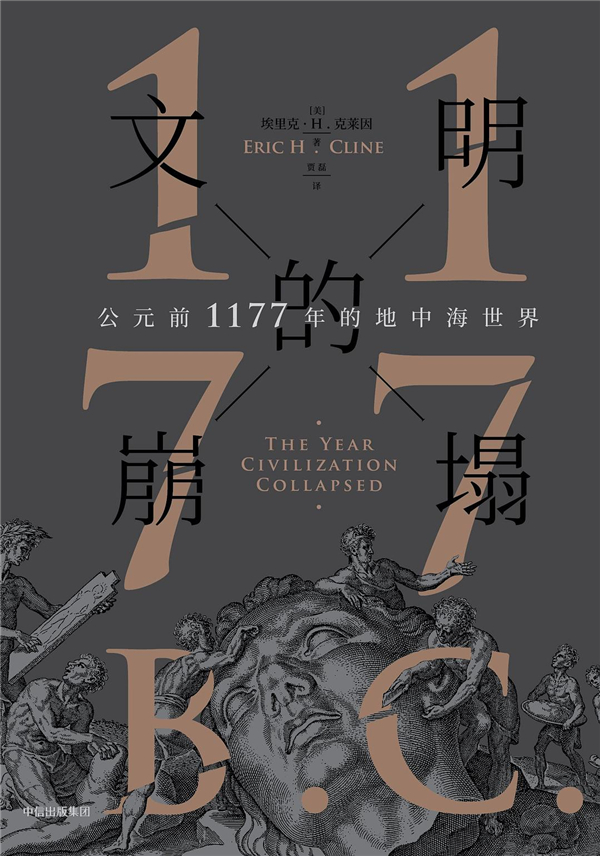 该书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古代史上的转折点》丛书中的一本分册,英文原版在2015年面世。作者克莱因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并任该大学考古研究所主任。他还是美国近东考古学界的顶级期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简称BASOR)的两位主编之一。 对研究古代近东(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和古代伊朗等主要文明区域)的学者而言,公元前12世纪堪称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古代近东地区经历了繁荣的青铜时代文明,各文明区域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源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成为各国统治者之间通信的外交语言。部分通信后来出土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所建的新都阿玛尔那,史称“阿玛尔那”书信。两河、埃及、米坦尼(位于两河流域上游以东以北的山区)和赫梯组成当时的大国俱乐部,地中海东岸的诸多小城邦也加入到当时的国际关系网络中。各国王室间作为外交礼物互赠的奢侈品还展现出所谓的国际主义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但上述欣欣向荣、开放交往的气象在公元前12世纪初戛然而止。随着海上民族入侵地中海地区,赫梯帝国瓦解,迈锡尼文明消亡,埃及的势力撤出地中海东岸回缩到本土,两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呈萎缩态势。爱琴海和古代近东从此陷入长达两三个世纪的黑暗时代。造成这一文明崩塌局面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为解答这一经典问题,作者首先把目光投向之前的公元前15世纪。本书第一章回顾了两位埃及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以及周边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发展态势。此时的埃及开始成为青铜时代晚期的强权。 发展到公元前14世纪,作者认为此时“各国间的政治、商贸及外交关系与当今世界全球化经贸主体的关系并无实质性差异,既有经济禁运、外交使团,又有最高级别外交层面上的‘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东岸成为大国间冲突的温床,主要处于埃及(历经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和图坦卡蒙的统治)与赫梯(两任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和穆尔西里二世)的拉锯战中。最知名的插曲当属图坦卡蒙的寡妻写给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的信,请求后者派一个儿子前来埃及和她成婚,同时许诺他将成为埃及的法老。但赫梯王子在路上就死于埃及人之手。赫梯国王大怒,派军队在叙利亚与埃及军队交战,最终自己也死于赫梯士兵感染后带回国内的瘟疫。 水下考古为则为窥视公元前13世纪的古代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经济一体化”局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材料。有一艘沉没于土耳其西南海岸乌鲁不伦的船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打捞。这艘沉船长约12米,用雪松借助榫卯结构制成,很可能从地中海东部的迦南地区启航驶往爱琴海地区。打捞出的物品种类之丰富,足以召开一次博览会:有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生料,来自迦南的约140个储物罐,来自塞浦路斯的黄铜,来自努比亚的乌木,来自埃及的圣甲虫雕像和近东其他地区的圆筒印章,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剑和匕首,以及大麦、树脂、香料乃至葡萄酒等产品。数量最多的当属近1吨的生锡(可能来自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地区)和10吨的粗铜,它们是制作青铜的宝贵原料。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评析了可能导致青铜时代文明崩溃的诸多原因,包括地震、气候变化导致的旱灾和饥荒、内乱、入侵者和国际贸易的崩溃,以及权力分散与私营商人的崛起。他最终认为,单一变量无法解释一个文明时代的崩溃,“复杂性理论”才是研究者的希望所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城邦、王国和帝国不仅构成一个政治经济体系,而且由于相互间的产品交换还形成一个贸易网络。在这般复杂和多层的系统中,单个组成部分由于上述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通过网络的影响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塌。崩塌也绝非线性推进,而是一个非线性的进程。 不过,本书的书名(英文为1177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貌似违背了作者用“复杂性理论”解释文明非线性崩塌的主张。公元前1177年不过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8年,所谓的海上民族在该年入侵埃及。以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年代作为整个爱琴海和古代近东地区文明崩溃的年代,很可能是作者在命名本书时的修辞策略。 本书的翻译亦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常见人名未能遵循学术惯例,如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被译为阿肯那顿。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近东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