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日除了读与研究有关的书籍之外,为了更新课程内容,还是要留意新上市的中译本,以便推荐给学生。以下是2018年为准备授课而阅读的部分书籍,限于篇幅,主要谈三本关于大历史和全球史的著作。 弗雷德·斯皮尔著,张井梅、王利红译:《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 弗雷德·斯皮尔提及自己研究大历史的契机是因为在1968年观看了阿波罗8号首次登陆月球的黑白电视实况转播。1969年的《时代》周刊上刊登的地出(Earthrise)图则“彻底颠覆了我对地球的看法”(《大历史》前言和致谢,第1—2页),也解释了这本书的原作封面图的由来。  1969年1月3日《时代》周刊封面上是三位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斯皮尔称是在1月10日的《时代》周刊上读到了地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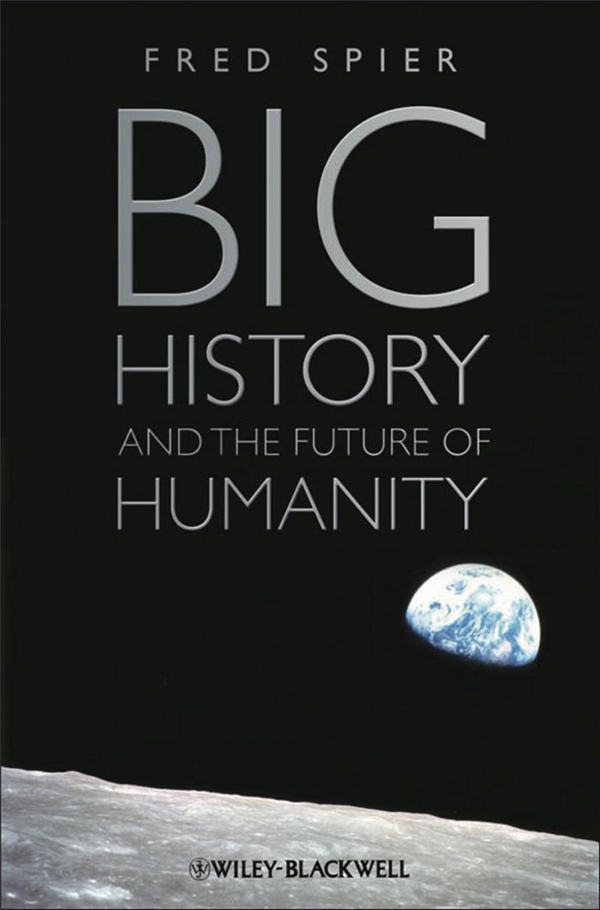 斯皮尔原作封面与中文本封面 对地球的认识视角的转变成了一粒播在斯皮尔心中的种子。不止斯皮尔,许多人对“全球”的直观认识,都源自这次直播和地出图。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外部视角观察所在,是对作为整体的“全球”的具象化,距今不过50年的时间。 尽管最初学习的是生物化学,但是在接触到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大历史课程之后,斯皮尔获得了解释自我和周围一切的新路径。他认为大历史和其他任何学科的不同在于“把所有过往研究整合成一种新颖连贯的视角”,并从1994年开始构建大历史课程,在1996年出版了《大历史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2005年发表的论文《大历史如何运行:能量流与复杂性的兴衰》则是这本《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的前奏(前言和致谢,第3—6页)。 相比不少历史著作给人留下耽于个案的印象,斯皮尔的这本书内容极为宏观,以创造一种“连贯的视角”。采取这种研究路径,和20世纪以来现代学科的发展割裂了许多知识之间的联系有关。大历史重新整合这些知识,展现整体的自然史,从大爆炸、地球的出现、生命的诞生,及至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无所不包。 历史学家若要驾驭本学科之外的议题,既要熟知其他学科的理论及其背景,还要有一条历史性的,打通所有学科的主线。斯皮尔选择的主线是“能量”和“复杂性”,并以“金凤花原理”(the Goldilocks Principle)作为变动发生的条件。大爆炸之时并无复杂性,但有惊人的能量。各种金凤花条件的出现,孕育了复杂性的叠加。所谓金凤花原理源自一则盎格鲁—撒克逊童话,指“复杂性存在的环境,必须恰好合适”(《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第39页)。历史学家所研究的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形成,是无数偶然“合适”的叠加造成的,并以消耗大量能量为代价。帮助人类应对社会的核心器官同样是极为复杂的、高能耗的大脑。  《三只熊的故事》里包含金凤花原理的由来 斯皮尔对历史性的呈现,是采用时间先后作为讨论的顺序。第一章引言是学术史回顾,第二章总体思路阐明了核心概念,随后的三章解释从大爆炸到地球上生命出现的过程。这三章对理科背景的读者来说应该会比较亲切。紧接着的两章以公元前1万年的农业革命为界解说人类的历史。至此,历史学家的研究才频繁出现。最后一章留下的问题再度跳出地球:人类会迁居到其他星球吗?他目前的结论是否定的。 相比其他很多“历史学”著作以文明社会作为书写的起点,斯皮尔的“大历史”将人的诞生置于宇宙而非地球的空间中讨论。译者认为,这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把科学思维和人文精神在历史书写中统一起来”(《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第270页)。只不过,大历史依然是以人类的视角解释当下的形成。就像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片头以对大爆炸的演示开篇,以主角们生活起居的客厅结尾。无论起点的格局多大,背景多宏阔,即便是站在地球空间之外看到了地球,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探索依然无法跳脱身心的局限。 约翰·R·麦克尼尔著,李芬芳译:《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虽然“地出图”激励了斯皮尔的大历史研究,克里斯蒂安给了斯皮尔接触大历史的入口,但他并没有把这本书献给促成登月的所有团队成员和克里斯蒂安,而是献给了他最敬佩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老麦克尼尔)。同样深受老麦克尼尔的史观影响的斯皮尔的同代历史学家中,还有中国学者熟悉的约翰·麦克尼尔(小麦克尼尔)。 两位麦克尼尔在2003年出版的《人类之网》被斯皮尔誉为“人类历史(human history)”的典范。2000年小麦克尼尔出版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同样以人类历史为单位书写,尽管更多人将之归为“环境史”的范畴。《泰晤士报》称《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是当年“最优秀的科学作品”,美国世界史学会2001年度最佳图书奖及森林学会图书奖都颁给了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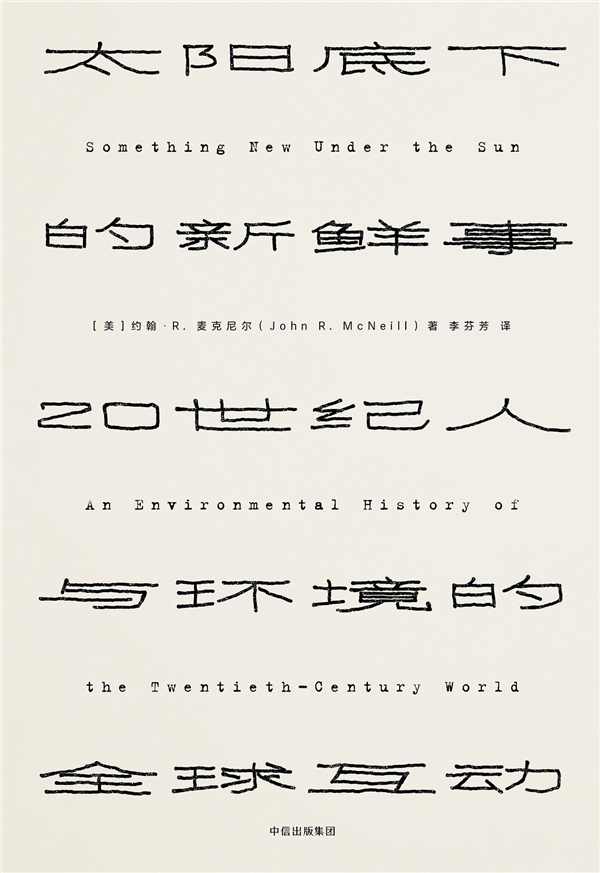 原作与中文本封面 相比斯皮尔,小麦克尼尔把空间范围从宇宙缩小到地球,把时间范围从大爆炸至今缩短为20世纪,把对象从宇宙中的一切缩小为地球上的万物。但他需要处理的问题对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依然是过于宏大的。与之相关的历史研究路径有许多,还涉及医学、生物学、气候学、农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资料。该书同样也以人类对能量的利用、空前复杂的社会和人类的适应性作为解读20世纪人类史的主线,刺激读者产生些许“末世恐慌”,进而善待环境,以确保人类这个物种的存续。 从写作来看,小麦克尼尔和斯皮尔的行文中很少有原创性的个案研究,主要是以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立论的基础。且无论是大历史还是全球史,都标榜抛却“西方中心论”来书写历史。只是,在资料的空间选择上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并且均衡,关于欧美的历史总是更为详细,而关于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常常是被罗列或仅仅是提及。这固然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例如研究者对非西方资料的掌握十分有限,也有不同地区全球史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即非西方学者中从事全球史研究的数量并不多。 从著作所使用的时间线来看,《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以时间顺序铺陈叙事,《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则并未严格按照时间先后解说。全书分上下两部,第一部以岩石圈与土壤圈、大气圈、水文圈和生物圈作为标题,第二部谈论人口、城市化、燃料、工具、经济学、观念和政治的影响。在追溯源头时,小麦克尼尔会回望人类诞生之初的情况。他并不否认19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了直接影响20世纪农业发展的技术,也出现了使用化石能源引发的环境问题。在阐述关于20世纪的现象时,又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行文中还能尚未完全退场的冷战思维。如在解说苏联的问题时,常常把原因归咎到体制缺陷。 环境问题不受国家疆域限制这一点,使相关研究很容易拥有全球史的视野。与之相关的历史主体不再局限于社会上层,而是包括许多普通人,尤其是科学家。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显而易见。全书的结论和小麦克尼尔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国》颇有共通之处,即强调环境是和人类发展是相互决定的,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协同进化。 小麦克尼尔应该是深谙通俗读物的写作之道的。书的标题来自《圣经》,行文中有很多诗意的比喻,利用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家的描述作为支撑材料(如第58页对乔治·奥威尔小说的引用),想必会让普通读者感到亲切。由此虽然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却也可能面临专业历史学者认为对研究资料批判力不足的挑战。全书通篇使用了大量小标题,对于读者集中注意力的要求也有所降低。即便是用零碎的时间来阅读,也很容易抓住作者讨论的重点。 只是,对熟悉全球史和环境史的读者而言,这本20年前出版的作品的内容甚少有新意。一方面可以说是环境史和环保意识推广的成功,另一方面也给全球史和环境史研究者留下了问题:如何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定义全球史?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尽管斯皮尔和小麦克尼尔处理了极为宏大的时空尺度的问题,但依然是具体的研究实践。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则从更为理论的层面追问全球史的意涵。2013年他以《全球史导论》(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为名出版德文版,201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规模改写后的英文本。中译本由英译本译出。该书德文版的介绍中提及了斯皮尔的“大历史”理论,并指出二者的相通之处都是跨越国家边界的、更为整体性的研究。英文版中,他也明确指出了大历史的问题在于弱化了人类的作用和影响,涉及许多和历史学家无关的问题,又试图总结出历史规律,也就很难被关注偶然性和异质性的历史学者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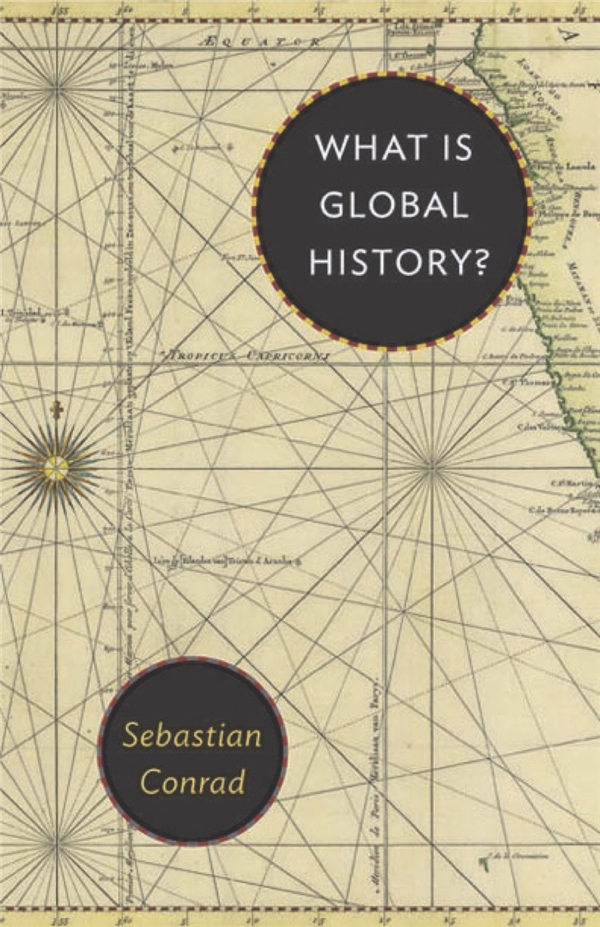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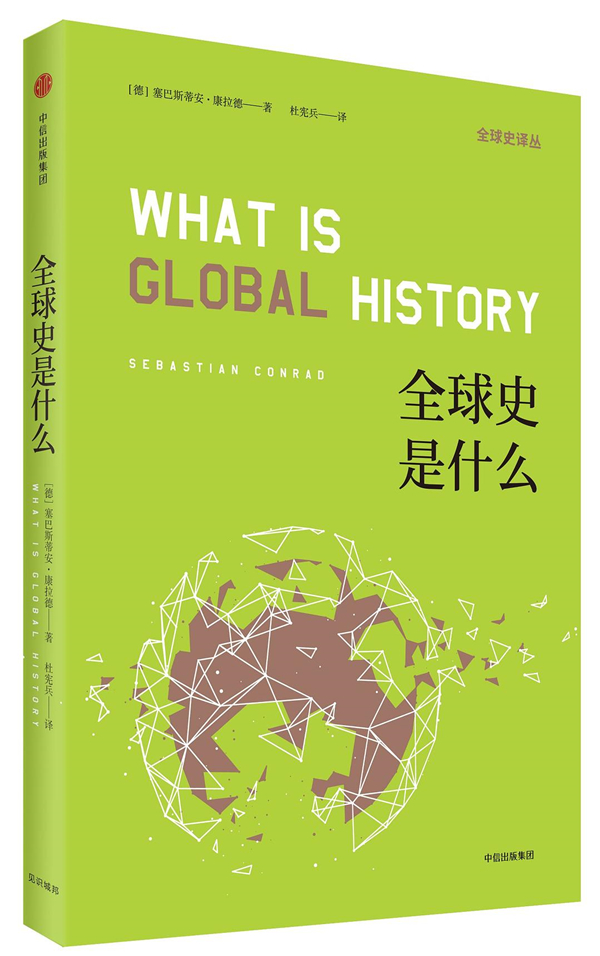 德文本、英文本和中文本封面 康拉德在导语中承认,很多研究者受到“全球史”这个概念的吸引并开始使用,将研究的空间边界从国家和地区转向更大的范围,努力破除西方中心论,但缺少共同的、明确的方法论。他把全球史研究分为三类,分别是“作为万物历史的全球史;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integration)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全球史是什么?》第5页)。 第一类中包括了大历史,以特定问题切入,将与全球有关的现象汇编在一起,并指出即便所有的汇编都不可能真正做到覆盖全球所有空间,包罗所有历史时段,但至少完成了一片拼图。第二类研究设定任何社会、国家和文明都无法孤立存在,因此要探索彼此之间的联接。观察的空间不一定是整个世界,只要是一个内部联系的区域即可。第三类将个案放在全球脉络(情境)之中考察,也是作者最着力研究和推崇的全球史。这种全球史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把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放在全球语境中解读(《全球史是什么?》第5—12页)。“全球”这一要素由此具有自反性,塑造着研究对象的同时,被研究对象所塑造(第73页)。 随后的九个章节里,康拉德先以两章的篇幅叙述全球史的学术前史,从包含对“世界”的思考的历史书写开始追溯,并指出这些研究的和全球史的不同以及不足,可视为对全球史的外部定义。尽管康拉德并未为读者提供了解全球史的单独书目,但这两章中涉及到的文献,都是了解全球史主要争论的基本读物。 之后的章节都是对全球史的内部定义。第三到五章指出全球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即关注“全球整合”这一全球层面的结构转型,在于强调比较(comparison)、关联(connection)之外,还要涉及因果关系(causality)。由此,全球史可以超越第一、二章中提及的其他跨区域研究的局限,也超越传统的比较研究所采用的内外二分的视野。但康拉德也强调全球化史并非全球史,只是全球史研究的背景。 第六、七两章以全球史的时间和空间,说明研究应如何展开。就空间而言,将微观研究置于全球脉络(情境)中是一种全球史的实践,但并无联系的两个宏大空间之间的比较却依然是传统的比较研究,而非全球史。换言之,研究对象决定了全球史考察的空间大小,而非所有跨区域的研究都是全球史作品。研究空间的变化影响了全球史研究的时间尺度,且全球史研究并非全是长时段研究。如果研究者选择考察长时段,是为了展现受到全球因素影响后长期的历时性变化。如果选择的是短时段,则侧重从共时性的角度剖析全球性关联。在落实到具体书写时,也要协调历时性和共时性情境的共同影响。 第八、九章回应了全球史应如何跳出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也就是对全球史的认识论的解析。如果以其他地区的中心论简单替代西方中心论,依然无法形成全球视角,因为无法抛却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也就无法看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彼此形塑。只是,从历史研究所用的术语来看,又有谁能完全不使用来自西方的诸如“文明”和“资本”这样的词汇,来进行写作呢? 在最后一章里,康拉德讨论了“为谁书写全球史”,认为让读者产生成为世界公民的意识,是全球史书写的目的。这一认识得以产生的前提,是以全球史来理解当下世界的相互关联和内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说明了全球史能对过去的历史书写的局限性如何矫正,例如超越内在主义的解释方式,以及可能的局限。毕竟,一旦“全球”成为了被频繁使用的概念工具,意涵就会变得极为复杂,会被粗暴地用于概括现象。但他认为,如果要研究真正的全球结构,“全球”依然是不能抛却的概念。 诚然,康拉德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了他所认可的全球史的意义,但没有明确论及书写全球史依然是一种“特权”。只有能广泛掌握并阅读涉及不同区域的资料的学者才有准入的机会。全球史看似是极为开放的研究领域,但若要达到他所预设的程度,有着极高的准入门槛,依然是西方学者更容易达到。当然,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学者作为全球范围内史学共同体的一员,完全可以更深入地尝试这类研究,或许能有新的洞见诞生。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帝国与英联邦史、民族与民族主义、全球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