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丁玲 原标题:“失贞”以后怎样——论丁玲的“创伤书写”(1936—1941年)  1933年《生活画报》第廿七号报道丁玲被捕消息时所刊的照片,下书“最近失踪之女作家丁玲女士” 1933年5月,丁玲遭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软禁三年后,1936年9月,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丁玲由南京逃到上海,随后离开上海经由西安转赴陕北。同年11月,丁玲到达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从1933年丁玲被捕起,有关丁玲“变节”“转向”的谣言便开始流传。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对她的南京经历提出质疑。南京三年的经历成为丁玲一生都绕不开的历史问题。她非同寻常的存活经验始终难以被纳入强调“忠烈”的革命话语之中,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失贞”的问题常常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坎”。 延续了“反右”运动中论者对小说人物贞贞与丁玲历史问题之互文性的关注,日本学者高畠穰在《丁玲转向考》中认为,丁玲创作于1937年8月的独幕剧《重逢》“是丁玲三年监禁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揭示了活着的人们内在的危机的秘密。换句话说,在自己的心中建起一道深渊,并与其相对峙,作家一面凝视着它,一面写出了不放弃正义而试图生存下去的精神的轨迹。丁玲撰写这部作品,也许免去了试图转向或已经转向的人们的或多或少必须背负的腐蚀作用”[1]。蓝棣之也曾在丁玲及其创作的人物之关系上做过精彩的症候式分析。他认为,在1958年《文艺报》组织的“再批判”中被认为是“毒草”的一批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是丁玲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2]。 本文即是在上述层面展开的尝试。在《松子》《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都隐含了对“失贞”现象的共性叙事。这是作者丁玲在创作时挥之不去的个人历史问题,也是小说人物在故事中面临的困境。“现实”与“幻象”的同构使得这些文本具有高度的症候性。在不同时期对“失贞”问题的镜像式书写中,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在强调“忠烈”的革命话语面前所进行的自我辩白、自我证成和自我斗争。 一 难以言说的“渣滓” 短篇小说《松子》写于1936年3月,发表在1936年4月《大公报·文艺》第130期,初收《意外集》。本文集收录了作者被囚后写就的五篇文章,对此,丁玲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解释。1936年10月到达西安后,丁玲在《〈意外集〉自序》中表示,这几篇文章是在“极不安和极焦躁中”勉强写成的,“简直不愿看第二次”,“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松子》“是那末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意外集》“不是一个好的收获,却无疑的只是一点意外的渣滓”[3]。多年以后,在1980年给赵家璧的复信中,丁玲却说“我对于那几篇文章没有什么感情”,一再强调“完全是为了稿费勉强凑成的”,并且将《松子》和《团聚》归入《奔》的创作路径之中[4]。两相对照,丁玲在1980年的说法淡化了《意外集》与她创作时的情感共鸣。 有趣的是,在1936年5月致叶圣陶的信中,丁玲的说法与上述又有所不同,《松子》的写作之于丁玲有积极主动的意义:“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释,只愿时间快点过去,历史证明我并非一个有罪的人就够了。三年过去了,我隔绝着一切,我用力冷静我自己,然而不知为什么却又忍不住给《文艺》写了那一点小东西(即《松子》——引者注)。而且还在预备写下去,你不以为我写得太早了或者太迟了吗?”[5]此处丁玲对《松子》的说法显然不是1936年10月宣称的“勉强”写成,更不是1980年所说的“没有什么感情”,恰恰相反,丁玲其实对《松子》的创作有“忍不住”的感情。1984年7月完稿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我反复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动,党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写文章。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6]到写作《魍魉世界》之时,丁玲口中《松子》的创作动机更加具体了——这是向党发出的求救信号。1936年萧乾收到《松子》后的反应也可佐证上述“言志”的说法。在和鲁迅的谈话中,萧乾以《松子》为证据,不同意鲁迅认为丁玲“完了”的看法,认为《松子》“毫不含糊地表明,她的思想并没改变”[7]。 自从1936年年初收入《意外集》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丁玲没有将《松子》编入自己的任何一个选本。直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丁玲小说选》之时,曾经的“渣滓”和“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的《松子》以“还是沿着小说《奔》的道路前进”[8]的理由被编入。事实上,《松子》和丁玲在“左联”前期以《水》《奔》为代表的“政治化”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小说中阶级斗争的设定并不典型:松子偷西瓜偷的不是地主恶霸家的;松子并未遭到地主恶霸及其走狗的欺凌,却险些被同为无产者的打铁学徒强奸[9]。 丁玲的丈夫陈明曾明确谈到《意外集》之于丁玲个人遭遇的独特含义:“限于当时的处境,《意外集》中的各篇可能都不是佳作。但在那特殊情况下,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值得深挖,并和她前后的作品相联系、比较,这也是研究丁玲作品、创作道路的一个方面。”[10]有研究者注意到《松子》的关注点“不再是以理性化的分析去鼓吹阶级斗争、传达意识形态说教,而是‘人’的生存困境本身”[11]。某种意义上,《松子》反映的更是丁玲自身的生存困境。  丁玲《意外集》(1936)封面。注:右下角的图画描绘的应是《松子》中的场景:松子母亲抱着妹妹小三子,扬手准备打瑟缩着的松子 小说讲述了一个“流丐”家庭中小男孩松子的“罪与罚”的故事:松子因为饥饿去偷西瓜吃而一时没有照顾好妹妹,结果妹妹小三子走上岔路被狼吃掉。自己也没偷成瓜,在瓜地里反而差点被打铁的黑小子强奸。当受尽屈辱的松子忍着痛即将回到家时,却因听见父母的厉声责难,害怕父母的暴力而不敢现身,最终悄然没入无止境的黑暗之中。 在丁玲的小说序列里,《松子》或许是一个最“黑暗”的故事。全篇充斥着饥饿、冷漠、死亡、鸡奸和暴力,笼罩在彻头彻尾的黑暗之中——连试图强奸松子的铁匠学徒也是一个“黑”小子!家庭在其中不仅不是庇护所,反而是恐怖的压抑性力量。耐人寻味的是,此前丁玲的小说基本不处理亲子关系式的家庭矛盾。正是从《松子》开始,丁玲第一次触及黑暗的亲子关系,而且写得如此绝望。正如范雪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穷人家里人们互相怨恨,进一步家破人亡”[12]的故事。故事矛盾更多指向了家庭内部的怨恨,而非阶级仇恨。 小说中父母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暴力和责难。小三子从摇篮里跌出来,松子挨打;小三子落水了,松子将其捞起后并无大碍,自己却差点被打死;小弟弟小毛被载重汽车压坏了脑壳,松子被父亲无声地狠狠打了一顿,连小三子也被父亲踢了几脚;即使小三子和母亲都吃着松子偷来的东西,母亲还是骂松子不成材,总有一天要被抓到警察厅里去打死;最后,小三子被狼吃了。这一次,父亲很可能将松子打死,这也直接导致了松子不敢归家、只得没入黑暗中的结局。父母在小说中纯然是惩罚性的暴力权威化身,松子与父母没有任何心灵交流的可能。有意味的是,在小说开头,当松子唯一一次带有依恋感地主动去“看”父母的时候,出现了颇具梦境色彩的一幕:黄昏阴暗的天际下,当松子“回头去看了一下坐在窑门口的妈和爹”[13]时,他们却不见了。 可以说,松子一家根本不像正常的家庭,其中看不到任何的爱,只有怨恨、恐怖和暴力。面对松子父母的责难与暴力,无论是叙述者还是小说人物松子都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之中。日本学者野泽俊敬敏锐地指出了松子与丁玲早期小说主人公在“苦闷孤独”上的不同。“莎菲”们“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才幻想、幻灭、痛恨,从而陷入虚无、颓废、自暴自弃”。而松子并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更谈不上“幻想”与“幻灭”,他只有“压抑状态下动物般的求生愿望”[14]。 在弗洛伊德看来,宗教和文明的起因在于一种成功引发个体罪疚感的压抑性结构:“社会以同谋罪中的共犯关系为基础;宗教以带有悔恨的罪恶感为基础;而道德的基础则一部分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一部分是为罪恶感所要求的赎罪行为。”[15]实际上,《松子》的故事展现的正是一个引发罪疚的压抑性结构。表面上看,妹妹是因为松子一时疏忽而被狼吃掉的,但细究起来却颇为可疑,整个故事更像一道“谶语”的应验,其中叙述者精心“设计”了松子的受罪。首先,叙述者明确提到松子母亲每次骂松子的结语总是“小毛被你弄死了,我知道你一定还不够,有一天小三子又会死在你手上的”[16]。故事后来的发展正好应验了母亲的话。此外,种种迹象表明,松子仿佛是故意要使自己获罪。比如,在离开妹妹去偷西瓜之前,松子便吓唬妹妹,庙里的大狗会吃掉她;又如,松子明知前天小妞子刚被吃,却依然选择丢下妹妹;再如,松子曾告诉妹妹自己会目送她去窑里躲起来,但后来他根本没有这么做。 丁玲曾在《〈意外集〉自序》里谈到自己“写时特别审慎着‘技术’”[17],陈明在注释里解释为“这里是指在敌人的耳目下,不让敌人从作品中揣摸到作者的意愿和动向,不是通常说的表现技巧”[18]。然而袁良骏对此却有另一番理解。他认为“技术”指的是情节安排的技巧。《松子》和《团聚》等像是“‘无巧不成书’的旧文艺”,“因为太巧,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是丁玲一贯作风的倒退,而丁玲以前的作品不是以情节取胜的[19]。实际上,在1931年5月的创作谈《我的自白》中,丁玲自己明确表示过,反对“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20]。 从上文分析来看,《松子》中种种“巧合”的叙事结构或许正是丁玲无意识的体现。我们可以将《松子》读成一个作者在“极不安和极焦虑”中创作的原罪式故事,即作者“无意识”地选择了“家庭”作为一种压抑性的、便于引发罪疚的叙事框架;与此同时,作者设计出“过失犯”松子,让松子在惩罚性权威的“教唆”下完成“无意识”的犯罪。 当自己普遍被外界认为“失贞”但却又准备再次投身革命之时,丁玲复出的第一篇小说《松子》高度症候性地表现出了她内心的矛盾情感。一方面,她强调自己的受难,希望将自己的幸存经验界定为一场自己无法抗争的苦难从而获得救赎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呈现自己的受难,对于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讲入革命话语中,丁玲却始终面临“失语”的难题,对自己究竟能否获得救赎抱有很深的疑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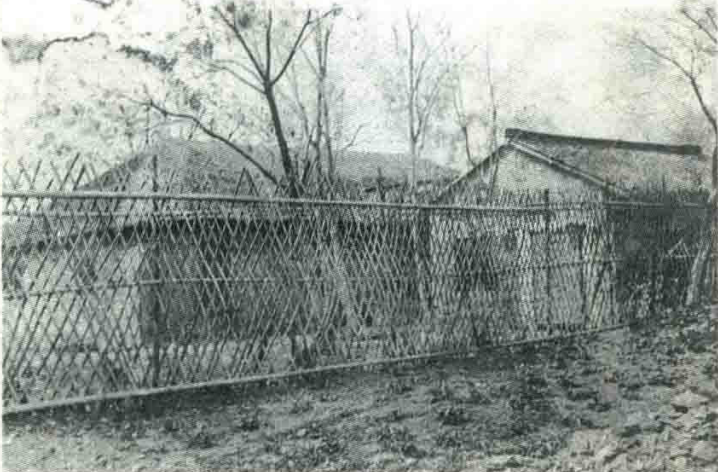 南京苜蓿园丁玲囚禁处 事实上,在南京的三年里,丁玲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之中。在谣言四起而丁玲自身表现也十分暧昧的情况下,她即便找到了同志,也无法交流,因为她很难得到同志的认可与信任。1934年,丁玲与张天翼在南京夫子庙偶遇,然而随后双方的会面并不愉快。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在敌人面前是受尽折磨的,但在朋友面前,忍受着这样的冷淡,却是第一次。”[21]“从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隐隐地难受。我不理解张天翼,只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22] 小说中还有一个情节值得我们注意,即黑小子想要鸡奸松子。如果松子愿意的话,他就允许松子把西瓜偷走。其实,这一幕是小说故事的旁支,大可以不写;要写,也可以写其他种类的欺凌方式。但丁玲偏偏写了性暴力,写了一个此前从未写过的“失贞”情节,而这类情节在她后面的小说中还将不断上演。 万幸的是,松子毕竟并非“故意”致死了自己的妹妹,也没有因为饥饿和暴力胁迫而“失贞”,这也是丁玲始终坚持的立场——自己从始至终并没有真的背叛党,写条子只是受敌人诱骗,是为了逃出生天以求继续为党效力的权宜之计。但丁玲非同寻常的存活经历却注定无法见容于革命话语,丁玲这段遭遇和心曲只能以“渣滓”“剩余”的方式存在。正是从《松子》开始,被符号系统阉割的“失贞”问题驱动了丁玲的欲望,暗中策划、影响着她的创作。 当松子受尽屈辱,从瓜地往家里走时,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或许反映的正是丁玲当时的心声: 他的难受的饥饿跑走了,代替的是更其难受的许多肉体上的疼痛,和一种被欺侮而又无告的凄伤。他用头枕着草,草已被露水湿透,草上的一颗萤火虫,无力的亮着那微弱的小灯,在前面飞去了,飞到无止境的黑暗里去了。他也有一点想哭,可是没有眼泪。他觉他需要一点什么,他说不出来,他却鼓着勇气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忍着痛,一跛一跛的走上岗去,是朝着有着窑的那方。[23] 二 被悬置的死亡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应博古之约,丁玲为创刊号写了《一颗没有出镗的枪弹》[24](即《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以下简称《枪弹》),这是丁玲到陕北后所作的第一篇小说。丁玲本人非常重视这篇小说,她到陕北后出版的第一个小说散文集即名为《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小说后来又被收入《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选集》等多个集子。1956年,丁玲将其改写成《一个小红军的故事》,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的政治意涵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有论者指出《枪弹》是一篇“主题先行、具有很强的政治说教色彩”的作品,是对《八一宣言》的图解[25]。更有论者进一步认为,小说为了政治功利以至于牺牲了人物真实与生活真实,小红军在生死关头说出的“用刀杀我”以省下子弹抗击日寇是“一种政治功利性的虚假而拙劣的演绎”[26]。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丁玲的创作受到了当时高涨的政治热情的驱使,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种可能性,即“失贞”问题对其创作的影响。有论者指出,丁玲受制于“囚徒生活留下的阴影”,“清醒的阶级责任感更使她不敢放肆地写作,以至于使得有着献礼意味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重逢》都只显出几条干巴巴的筋,几乎仅存一个概念的框架”[27]。 事实上,丁玲到陕北后曾经打算写一本关于南京三年幽禁生活的书。但据说后来因为顾及统一战线的利益,最终放弃了出版的计划[28]。在接受访谈时,丁玲虽然不愿意多谈自己南京三年的经历,有趣的是,她却一再强调女性在革命事业中的忠烈,甚至不惜因此贬斥男性:“她说:‘在磨难中的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甚至比男同志们更坚定。在党的记录中,指出了许多男同志在监禁和磨难之后自己认了罪;但是女党员们呢,不管遭遇着怎样的痛楚和羞辱,终不肯自认其罪名。许多女同志已死在刑房中,更有许多在刀枪之下被处决了。’她追述到几年以前在‘湖南的清共’中,被湖南省主席何键处死的女性比男性为更多。”[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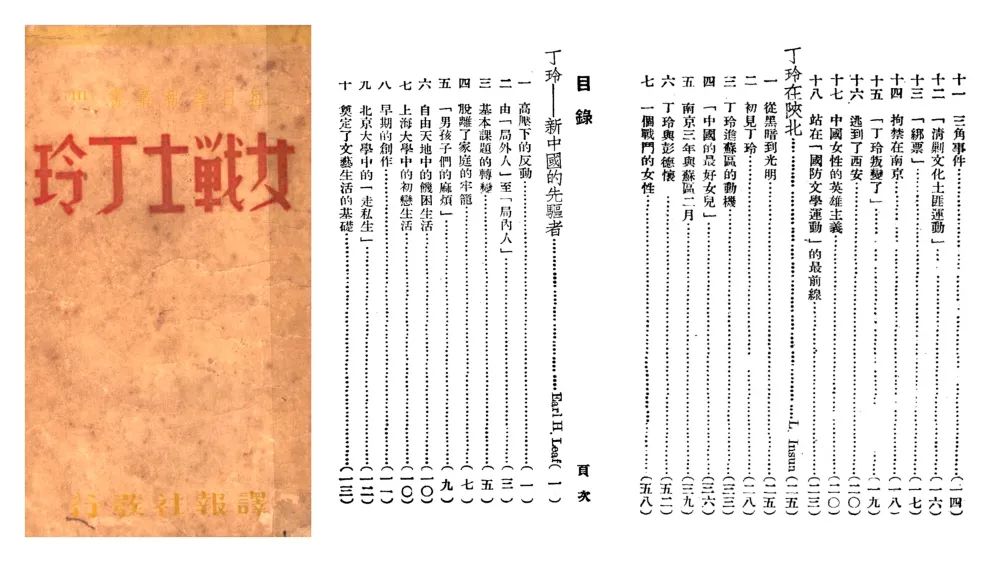 《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社1938年版 丁玲一开始决意要写却没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是顾及统一战线的利益,但另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她不愿写,不敢写,也不会写,她难以把自己的遭遇讲入强调“忠烈”的革命故事里去。某种程度上,她为革命女性所鸣的不平应该也是为自己而鸣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丁玲这般强调女同志的忠烈,自己却从未写过一个女烈士的故事,也没有写过一个以烈士为主角的故事。在《枪弹》中,小红军可能的壮烈牺牲被高度戏剧性的情节抹去了。小说实际上悬置了“失贞”困境下“生还是死”的问题,选择带来的真正后果并没有发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小说与丁玲的遭遇在情节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掉队→行将被东北军士兵鸡奸,如果失贞可保性命无虞→选择反抗从而保住贞洁”的结构对应的是“丁玲落入魔窟与同志失联→面临敌人诱骗→不屈服从而保住贞洁”的故事。不同的是,小红军的反抗以极其戏剧化的仪式收场——他被举起来了,敌人被感化了!显然,这是丁玲在过去无法做到的事情。作者用政策话语替代性地实现了自己的欲望。 在1937年6月应博古之约创作的另一篇小说《东村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有关“失贞”的情节。为了救佃户陈得禄的父亲,陈家人选择以做工的名义逼迫童养媳七七去赵老爷家,致使七七被赵老爷奸污霸占。然而,陈得禄在与七七私会时,他并不理会七七“失贞”的缘由,反而对七七施暴。 对于七七的“失贞”问题,叙述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是不能责备七七的,七七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她没有抵抗的力量,当她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的时候”[30]。显然,叙述者并不认为失贞的七七应当去做一个“烈女”。有趣的是,在小说开头,陈得禄的母亲曾去见过七七,“说她只会哭,咒骂他,说她总有一天要上吊,否则就跳水”[31]。但到了结尾处,叙述者并没有给出七七自尽的可能性——“他(陈得禄——引者注)想着一个人,不知道是趁机会跑丢了,还是又正被人拷打着”[32]。 可以说,这与丁玲之前关于女性死烈的叙述是矛盾的,但与她自己的遭遇却是相符的。这正如符杰祥指出的那样,“丁玲文学与人生世界中的烈女/烈士认知”,“其所诉求的‘忠贞气节’与传统女德、革命政治”之间,存在着“相纠缠的压抑、变形、扭曲、扬弃等系列问题”。“围绕‘死之歌’所缠绕的‘不死’心结,也许才是丁玲表达‘忠贞’的最大心结”[33]。 由此,处理“失贞”问题更大的困难其实发生在,假如“不死”,“失贞”回来之后怎样?在1939年春创作的《泪眼模糊中之信念》与1940年秋冬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这个问题以两种极其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回应。 三 奇诡的归来 《泪眼模糊中之信念》[34](即《新的信念》)创作于1939年春,同年9月16日发表在《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上。小说写的是一个失贞苟活的老太婆在归来后宣说自己苦难遭遇的故事。在敌人的羞辱面前,陈老太婆没有像自己的孙子一样拼死反抗,没有如自己孙女一般在失贞后死去,也没有像她对一个姑娘提供的建议那样咬舌自尽,而是顺从鬼子从而苟活了下来。期间她不仅在“敬老会”里帮鬼子做事,还和一个中国老头子被迫在鬼子的观看下发生了性关系[35]。从故事发展来看,老太婆失贞之后健在的代价则是,她必须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施虐和受虐的方式向家人和村民反复宣说她的残酷遭遇。这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费解的地方。 对于老太婆的癫狂之举,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解释:“这并不爱饶舌的老太婆,在她说话所起的效果中,她感到一丝安慰,在这里她得着同情、同感,觉得她的仇恨也在别人身上生长,因此她忘了畏葸。”[36]然而,作品没有从根源上交代老太婆为何会对自己的受害经验有如此特异的态度。从最初家人和村民的反应来看,老太婆根本就是“疯”了。 有论者认为,老太婆的讲述虽然被设定为对受害的疯狂式反应,但她从一开始就有积极、主动的目标,而且有坚定的意志去贯彻,老太婆对家人和村民实际上承担起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37]。“被强暴的女性身体”的隐喻是“女性可以成为民族/革命主体的手段”[38]。在这种解读方式下,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从“癫狂故事”到“启蒙故事”的转变其实发生在三儿子从游击队带回的“打日本”的话语进入之后。当老太婆最爱的三儿子从游击队上回来之时,老太婆感到“不需要在儿子跟前诉苦”,因为没什么用处[39]。此后,老太婆的残酷宣讲即有了理性的目的——诉完苦后,用“打日本”的英雄故事激励大家,并且动员大家参军。随着公家人的介入,她的话不再是疯人疯语,而是妇女会也在宣讲的“道理”。针对老太婆的歇斯底里症,民族革命话语似有一种神奇的药效。当“失贞”的老太婆能够将她被强暴的生理体验讲入一个抗战动员的故事里时,她便不再疯癫而成为了一个抗日的主体。 冯雪峰在为《丁玲文集》撰写的后记中这样谈到他理解的老太婆形象:“从莎菲到《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和《霞村》中的贞贞,这两种对象的不同,是两个世界的不同,并非作者用同一个主观可以同样去打入的;作者必须在新的对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并用这新的世界的意识和所谓心灵,才能走得进去。作者并且必须拥有这个世界及其意识和心灵,才能够把这世界和人物,塑成使人心惊肉跳的形象。”[40]在冯雪峰看来,丁玲能够走进老太婆和贞贞的“意识和心灵”,而且是“在新的对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的,他读出了老太婆和贞贞与丁玲经历的互文。实际上,创作《新的信念》之时,丁玲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在1938年,中央党校校长康生在一次会上曾言,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41]。尽管丁玲声称自己是1940年才从罗兰口中得知康生对她的怀疑,但王增如和李向东认为,“即便果真如此,她在马列学院也会感觉到这种氛围”[42]。  陈明、丁玲及蒋祖林、蒋祖慧在延安 对于老太婆在失贞苟活后发生的施虐/受虐行为,我们或许可以参考齐泽克对受虐狂做出的阐释:“性受虐狂使我们面对作为‘虚构’秩序的符号秩序的悖论:在我们所戴的面具中,在我们所玩的游戏中,在我们所遵从的‘虚构’中,存在着的真理比隐藏在面具背后的要多。”“暴力的实在正好爆发于性受虐狂的歇斯底里状态——当主体拒绝他的他者快感的对象-手段的角色时,当他震惊于存在的前景在他者的眼中被还原为对象a时,为了逃出这种僵局,他求助于行为的通道,针对他者的‘非理性的’暴力。”[43] 置身于民间伦理的环境里,老太婆难以找到她失贞苟活的合法性。她只能通过施虐和受虐般的苦难宣说,在抗战动员的主人能指中获得意义,取得在革命伦理中的崇高地位。事实上,老太婆疯癫行为的伦理正当性是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从故事的发展来看,她施虐是因为被施虐对象需要受虐,他们在未来召唤着她的“语言暴力”,以获得抗日民族精神的觉醒。这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对施于受害者的残酷行为的效果的理解(或误解)反作用地使伤害行为合法化了”[44]。在丁玲最后的遗作《死之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意义生成结构:“但是后来,时间隔久了,我慢慢地体会出来了,我还是不应该死。死,可以说明我的不屈,但不能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不能把我心里的历程告诉人们。因此,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45] 小说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变,即老太婆一开始在儿子面前宣说会感到羞耻痛苦,但到后来却越来越放肆。最后当儿子们全都来会场听她的宣说时,她内心涌动起“似乎是羞惭,实际还是得意”[46]的感觉。在精神分析的视野里,受虐对于主体而言不一定是痛苦而也可能是快乐的。“受虐狂主体认为,想象一位他深深依恋的人无意识地伤害了他,他将因某些罪行而错怪他(或实行了某些类似于错误的责怪行为),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这种快乐是因为他想象到了未来情景,即他所爱的人无意识地伤害了他,他将会对自己的不公正的责怪而感到深深的内疚。”[47]与此同时,“受虐者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为大对体提供原乐,而是令其焦虑。也就是说,尽管受虐者心甘情愿地忍受大对体的折磨,尽管受虐者要对大对体毕恭毕敬,使自己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但真正制定规则的是他自己。结果呢,尽管看上去是他勇于献身,把自己当成了供大对体享受原乐的工具,但实际上,他向大对体披露了自己的欲望,这导致了大对体的焦虑”[48]。然而,这种欲望并不光明,小说必须借助其正式的故事线把这种不堪的欲望加以升华。 四 穿越幻象 《我在霞村的时候》大约创作于1940年秋冬之际,也就是延安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南京历史作出审查结论的前后。1941年6月20日,小说发表在《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评论界主要有“启蒙主义”“女性主义”“革命主题”的三种解读方式。然而,无论做何种解读,我们势必都要面对陆耀东和张光年(华夫)文章中对小说情节真实性提出的质疑。在20世纪50年代的“再批判”中,评论家认为贞贞替党做情报工作的情节根本就是捏造的,因为贞贞“并没有半点革命者应该具有的认识和觉悟,她并不热爱祖国,也不懂得爱党,爱人民,对敌人也没有刻骨的仇恨”[49],党不可能“委托一个毫无民族气节、毫无政治觉悟的不可靠的人物来做这个工作”[50]。然而,有趣的是,此前冯雪峰却认为“她(贞贞——引者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51]。 丁玲曾多次表示小说的创作是基于一个她听来的故事。其中,细节最丰富的故事版本见于1952年4月24日丁玲所做的一次创作谈:“‘人要活下去,要斗争下去!’但在我思想上又觉得必须要牺牲一些东西,才能得到成功。譬如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思想。其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其人,不过我却曾听到过这样一个新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志要到医院里去,他告诉我说,是去看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女人,那个女人曾被日本人强奸了,而她却给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她原来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为了工作,为了胜利,结果还是忍痛去了。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难过,我想,她真是一个品质崇高的人,她不仅身体被损害了,精神也受了损害,虽然当时有许多人不能同情她,但是她有崇高的理想,她要活下去,党在同情她,在支持她。这个人物一直是在我的脑子里活着,酝酿着的,最后终于把她写了出来,起初是以第三人称写的,后来改用了第一人称。”[52] 这一故事样本也在1940年8月19日萧军的日记中出现:“一个在河北被日本掳去的中年女人,她是个共产党员,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掳到太原,她与八路军取得联络,做了很多的有利工作,后来不能待了,逃出来,党把她接到延安来养病——淋病。”[53]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萧军日记里记载的故事是丁玲小说所依据的本事的话[54],不难发现,在小说、萧军的记录和丁玲的回忆之间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同点。首先,在萧军的故事里,这个妇女是一个中年女性党员,最初可能是她主动与八路军取得的联络。然而,在小说中,这个女人的党员身份被抹去了,而且变成了未婚青年。其次,相较于1952年的讲述,小说中这个女人对日本人鲜明的仇恨也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其痛苦遭遇的淡漠态度。如此一来,贞贞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从而为党做情报工作的动机便十分可疑。这与《新的信念》里的蛮横地不断宣讲自己苦难的老太婆,与《重逢》中严词拒绝男同志的建议——通过“失贞”以成为“桃色间谍”的白兰是多么不同!最后,当这个女人进入小说中时,她变得异常“倔强”,不肯接受任何人的规劝,以至于后来被指认为“复仇的女神”[55]。 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这种执拗和直面现实的态度无论对于落后的村民还是对于先进的青年,乃至对于革命组织都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因为它挑战各个立场、认识基础上的对‘受害’、‘反抗’、‘斗争’、‘生存’的规范性看法。”[56]实际上,与其说贞贞“不是向敌人复仇,而是向人民群众复仇”[57],毋宁说贞贞反抗的是整个符号秩序本身。 从小说一开始,面对民间伦理的律令,贞贞始终坚持了一种决绝的反抗性姿态。很大程度上,她的悲剧根源便在于她的这种反抗性姿态。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跑到天主教堂的她恰好被日军掳去。归来后,家人要求她和她曾经爱过的男人结婚,她却做出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可理喻的拒绝,并且拒绝解释她的拒绝,以至于无法继续待在霞村。不仅如此,她对马同志和阿桂对她遭遇的探询也显示出拒绝的姿态。某种程度上,村里负责工作的马同志和从政治部出发与“我”同行的宣传科女同志阿桂或许可以视作当时政治伦理的代言人。也就是说,马同志和阿桂的看法很可能代表的就是贞贞去了延安之后将要面临的审视。然而,贞贞也以沉默平静的姿态,拒绝了两位同志在“看”她的时候,流露出的一种猎奇式的和政治功利性的眼光。在小说结尾贞贞甚至拒绝了“我”对她的怜悯——当“我”劝贞贞听娘的话嫁给夏大宝时,贞贞却告诉“我”她也要离开霞村去延安了。  1941年,丁玲在延安 有意味的是,我们在丁玲1942年3月创作的《“三八节”有感》也能看到这种决绝的姿态: 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58] 面对女同志的婚恋困境,丁玲开出的药方是要女同胞“坚持到底”,“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这让人不禁想起拉康的箴言——“涉及欲望不让步”。拉康认为,人有两种死亡,一次是生物性的死亡,一次是符号性的死亡,而安提戈涅进入了介于两次死亡之间的空间,即她的符号性死亡先于她的实际死亡。安提戈涅获得永恒安宁和救赎的方式,是以歇斯底里式的要求悬置和颠覆整个人世间的符号秩序,不对欲望让步,穿越为我们欲望提供坐标的幻象,因而无法被驯服和教化。在安提戈涅身上,齐泽克辨认出了死亡驱力的要求对于意识形态秩序的解构性与颠覆性[59]。 可以说,贞贞“不可理喻”的彻底的反抗性姿态正是在安提戈涅式“穿越幻象”行动的维度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她的行动在民间伦理和民族革命话语之中都难以找到位置。象征界中她已然“死亡”,但她却依然坚持自己的行动,并拒绝加以解释,这引发了人们因无法弄清其想法而产生的难以忍受的焦虑。与此同时,“穿越幻象”也意味着“认同征兆”,即在“过度”中发现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以及有关自身的真相[60]。正如颜海平所指出的那样:“丁玲故事示意着的真实变革,只有在参与者们挣脱他们自己亦在其中的‘历史常态’结构关系及其强制逻辑,超越他们自身以植根其中的‘正常’现状及其界定惯势的情形下,才会发生,才能发生。”[61] 经受了组织审查和流言蜚语,看到了延安的“封建色彩”和官僚主义,有了种种复杂经验的丁玲,对自身遭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1940年到1942年春“整风”开始之前,丁玲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包括: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杂文《开会之于鲁迅》《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这些作品由前期的“歌颂”转向“暴露”,更加注重对革命队伍中消极现象的揭露和针砭。贞贞“穿越幻象”的行动暴露了话语结构中的空隙。象征秩序的吊诡之处在于,混杂有“封建色彩”的革命话语被放置在比人的解放更高的位置之上。但仍需要指出的是,贞贞的这种革命性解放姿态并非出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哲学”,而是体现了蕴含于左翼文化逻辑中的“不断革命”的激情[62]。 然而,“穿越幻象”之后,生命将丧失立足之地。实际上,“主体生命的一致性就是建立在想象性认同上的。主体一旦‘知情太多’,一旦过于接近无意识之真(unconscious truth),他的自我(ego)就会土崩瓦解”[63]。尽管丁玲看到了革命话语中的复杂和难以自圆之处,但她却无法提供摆脱这种困境的道路,她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不堪忍受的空白之中,从而必将再次陷入难以自拔的僵局。因此,创作于1941年的《在医院中》注定成为一个丁玲无论如何都难以完成的成长故事。 注释: [1]转引自小林二男:《丁玲在日本》,《丁玲研究在国外》,孙瑞珍、王中忱编,第37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7][18]丁玲:《〈意外集〉自序》,《丁玲全集》第9卷,第25页,第25页,第2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8]丁玲:《致赵家璧》,《丁玲全集》第12卷,第137—138页,第137—138页。 [5]丁玲:《致叶圣陶》,《丁玲全集》第12卷,第16页。 [6][21][22]丁玲:《魍魉世界》,《丁玲全集》第10卷,第75页,第62页,第63页。 [7]安危:《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9]参见宋建元:《丁玲评传》,第22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彭淑芬:《试论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编者注,《湖南教育学院院刊》1983年第1期。 [11][25]秦林芳:《丁玲评传》,第121页,第140—14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2]范雪:《谁能照顾人——丁玲延安时期(1936—1941)对人与制度关系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 [13][16][23]丁玲:《松子》,《大公报·文艺》第130期,1936年4月19日。 [14]野泽俊敬:《〈意外集〉的世界》,《丁玲研究在国外》,第249—250页。 [15]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邵迎生译,第103页,长春出版社2010 年版。 [19]参见袁良骏:《丁玲研究五十年》,第55—56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0]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7卷,第2页。 [24]丁玲:《一颗没有出镗的枪弹》,《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1937年4月24日。 [26]刘思谦:《丁玲与左翼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 [27]聂国心:《论丁玲创作的情感历程》,《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28]参见朱正明:《丁玲在陕北》,《女战士丁玲》,第45—46页,每日译报出版社1938年12月版。 [29]里夫(Earl H·Leaf):《丁玲——新中国的先驱者》,《女战士丁玲》,第21页。 [30][31][32]丁玲:《东村事件》,《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5—9期。 [33]符杰祥:《“忠贞”的悖论:丁玲的烈女/烈士认同与革命时代的性别政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34][36][39][46]丁玲:《泪眼模糊中之信念》,《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4号,1939年9月16日。 [35]这一情节在《丁玲全集》的版本中遭到删除。 [37]参见程凯:《重读〈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 [38]吴晓佳:《“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0][51]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第254页,第254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41]参见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第1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2]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20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 [43][44]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胡大平等译,第116页,第1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5]丁玲:《死之歌》,《丁玲全集》第6卷,第322页。 [47]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第3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8]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第22页,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49]陆耀东:《评“我在霞村的时候”》,《再批判》,第96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50][55][57]华夫:《丁玲的“复仇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再批判》,第87页,第89页,第86页。 [52]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转引自《丁玲传》,第245页。 [53]萧军:《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 [54]有论者认为萧军所记录之事即是丁玲小说的本事。详见李明彦:《一类故事的两种写法——〈我在霞村的时候〉与〈金宝娘〉的互文阅读》,《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56]程凯:《重读〈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 [58]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98期,1942年3月9日。 [59][60]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第188—194页,第17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61]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第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2]李杨:《“右”与“左”的辩证: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年第8期。 [63]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第7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