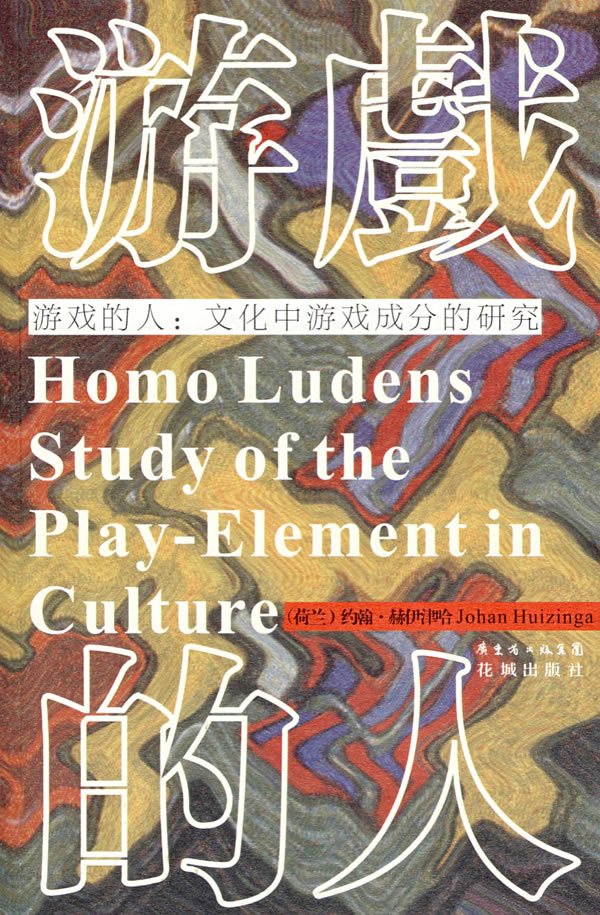[何道宽]游戏·文化·文化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21 传播学论坛 2007-12-19 何道宽 参加讨论
一、缘分 我的同事张晓红博士和花城出版社希望由我来翻译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我欣然从命;虽然手里其他书稿已经忙得够呛,我还是求之不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和赫伊津哈及《游戏的人》,间接相知已经20来年。20年来,我翻译并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代表作,屡次读到赫伊津哈其人。比如,麦克卢汉推崇《游戏的人》说:“游戏和娱乐的观念在当代获得了大量新的意义,新意义的源头不仅有约翰·赫伊津赫《游戏的人》之类的经典著作,还有量子力学。赫伊津赫把游戏理论与一切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 [i] 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语文学家、传播学家、休闲学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游戏的人》进行诠释。翻译该书的过程,是一个多角度审视文化史、理解游戏在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过程,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如我十几年前翻译麦克卢汉的感觉一样:消化这本书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体会和读者做一点交流。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回头再读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游戏》那一章,发现两本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下文。 二、兴趣 《游戏的人》国内已经有两个译本。[ii] 作第三个译本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为什么要知难而上呢?因为我不但想要推出一个比较好的译本,而且很想借此进一步了解荷兰这个文化大国。这个国家地理面积狭小,对人类思想文化和学术进步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拥有数以十计的世界级文化巨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博学鸿儒就有: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哲学家斯宾诺莎、历史学家威廉·房龙、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国际法先驱雨果·格劳秀斯、大画家伦勃朗和梵高等等;现今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比较文学大家杜威·佛克马,中国学人也相当熟悉了。 历史何以成就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呢?这是我有兴趣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限于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 (1)1568年荷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581年荷兰共和国诞生,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证券业、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加上学术自由的政策,荷兰取代法国而成为西欧的学术中心之一。几百年来,由于它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齐头并进,这个远方的小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2)学术中心转向荷兰。16世纪末,由于专制皇权和宗教思想的压迫,法国的大学者们流亡到学术自由的荷兰。从此直到19世纪,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学术圣地之一。[iii]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和“百科全书”派的许多著作,都是“出口转内销”,先在荷兰印刷出版,然后才偷运回法国的。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印刷品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在19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中。”[iv] “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到邻国瑞士与荷兰,把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荷兰的印刷业取得长足的进展,……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上升。”[v] “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荷兰通过引进却大大促进了造纸工业。法国的难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培尔和笛卡儿即在其中。”[vi] “从1587年斯卡利杰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vii] “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张的生产……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viii] “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ix] 自此,莱顿大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它已经并将继续吸引许多中国学者。 三、其人其书 约翰·赫伊津赫(Johan Huizinga,1872-1945)是荷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他攻读印欧语-日尔曼语语言学,1897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荷兰和德国的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等著名大学执教,曾任莱顿大学校长;二战期间对法西斯占领者持严厉批判态度,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被迫害至死。 他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文明复活的必要条件》、《愤怒的世界》、《17世纪的荷兰文化》、《文化史的任务》、《历史的魅力》、《痛苦的世界》等。他在世时已经成为欧洲文化史尤其是荷兰文化史的权威。他的著作经久不衰,《中世纪的衰落》和《游戏的人》均曾在国内出版,而且《游戏的人》已经有3个译本问世。他在中国学界的影响还在上升。 1903年,赫伊津赫就开始研究游戏。1933年,在莱顿大学担任校长的年度演说中,他又回答游戏的母题。1938年,《游戏的人》面世,这似乎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分为12章,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和功能,阐述游戏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主要是游戏和神话、仪式、法律、战争、诗歌、知识、神话、哲学、各种艺术门类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特别关注的是游戏精神在近代西方的衰落。他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对战争阴云表示严重的关切,对法西斯破坏国际法游戏规则极端愤慨,他希望人类社会和文化能够在游戏中继续成长,而且希望人能够学会更好地利用休闲。他把法西斯和政客叫做国际政治的破坏者和“搅局者”,控诉他们对文明的破坏。 在本书结尾前,他发出了这样的警世名言:“于是经过曲折的道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真正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文明的预设条件是对自我的限制和控制,文明不能够将自己的倾向和终极的最高目标混为一谈,而是要意识到,文明是圈定在自愿接受的特定范围之内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总是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文明总是需要公平的游戏。公平游戏就是游戏条件中表达出来的坚定信念。所以游戏中的欺诈者和搅局人粉碎的是文明本身。”(英文本238页,下同) 该书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目录管窥一豹:作为文化现象的游戏:性质与意义/表现在语言里的游戏观念/发挥教化功能的游戏和竞赛/游戏和法律/游戏与战争/游戏与知识/游戏与诗歌/神话的形成与游戏/哲学中的游戏形式/艺术中的游戏形式/游戏人视野中的西方文明/当代文明中的游戏成分。 这是一本研究文化史的严肃之作,说它是研究休闲学的著作固然不对,但它倡导游戏和严肃并重、不排除嬉戏运动、闲情逸致,还是有道理的。作者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比工作更为可取,实际上它正是一切工作的目的……希腊的自由人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他们有闲暇在有教育意义的高尚消遣中去追求生活的目的……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闲暇。” 因此,爱挑剔的史丹纳指出:“休闲问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突出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赫伊津哈的预期。我们陷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和资源,以便用创造性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去利用闲暇……“玩游戏的时候”,人处在创造力的巅峰,他完全摆脱了互相仇视的羁绊,他从粗俗的需求中彻底解放出来。”(16页)。与此同时,史丹纳又不惜用阿谀之词肯定该书的权威,他说:“赫伊津哈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于社会的母体,它在游戏中诞生,并且以游戏的面目出现。’”(12页) 史丹纳在序文里从两个层面对赫伊津哈提出批判,实际上,他提出了三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混淆高雅和委琐,对当代文明抱悲观的态度。史丹纳借用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的文章《赫伊津哈责难他的时代》的观点并且指出:“赫伊津哈骨子里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浸透了资产阶级高雅文化的理想和闲情逸致。他自始至终以挑剔和怀旧的观点来看待文明……他把整个文明当作游戏的观念固然给人启示,却是一种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观念把最高尚的价值即艺术、法律、哲学和文学放置到最委琐的审美层次上。” (13页) 第二种批评是,赫伊津哈的许多论述缺乏佐证:“赫伊津哈提出的许多佐证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许多词源的考据是业余水平”(14页)。由于译者不擅欧洲语言,所以我们不敢完全否定史丹纳的指控,说他是毫无根据的;但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说:赫伊津哈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以他印欧语文学家的背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判断,他的词源考据不会是“业余水平”。 第三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没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成果:“赫伊津哈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却采取孤傲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使他无法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成果……他对社会演化的观察太笼统,他使用“原始”这个范畴太简单。”(14页) 对于这种批评,赫伊津哈在自序里做了令人信服的答辩。原来他是有意识地使用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尽可能少用甚至避免使用其他的方法:“我所谓游戏不能够理解为生物现象,只能够理解为文化现象。我们研究游戏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读者将会发现,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游戏,无论这样的解释是多么重要;我使用了人类学的术语和解释,不过用得相当谨慎,即使不得不引用民族志的材料,我也是尽量少用。”(17页) 他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能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层次去研究游戏:“我们立即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使在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范畴。它有一个意义隽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在游戏时,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它超越了生活的眼前需要,它给行为注入了特定的意义。一切的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倘若我们把构成游戏本质的积极原理叫做‘本能’,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倘若我们称之为‘心灵”(mind)或‘意志’(will),我们的解释又太过头。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游戏吧,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个事实隐含着游戏本身的非物质属性。”(17页)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重要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自序里说:“本书旨在把游戏的概念整合进文化的观念之中。”他认为,“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17页)。 在国内外的多次讲演中,他“抠字眼”,多次纠正东道主用词不当,以杜绝对他讲题的误解:“我的讲题是‘文化固有的游戏成分’(The Play Element of Culture),每一次讲演的时候,东道主都想把我的题目改成‘文化里的游戏成分’(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他们把里面的‘of’改成‘in’。每一次我都提出抗辩,并坚持用“of”。”(17页)。 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用‘of’的目的是要说明: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决非偶然的成分,游戏就是文明,文明就是游戏。如果改用‘in’,游戏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游戏可能是非本质的、非固有的、可以或缺的、偶然的文化因子。游戏在文化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在“中译者序”的“定义和本质”与“功能和地位”里做进一步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何明修]革命的节庆,节庆的革命
- 下一篇:[李公明]吃,就是……权力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