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看到的这本书(《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记录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5年联合在越南所做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2005年的这次看似普通的考古发掘,是我国内陆省级考古研究机构在国外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也有人说是这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发掘完成的考古发掘报告。多年来,每当谈起这事,总不断有朋友同行问起我们为什么早在2005年就去国外发掘了。借报告出版机会,同时也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老院长焦南峰、新院长王炜林的委托,我把发掘的缘起、过程、以及发掘的收获体会唠叨几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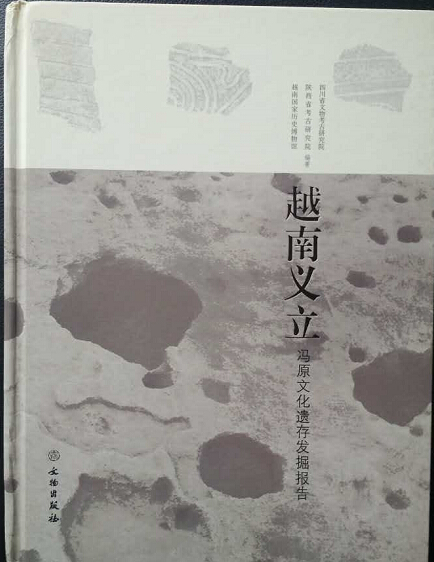 1992年夏天,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行业思想大解放。在此背景下,又逢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郑德坤教授八十寿辰的纪念大会。鉴于郑德坤教授在四川工作时收集研究过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所以这次大会是一个以古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地参会学者空前踊跃。四川因为刚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尤其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又加上四川是郑德坤教授工作过的地方,受到了特别的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都有专家参加大会。当时的我,尚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工作,个人的兴趣也有一部分在考古出土古玉器方面,而且,正在参加由李学勤先生主编,漓江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文物鉴赏丛书》中《玉器鉴赏》一书的撰写,因此之故,本人对玉器研究的学术动态尤为关注。当听到参加香港会议的专家介绍大会情况时,也格外留心。也就是从他们那儿第一次听说在香港会上,越南学者带去了在越南著名的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玉牙璋照片,并且说越南这位学者认为这与三星堆是有联系的。听到这消息,当时是感到吃惊的,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当时也就是听听而已,绝没想到我们会在十多年后到越南考古发掘以探究竟。 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发起召开了比1992年规模更大的东亚古玉研讨会,内地参加的学者有数十人之多,本人很荣幸也在受邀之列,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学和越南参会学者面对面交流并看到了越南出玉牙璋的照片。记得在会上,越南学者还表示可以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而且欢迎中国考古机构去越南考古调查发掘,当时在场的中国学者并没回应,本人以为是说给在场的考古所的同行听的,虽然听到越南学者发出的英雄帖后,心中曾怦然一动,但彼时我在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单位是没有田野考古职能的,就以为是说给国内考古部门的人听的,所以几乎没考虑过去越南考古发掘这事。 光阴荏苒,到了2004年夏,我调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已有两年,承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黄启善馆长的邀请,去参加他们馆70年庆祝大会。会后,我报名参加了中越边境学术考察,考察团里来自国内各博物馆的专家馆长不少,考察的重点有越南国家博物馆。广西自治区博物馆组织得很好,越方非常重视,馆长出面接待大家,参观完陈列后还举行了座谈。自从踏上越南国土我就一直惦记着1998年越南专家说的欢迎中国考古机构到越南发掘一事,在他们国家博物馆展厅里第一次看见玉牙璋实物,现在有机会和国家博物馆馆长座谈,机会难得,在自由发言环节,我向馆长提出我们单位如果到越南考古发掘,有无可能性?馆长立即向我介绍了越南的考古管理机制和考古工作情况,说非常欢迎中国的考古同行到越南考古,并十分肯定的说可以和他们合作。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自然喜出望外,我也当着大家回答说,我回去后立即研究并向上级汇报,争取能到越南来考古发掘。当时,参与座谈的中国同行,一部分人认为这事不可能。一部分人私下还不以为意,以为我有逢场作戏的成份。 其实我是非常认真的。回到四川后,我立即向院里领导班子成员和几个业务骨干通报了越南国家博物馆馆长欢迎我们去考古发掘一事,出乎意料的是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和支持。大家认为,中国考古是该走出国门了,而去越南发掘一处与三星堆遗址同时代,且出过与三星堆相近的文物的遗址,对我院的考古事业发展是个机遇,对推动三星堆文化的学术研究意义深远,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们在初步论证计划后向省文物局做了报告,省局领导也认为我院若能去国外考古发掘,特别是发掘点可能与三星堆有一定的关系,是件大好事,能有力扩大四川考古的影响力,省考古院的闯劲和主动作为的精神是可鼓的,很快同意了我们的报告并转呈报到了国家有关部门。但是,这个报告在国家有关部门近一年我们也没有得到批复。经了解,国家的这个部门拿到我们的报告后也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他们认为是件好事,但这事从没遇到过,他们的上级部门也没有赋予他们审批到国外考古发掘的职能,所以没法批复。他们表示爱莫能助。等不到批复,怎么办,放弃还是继续?我们觉得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弃。于是我们决定作为院里自拟项目来实施。这时,我们想到,我们的想法虽是地方考古所所为,但若成行,在国外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中国考古的形象,为了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我们还该找田野考古力量更强、经验更丰富的考古所合作。我跟时任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的焦南峰先生通报了情况并征求合作意向,焦院长听完后当即表示,这事是大好事,感谢我们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愿和我们一起去越南考古发掘。我同时也谈到我们遇到的困境,焦院长爽快地说愿和我们工作共进退、风险共担当,很是令人感动。这也更增强了我们去做这件事的决心和信心。到2005年秋,我院和陕西考古院自立项目、自筹经费、各出两人组成的赴越南考古队终于成行了。 考古队到越南后,受到越南国家博物馆的热烈欢迎,他们派出了专人配合我们考古队的业务和后勤工作。我方考古队详细调查了越方提供的几处遗址,最后选定永福省义立遗址作为发掘点,发掘前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最后才选定发掘地点,每次布5米乘5米探方四个,共布方两轮。在越南前后工作近三个月,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我们亲手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收获远超预期。 发掘期间,考古队开放工地让当地民众参观,结束后,还在永福省政府的组织下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社会展示出土文物,这支来自中国的考古队的工作得到了越南国家博物馆的首肯,赢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考古队员的敬业精神、认真态度都给越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国内早就出名的洛阳铲在越南考古工地的使用效果极佳,令越南同行大感兴趣,我们新中国考古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也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 2006年春天,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考古研究院在中国文物报社的帮助下,在北京举行了越南义立遗址发掘的汇报会,请到老一辈考古学家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李学勤等先生二十多人和各大媒体到会听取汇报。汇报会由我主持,发掘领队之一的雷雨做了汇报。专家们对这项工作给与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川陕两家考古院在越南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发展史上有极其正面的示范效应,给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开了个好头,中国考古发掘应该走出国去,也到了能走出去的时候了。当然,专家们对出国考古发掘应该着手的语言、专业、文化、外交上的准备也提出了很多好的指导意见,令我们受益良多。当天的汇报会专家们的发言在随后的《中国文物报》上有整版刊出。焦南峰院长代表我们两家做的总结有一段话给大家印象深刻,他说,高深道理大家都知道,文化交流需要,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也不用多讲。我们自己国内发掘都忙不过来,可为什么还要去国外考古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进大学起受到的考古史教育都在讲外国人在中国考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和国外考古合作发掘不少,可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现在中国开放了,我们也想去国外考古发掘,于是就有了这次越南考古。他这番朴实无华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随后,我们还邀请越南国家博物馆的同行到陕西四川两地访问交流,2010年后,陕西考古院王炜林院长也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的考古工作,2011年年底,应越南国家博物馆的邀请,我、焦南峰老院长和当年参加发掘的队员们组团专程前往越南访问,主要商讨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事宜。此后,报告编写工作驶入快车道,今年春节后,报告正式交付文物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国外考古——越南考古,算是划上了句号。 如果一定要对这次行动做个总结的话,我以为,我们的第一次国外考古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点是我们自发、自觉去做的。它既不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也不是去争取来的科研项目。 第二点是遗址和发掘点都是我们自选的。如前所述,我们向越方提出要求后,他们给了我们一片区域任我们挑选。 第三点是我们在越南的调查、发掘、整理都是独立、自主进行的,越方做了积极的配合。 第四点是我们的调查、发掘、整理、出版经费全是我们两院自筹的。 回顾中国一百多年的考古历程,若按从事考古工作的机构和参加者的国籍来划分,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河南、新疆、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做探险和考古调查。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才有中国机构和学者独立开展的考古发掘。二十世纪30年代,除中国考古机构自主的发掘外,也有中外合作的考古调查项目开展。50年代后,中国在自己的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从中央到各省市纷纷成立考古研究机构,考古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这期间几乎没有外国机构和学者在中国考古发掘。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的大门也慢慢向国外打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考古学者接连来中国访问讲学,有的直接和中国考古机构进行了联合发掘,中外考古学术交流一派繁荣。但是,冷静思考中国的考古发展史就很容易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初期的外国人来、到中外合作、到拒绝外国人来,再到中外合作,都是在中国土地上考古,还没有中国考古机构有组织有目的地到外国考古的(不排除有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以个人名义参加国外考古的),从学术和文化交流来说不应该也不正常。我们认为,作为文化大国和经济强国的中国考古界必须尽快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考古专业学生的共同心愿。后来,当我们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并走上考古院、所领导岗位后,虽地处内陆,又还仅是两个省级考古所,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时逢国家经济腾飞,我们更有把愿望变成行动的冲动,顺理成章有了2005年的越南考古行动。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们越南考古之后不久,国内陆续就有考古机构去蒙古、俄罗斯、肯尼亚、越南、老挝、孟加拉……,特别是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先生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袁靖先生同时呼吁国家应高度重视中国考古走向世界,提请国家把考古走出国门作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项目,上升到大国的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而一周前在郑州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主题就是走向未来,走向世界,大会特别安排了国内四家考古机构近年在柬埔寨、洪都拉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报告,大会国际味特浓。 最近有朋友对我们说,从十年前你们出国考古的一小步,到今天中国考古界出国考古迈大步;从十年前你们出国考古的一个蝴蝶翅膀振动,到今天中国考古即将刮起的走向世界的大风,很佩服你们两院当年的勇气和担当。我回答他们说,别把我们当年的决定和行动拔得那么高大上,我们只不过是把考古当事业在做,是职业使命感的驱使、是时代和机遇、是同事们的努力和担当、是领导们的支持和老专家及同行们的鼓励成就了我们这次国外考古行动。仅此而已。 感谢参加越南义立考古发掘的川陕两省考古院的考古队员的辛勤劳动;感谢对本次考古行动给与过支持的国内外领导专家和本单位的同事们;感谢越南国家博物馆和馆长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和在越期间给予我们的各种帮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高大伦 2016.05.30于成都 (责任编辑:admin) |
